|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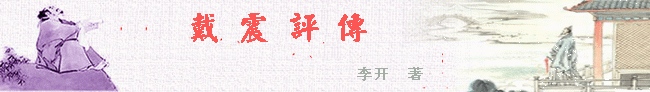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五、对《尚书》的研究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始于《尧典》,终于《秦誓》,其时代起自上古的唐尧,终于春秋初世,为我国上古时代的史料,故名曰《尚书》。它大体上是我国奴隶制时代早期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书》有所谓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分,今文《尚书》为汉初伏生所传,共二十八篇。伏生用这二十八篇在齐鲁间传授,逐渐形成西汉《尚书》学三家;欧阳《尚书》、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从汉武帝到汉宣帝,这三家都先后被立于学官,所教的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后来又加上汉武帝时民间所献的《泰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又把《盘庚》分为三篇,这样共三十一篇。西汉末年又忽然出现古文《尚书》,说孔安国家藏,比原来的今文《尚书》多十六篇。两汉古文《尚书》问题是个难题,戴震曾详为考证。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趁司马氏广求圣典之际,献上了一部伪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还有各篇标为“孔安国传”的注,还有一篇《孔安国序》。这部伪古文《尚书》一直被人们看作传说中的汉代孔安国传的真本,直到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才彻底揭穿了梅氏的伪作。阎氏以后,有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八卷,力反阎说,以驳辩求胜,不料引出了更多的申阎非毛之著,其主要著作有惠栋《古文尚书考》、程廷祚《晚书订疑》、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彻底驳倒了毛奇龄说。论战结束后,伪书已成定论,但剩下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因年代久远,读起来佶屈聱牙,很难读懂,更兼伪孔传的长期通行,汉儒传注一概亡佚,读《尚书》无所凭借。乾隆中叶的学者致力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解释工作,最著者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王鸣盛《尚书后案》三十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他们的共同方法,就是拿《史记》、《尚书大传》当底本,把唐以前的各种子书、笺注乃至宋《太平御览》以前的各种类书中凡有征引汉儒解释《尚书》文字逐一收集,分缀《尚书》各篇各句之下,使之成为辑佚性的汉儒新注本。戴震对《尚书》的研究,是在论战结束以后不久,重新解释《尚书》的工作刚开始时进行的。戴震一生,直接和《尚书》学有关的事件有以下一些:乾隆二十年(1755)秋,戴震在《与王内翰凤喈(按:王鸣盛)书》中用古音通假原理解释《尚书.尧典》“光被四表”即“横披四表”。
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有《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
此外,为校注《水经注》而研读《尚书.禹贡》和胡渭的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10 月校《五经算术》而举《尚书》待算明者列之,对《虞书》和《夏书》中有关“漩机玉衡”的研究等,已成为史地学和天文学研究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戴震的后期,还有专著《尚书义考》二卷,收入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原据贵池刘氏聚学轩本。该书是戴震思想完全成熟以后的著作,书中《义例》云:“至宋以来,凿空衍说,载之将不胜载,故严加删汰。”在清初《尚书》今古文问题论战及继后的解释《尚书》的工作的大背景下考察,戴震的《尚书》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尚书今文古文考》是一篇带总结性的文章。段玉裁《年谱》说它著于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这时距《尚书古文疏证》问世至少已有五十年(阎死于1704 年)。戴震在自己的考释文章中对《尚书》今文二十八篇与二十九篇问题,汉古文《尚书》的含义,《泰誓》篇的由来说得一清二楚。戴震说:《尚书》二十八篇,济南伏生所传,后附益《太誓》一篇,用当时隶书写之,故称《今文尚书》。
关于汉古文《尚书》,戴震因笃信汉儒,尤其是因笃信许慎而相信该书的真实性,他说: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许叔重《说文解字叙》记六体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盖如商、周鼎彝之书,故称《古文尚书》。入于秘府,未列学官,故谓之“中古文”
关于《泰誓》篇的由来,以及它如何进入今文《尚书》而成二十九篇的,戴震指出:伏生书无《太誓》,而《史记》乃云:“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时已于伏生所传内益以《太誓》,共为博士之业,不复别识言耳。刘向《别录》曰:“民有得《太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生屋壁,朽折散绝。《太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郑康成《书论》曰:“民间得《太誓》。”刘、郑所记,可援以补史家之略。应该指出,戴震就《史记》伏生书“二十九篇”有误的看法是正确的,司马迁正当汉武帝立欧阳《尚书》于学官之时,欧阳受之于伏生,故戴震肯定《史记》说的二十九篇就是民间的《泰誓》,后来进入了伏生所传书。戴震还主张以刘歆和郑玄之说补《史记》之疏略,这一主张无疑是可取的,因为刘说、郑说较司马迁的说法更近于情理③。至于汉代卫宏《古文尚书叙》说:伏生老而不能言,叫自己的女儿传言教晁错,又因方言不同,晁错不懂,“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戴震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早在晁错以前,早就有张生、欧阳生等从伏生受读,文化的传授不可能等到昏聩不能言的人而为之。戴震说:此不察之说也。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和伯实躬事伏生受《书》,由是《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之学。《史记》及《汉书》皆日:“秦时潘书,伏生壁藏之。汉兴,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其非得之口诵,无女子传言,事甚显白。还应说及的是,戴震为说明伏生《尚书》仅二十八篇,原无《泰誓》和百篇《书序》,引用了伪书《孔丛子》,不足为训。但他作出的判断结论是正确的。此外,戴震还著有《书补传》②。
① 《尚书今文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
② 同上。
③ 关于《太誓》,清儒有过不同看法,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1957 年版67 页。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
② 《书补传》已佚。秦蕙田《五礼通考·观象授时》卷三、卷五引用《书补传》为今仅见。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五礼通考》,卷181 至卷200 为《观象授时》,引戴震可见页139—366、367、369、374、37s、390 等。
自从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揭穿东晋梅赜伪书以后,对汉代古文《尚书》也一直是怀疑的,戴震对汉代古文《尚书》是不怀疑的。他对它的篇目作了详细考证。他指出,《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荀悦《汉记》、马融《书序》都讲到逸书问题,几乎众口一词他说是“十六篇”,戴震说,这十六篇“其篇名则郑注《书序》逸篇之目”,它们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弃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伊涉》、《原命》、《武成》、《旅獒》、《冏命》③此十六卷加今文《尚书》二十九卷加百篇《书序》一卷,“是为《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而逸书《九共》析为九,则逸书成了二十四,而今文《尚书》二十九又析为三十四:《盘庚》、《太誓》各分为三则净增四,《顾命》分“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浩》则净增一。如不算百篇之《序》,戴震认为汉古文《尚书》就是这五十八篇[逸书24+(今文29—2+6—1+2)= 58]。他说:不数百篇之《序》,故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桓谭《新论》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艺文志》虽数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郑康成所谓“《武成》逸篇,建武之际亡”,适当其亡篇,故《志》仅称五十七篇。戴震由汉古文《尚书》篇目的增减过程推论当时的学术传播情况,特别提到好古文的贾逵、马融、郑玄等人为什么不为古文《尚书》作注,却为今文《尚书》作注这样的有趣的问题。戴震说: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谓之《逸书》,刘向、刘歆、班固、贾逵校理秘书,成得见之。民间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学。建初、延光、光和中,尝诏选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学、广异义。而后汉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玄)传是学不一人。然贾、马、郑虽雅好古文,其作训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于学官者,岂逸篇残脱失次,不乎读欤?
戴震还考证了伪古文《尚书》。今本《十三经注疏》仍是伪古文《尚书》,故了解该书还是很有必要的。《十三经注疏》之所以如此,一是伪书中有真,那就是包含了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的内容,二是唐人作疏证就是用了梅赜本,三是认识其伪,当作伪书读,何况伪中有真,存此部分伪书亦无妨碍。故阎若璩订伪有功,但无妨仍存其伪书,不必销毁或剔除的。戴震简述伪古文《尚书》的出台及篇目组合时我们阅读是有帮助的。梅赜献出的伪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包括今文二十八篇(欧阳《尚书》已列为三十一篇)。有人分《尧典》后半部为《舜典》,分《皋陶漠》下半部为《益稷》,成为三十二篇[31—1+2—l+2=33]。等于说今文《尚书》未变。有人又另从百篇《书序》中采集了一些篇题,从当时已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集成篇,又另撰《泰誓》,总成二十五篇,从而凑足刘向、郑玄所说的汉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数。至于卷数,伪作者也作了安排,凑成《艺文志》所录数四十六卷,戴震对这一制造伪书的事实作了概括,最后指出:“是① 《尚书今丈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 页。① 《尚书今文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 至8 页。又今之《古文尚书》而非汉时秘府所藏、经师所涉之十六篇矣。”②肯定了伪作与汉古文《尚书》根本不同③。
戴震的《尚书今文古文考》,把一部十分复杂的《尚书》今古文史说得十分透彻,成为《尚书》学的入门教材。这除了戴震本人的识力以外,实际上也是对清初以来《尚书》学成果的一个总结。戴震曾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文字却认真。”①诚非虚言。
《尚书》原是古典文献,后来成为宣扬儒家“道统”的圣典,尊为《书经》,成为两千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主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清代学者研究这本书时,还是把它当作古史文献来笔耕的,戴震也不例外,如前所说:江声、王鸣盛、孙星衍研究《尚书》的方法基本上是个辑逸的方法。但也各有特色,江声是惠栋的学生,一味好古,唯古是收,剪裁甚少。王鸣盛的搜罗极博,劝夫很深,但把今古文学说调和在一起,看不清学派分脉。孙星衍是三家之冠,他的体例是“自为注而自疏之”,注简而疏详,努力区分今古文学派的不同,各还其是。戴震后期之作《尚书义考》很有特色。
一是区分汉宋,尽量兼古文和今文《尚书》三家说②,汉儒注释,力致无一遗漏。他说:有书契以来,莫古于《尚书》,汉儒训诂,各有师承,又去古未远,使其说皆存用备参稽,犹不足以尽通于古,况散逸既多,则见者可忽视之乎?故是编于各书所引欧阳、大小夏侯氏说,及贾、马、郑之注,详略必载古注,语简义精,虽尽收不见其多。至宋以来,凿空衍说,载之将不胜载,故严加删汰。但是,今古文《尚书》学不是每句、每字都能体现出来的,真要区分,也有相当难度,区分的方法,一是凭文献,二是凭识力。引用文献时既有辨正,又得尽量不遗漏,戴震就在引用文献过程中随时申明己见,这些申述处,大部分是想阐述今古文学理区分的。如“曰若稽古”条②:日若稽古(戴震按:曰当从古本作粤。)
《尔雅》:粤,于也;若,顺也。
《后汉书·李固传》注曰:“《书》曰:‘粤若稽古帝尧’。郑玄注曰:‘稽,同也。古,天地,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尧。’”
《三国志·三少帝记》:“帝问曰:‘郑玄日,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地。’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庚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考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戴震按:孔氏颖达《尚书正义》曰:郑玄信讳,训稽为同,训古为天,能顺天而行之,与之同功,古之为天,经无此训。)
② 同上,8 页。
③ 梅赜献出的《伪古文尚书》,清丁晏《尚书余论》考定为出自三国魏王肃之手。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90 页。
② 贾逵、马融、郑玄虽解其今文立于学官的《尚书》,但因其以古文经观点解今文仍可视作古文。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尚书义考·义例》。
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尚书义考》。
戴震的头脑是清醒的,并没有“唯古是信”。梁启超在评价清儒《尚书》学成就时曾说:“我稍为不满意的,是他们有时拘宋汉儒太过。例如‘粤若稽古’郑注训‘稽古’为‘同天’,甚可笑,但以出于郑而强从之。”①戴震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从郑玄古文经中严加剔除。
二是针对《尚书》古解古注缺乏,戴震努力建设自己的注释体系,他的基本思路是从语言文字入手,从今文《尚书》的原著出发,“以词通道”,作出他本人的、合乎古义的解释,并以自己的解释为判别标准来区分今古文义。他说:《尔雅》解释《诗》、《书》,汉儒释经多宗之,则注内已见采录??惟《尚书》无汉儒全注:今经文之下,即取《尔雅》以存古义仍以“曰(粤)若稽古”条为例,看看戴震是怎样形成自己的《尚书》注释体系的。
戴震案:发端之辞,或言“于”,或言“爱”,或言“粤”,声义相近,《说文》“粤,于也。审慎之词。”《周书》“粤三日丁亥。”据《说文》“粤”为本字,其作“越”,或作“曰”,并六书之假借。《尔雅·释诂》:“粤、于、爱、曰也。”“爰、粤、于也。”“粤”与“曰”重出于六书为疏。《尔雅·释言》:“若、惠,顺也。”“若”与“如”一声之转,“惠”与“顺”一声之转。《说文》:“如,从随也。”“从随”之义引伸之为顺为同。篇内“若”字多矣,皆相因无异解,不得合“日若”二字为发语辞。《召诰》之“越若来三月”,“越”者发端语辞(徐锴《说文系传》释“粤三月”云心中暗数其日数,然后言之。)“若来三月”则由二月顺数之,至方来之三月也。“若”字宜从古注。“稽古”犹言“考之”,昔者几已往则称“古”、“昔”,《盘庚》篇谓前王曰:“古我先王。”《孟子》书谓数日之间为昔者是也。前史所注记,后史从而删取成篇,故发端言“粤若稽古”,犹后人言“谨案”云尔,明不敢以臆见爽失其实也。自汉迄今并误读“粤若稽古帝尧”为句,汉唐诸儒以稽古属尧,郑康成训“稽古”为“同天”,于字义全非,贾逵马融王肃皆为尧考古道,而梅喷奏上之《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亦同。孔传本晋人伪撰,袭取贾马之注,故魏博士庚峻引贾马及肃,而不言安国。《周官》“唐虞稽古,”又伪古文语,与伪传同出一说也。宋儒以“稽古”属“史官”,而未明于“粤若稽古”四字句绝。其下文“帝尧日放勋”,记帝名号也。《皋陶谟》与《尧典》一例下“皋陶日”,则直记皋陶之言也,林氏疑于两“曰”字,由句读失传耳。从戴震对“曰(粤)若稽古”四字的长篇按语中可看出以下几点。一是“粤”为发语词,“若”为“顺数”之义,“稽古”为“考之”之义,四字为句,意犹后世云“谨案”。二是从《尚书》发掘语言表达的内证,“若”不当连上说成“粤若”为词,也不当连属“帝尧”为句,三是批评郑玄的荒唐解释“稽古”为“同天”。四是批评程宋对《尚书》的解释。五是发扬《尚书》古文经说。六是对收集到的解释《尚书》的资料一一严加辨别,最后批评林之奇《尚书解》即此一例。戴震试从语言文字入手直取《尚书》原意,辨证汉唐以来的占注疏。可谓另辟蹊径,创《尚书》学研究的新路;和江声、王鸣盛、孙星衍《尚书》学名著相比,义例之严,识见之深,辨证之细,不是很可观吗?可惜的是戴震的《尚书义考》仅两卷,没有形成大气候,但它无疑是《尚书》学研究中的“少而精”的精品之作。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83 页。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尚书义考》。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尚书义考》。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