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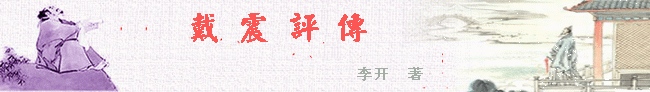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六、对《春秋》的研究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今存的《春秋》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历十二君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谷梁传》所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记二年)。它基本是鲁国史书的原文。传说孔子著《春秋》,不可依信,但孔子以《春秋》作历史教科书授徒却是可信的。无奈此书太简,没有传注简直无法读懂。宋王安石答复他人问《春秋》说:“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公羊传》、《谷梁传》解释经文为主,叙事极少,不是历史性质的书。西汉时只有《公羊传》设立博士,可以说那时《春秋》只有一传。后来又有《谷梁传》问世,但东汉时仍以《公羊传》为最盛,六朝以后,《公羊传》、《谷梁传》渐废,独行《左氏传》。到了唐代、出现了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①的状况。宋代治《春秋》的人很多,以胡安国的《春秋传》最为盛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①元明两代以胡传取士,《春秋三传》基本被废,间有治《左传》的,也仅是当作策论的资料。清代以前《春秋》学的状况基本如此。
清儒复兴古学,《春秋》及三传之学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顾栋高(1679—1759)对《左传》作历史的研究,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将春秋列国史事,天文历法、世系官制、疆域地理等列表说明。梁启超曾评论这部书说:“《礼记》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象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用这种方法治历史的人,向来很少,震沧(按:顾栋高的字)这部书,总算第一次成功了。”②用治经的方法治《左传》,大抵是嘉道年间才有巨著,那就是刘文淇、刘毓崧父子的《左传正义》③。《公羊传》的研究肇始于戴震的学生孔广森,和较孔氏成就为高的庄存与(1719—1788)。庄氏是与戴震同时代的人,常州学派的开创者,著《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庄氏将公羊学传给他的外甥刘逢禄,著《公羊传何休释例》,从此公羊学大昌,继后有龚自珍、魏源、戴望等,皆公羊学派。《谷梁传》自古清孤,清代中叶以后有钟文丞的《谷梁外注》、侯康的《谷梁礼证》、柳兴思《谷梁大义述》。
戴震对《春秋》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今本《戴震集》中《春秋改元即位考》上中下三篇中。此文是与《尚书古文今文考》同时代的著作,都是1753至1763 年间的成果。戴震曾自述这三篇文章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①此外,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戴震校毕《五经算术》呈交时,亦举《春秋》之“待算乃明者”列之。戴震的时代,刚刚跨过宋元明三代取消《春秋三传》的年代,对① 韩愈《赠玉川子》诗。
①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本219 页下栏。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95 页。③ 今有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文淇《春秋左氏旧注疏证》。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5 页。
“三传”的学术地位的确认是一大事。戴震对“三传”十分重视,他在例论郑玄《三礼注》时,说:“当与《春秋三传》并重”。②可见《春秋三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在谈到唐代作《五经正义》时曾说:“唐初,汉时书籍存者尚多,作《正义》者不能广为搜罗,得所折衷。于《春秋》专取杜预,于《易》专取王弼,于《尚书》专取孔安国,遂使士人所习不精。”③言下之意,甚责孔颖达专取杜预《左氏传注》,而不能通观《春秋三传》。在《改元即位考》一书中,戴震同时强调习《春秋》本经时应重视《左传》、《谷梁传》,虽书中未提及今文经的《公羊传》,但从他强调《三礼》郑注可比《春秋三传》,强调研治《春秋》当可通观《三传》而折衷看,戴震对《公羊传》同样是重视的。
《春秋》为史,《左传》亦史,唯《公羊》、《谷梁》为经,清儒治《春秋》学有从史入手,有从经人手的,治《左传》亦从史、从经两个方面入手。戴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治《春秋学》从何入手呢?从《改元即位考》看,他从治经入手,推论史实,是要从经论中推求历史,他是并不昧于治史的。纵观《即位考》三篇,上、中、多重《春秋》名分辞例的考索,与《公羊》、《谷梁》考《春秋》辞例“一字褒贬”的微言大义相类,可看作是经的研究,而下篇则由名分辞例考索进入历史奥秘的探求,戴震说:不废改元朝庙,与名更始,而废正百官,非义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礼,鲁史记皆书即位也。盖继弑君,大变也,典礼所无;继弑君不书即位,史法所无。君子修之,以为深痛之情异于继正,是以不书。不书而仍不没其即君位之事,于“春王正月”之文见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管《春秋》辞例多么谨严,多么讲究名分之正,但历史不是沿史家的书本逻辑辞例更迭的,而是发生了一系列不合名分的诸如弑君之类的事。不管现实又是多么残酷,史书《春秋》还是要突破原有的名分辞例而于别处记载之,虽弑君不书“即位”,但仍“不没其即君位之事”,亦即仍须直言之。在记史实,存客观事实,不得不书的要求面前,经书《春秋》的原有的谨严辞例和名分制约往往不发生作用了,戴震看到了历史事实,客观存在的不体面不合名分的更迭,越出了那《春秋》的书本逻辑。《春秋改元即位考》全文似乎在寻求逻辑辞例和历史更迭的相符,但戴震最终所发现的还是那脱出常规,与名分不相符的严酷事实和《春秋》不得不书的做法,戴震的探求,在经书逻辑辞例背后深深隐匿着历史更迭的反思,虽然这种反思并没有达到后人所期待的那样的高度。限于当时的时代条件,我们只能公允地说,戴震从经书考据、逻辑辞例的剖析中能作出这样的尽管是有限的反思,已十分可贵了。
今本《戴震集》中有一篇与《改元即位考》紧相邻的文章《周之先世不窋出上阙代系考》,更是一篇寻求历史发展完整过程的考释文章。戴震发现,不管统治者是怎样的昏乱,历史是决不会终止的。历史上,竟然会有中原后主自窜于戎、狄而东山再起的,戴震通过考释,企图填补历史的空白,他说:周自公刘始居豳,书传阙逸,莫能详其时世。考《国语》、《史记》所录,祭公、谋② 《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
③ 同上,490 页。
① 《春秋改元即经考》下,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6 页。父谏穆王日:“昔我先王(俗本《国语》脱去“王”字,宋本及《史记》并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复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盖不窋以上,世为后稷之官,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夫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时,《史记》称孔甲淫乱,夏后氏德衰,诸候畔(按:通叛)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邹之封,此时乃相因而失,诸侯侵夺,天子不正之,是以远窜。从上面的文字看,戴震追索历史的真正面目已不限于辞例谨严的《春秋》,而是开明地求助于《春秋》外传《国语》及后起的、经常违拗《春秋》经训的《史记》,从而正确地推求出公刘立国于豳以前的周的先世之代系。
旧时代,还有什么比皇权更替更重要的事情呢?《春秋改元即位考》就是考证奴隶制时期最高权力更替时的仪式、相关的内容等级划分、《春秋》记述相关事例的辞例,戴震考得的主要之点有:一、即位和改元。即位即天子就职,改元即改定始年。即位有即位之礼,一般是服丧一年后改元即位。《春秋》于改元前后称名皆不同。戴震说:“即位之礼,先朝庙,明继祖也;出适治朝,正君臣也;事毕反丧,服丧未终也”。又说“逾年而后改元即位,《春秋》于内称公,于外书爵,未逾年于内称子,于外书某子。”①但是,平王东迁以后僭越之事屡屡发生,陪臣亦执国命,弑君之事亦不少见,故改元即位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从而有了变例:先即位后改元,戴震考释曰:“世变相寻,未逾年,既葬卒哭而即位焉,逾年乃改元。”②可见彼时改定始年和即位已分开,当时“即位”掌权比改元更迫切。二、归纳出几种彼时皇权陵替,权力再分配时的情况及相关的君臣名分。大体上说有:君臣名分定,君臣名分不定而不以国姓称之,君臣名分尚未定而以国姓称之。戴震说:“立子以正,君薨为丧主,《春秋》即正其为君,义素定也。世子虽在丧,未改元即位,不可谓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国者绝之,不以国氏,以有正也。公子争国,分非君臣,不绝之,无正也,则以国氏。立子不以正,未即位不正,其为君义不素定也;虽有先君之命,私也。”③三、面对复杂的皇权陵替和君臣名分的类别,《春秋》辞例是怎样叙述的?戴震归纳《春秋》分继正即君位、继正变文、继故即君位、继故变文。继故指有僭越、弑君之类引起的提早即位。继正:《春秋》书“春,王正月,公即位。”例昭公元年。这一说法,《三传》曾经作过解释,戴震把它作为全书辞例而列出“继正”,是一大创发。继正变文:“书‘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书即位以表微。”例《经。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对继故即君位,戴震讲得较客观,他说:“继故即君位,经国之体,不可以已也,践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书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书即位,以见其情。”①例庄公、阂公、僖公皆有此例。最后一种是继故之变文。戴震评述此辞例说:“继故之变文,则书即位,继故而书即位,以不书即位者,比事类情,是为忍于先君也。”②例如桓公、宣公。
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7 页。
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3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3 页。② 同上。
在以上条例的归纳中,都涉及到经文中“春,王正月”这句话。戴震事实上已把这一表达区分成:继正、继正变文、继故、继故变文四种。也是对《春秋》全书义例的一个创发。对“春,王正月”这句话,《左传》、《谷梁传》、《公羊传》都作过解释,特别是对《经·隐公元年》的解释甚详,但仅仅围绕某年事实言之,未创为全书义例,将此同一句话创为全书四种义例的,肇始于戴震。
四、先君下葬与逾年改元的关系。后者更为重要,从这一点说《春秋》倒是就活人而不就死人的。戴震归纳其例说:“先君虽未葬,即逾年则书爵。”例如桓公十三年书卫侯,成公三年书宋公、卫侯是也。又“书爵与国内称公同,”例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而《春秋》曰“公即位”,是逾年之故,既葬逾年,当然就更不必说应书爵称公了。又虽葬但未逾年,犹称子,例文公十八年书“子卒”,值公二十五年书“卫子”都是适例。而未葬未逾年,更不必说起应称子了。可是有没有既葬而未逾年称其爵位的呢?有的,如宣公十年书“齐侯”,成公四年书“郑伯”,戴震认为这是《春秋》重“逾年改元”的变体和特例。戴震说:“既即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书子也。其变礼也,不知所始,始变礼者,不恤人言,必有所托。”①戴震清楚地看到用此“不就活人”的“变礼”是“不恤人言”,戴震从《春秋》义例中看到了上古对人的态度问题,一般说,《春秋》还是主张重视人,“恤人言”的(当然主要是指统治阶级中的“人言”)。
五、关于先君未葬而是否可书君的问题。戴震认为,《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一语,该年夏五月齐侯潘卒,九月舍被杀,先君潘未葬,舍未即位而书君,那是“义素定者也,书君不与书爵同,不可以爵书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②《信公九年》“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一语,献公未葬,奚齐未成君,故称“君之子”,戴震说:“义不素定,而未即君位也。”③而《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这时献公已葬。《哀公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茶。”戴震指正:“逾年即君位,而后得为君,此义明而嗣立之际严。”④可见称君与否,完全视正其君臣名分而定。至于《桓公十五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那是忽在外五年,未即位而出奔,归不得书爵,故不称“郑伯”,《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卒。”戴震指出,此“王”字是“王畿”之义,非天王之号。不可曰周,故曰王,犹《诗经·王风》,不可谓“周风”,戴震并指出:《春秋》书“王”字从同①。
六、进一步分析“继正之变”。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这一说法,《左传》云“不书即位,摄也。”戴震说:“终隐之身,自以为摄,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书。”②而庄公、闵公、僖公同样的说法是“继故即位”。谷梁氏说:“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弟不忍即位。”杜预注:“虽不即君之位,而亦改元朝庙,与民更始。”③戴震不赞同这个看法,他说:“余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4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5 页。② 同①。
③ 参见《十三经注疏》1713 页中、2372 页中。
以谓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云尔。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虽先君不有其终,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即君位于改元之初,及其视朝,将不正朝位乎?苟视朝然后即君位,岂得无深痛不忍之情?然则改元之初而即君位,于深痛不忍之情何伤?彼所谓不即君位者,迨至视朝,终不得避君位也。则初视朝,乃其即君位之始,何进退失据乎?不废改元朝庙,与民更始,而废正百官,非义也。”④这一段关于君位问题的议论,是戴震《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他的意思是说,改元即位是国君莅事的一个必要的仪式,不能因为旧君不以道善终,而后君就不忍即位,君位“非先君一人之位”,“先君不有其终,新君不可不有其始”。戴震是想通过即位这样的大典仪,促使新君成为一个有开始且又以道终的好皇帝。按杜预的看法,无即位大仪,但又改元,与民更始,废正百官,戴震认为这样做不合古之礼法,当然也不合《春秋》辞例谨严的本义。当行即位之礼,不失为封建时代的一位智者的识见,为什么行即位大礼能帮助新君有其始而又能以道善其终呢?这是找不到切实的根据的。戴震的这一研究,作为发现《春秋》的书本逻辑辞例无疑是有贡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希望有个好皇帝善终,也不能说是坏事。早期戴震对《春秋》的研究,是积淀着亿万穷苦百姓想有好皇帝的愿望的。
以上六条,是戴震研究《春秋》归纳出的体例,朱彝尊曾说:“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①洪兴祖说:“《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求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也。”戴震寻求《春秋》的内在规则,并为阐释,对理解该书是有很大帮助的,且创发了前人未及之说,甚是可贵,且由书例而及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形,虽后者的说明不免苍白无力,但可看作研究者的思路是想架起书本的深层体例与历史现实间的桥梁,是个从逻辑规范到历史的过程。戴震归纳条例以说《春秋》的方法,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戴震本人曾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将《改元即位考》付抄时说:“《春秋》一经,余欲做此种文字数十篇,便令大义毕举。”由此可见,戴震研究《春秋》的方法是个“高屋建顿觅条例,傅例再说原经义”的方法,这是个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但条例本身仅限于书本逻辑之内,就古代文献本身的研究,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具体到残缺不全的太简单的《春秋》来说,更是一种好方法了。
以上主要是指戴震早期对《春秋》辞例的研究,如综观戴震一生,则又另当别论。汉代董仲舒著过一部《春秋断狱》,又叫《春秋决事比》,完全化《春秋》为法典,是儒学的法家化。清赵翼说过,“汉制法制未备,”所以要用“经义断事”①。马端临论《春秋决事比》也说:“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按:指《公羊传》、《谷梁传》)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②这正是“以理杀人”的根源。戴震后期对“以理杀人”的控诉,是他早年研究《春秋》的重要补充,也是对“春秋断狱”之类的做法的严正声讨。一个正确的理论,其意义和价值往往可以辐射到书本理性和现实世界等④ 同①,25 至26 页。
① 朱彝尊《经义考.论崔子方〈本例〉》。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见《丛书集成初编》3543 号38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二,见商务万有文库本第二册考1567 中栏。各个方面。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