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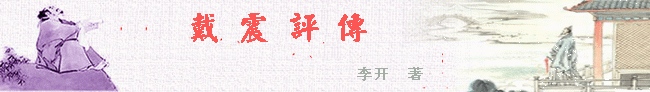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二、与章学诚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已(1773)夏,戴震和章学诚相见于宁波道署。那时,戴寓居浙东,主讲金华书院,授课之余,研读顾炎武《诗本音》,讽诵经文,叹为不易。而章学诚正撰《和州志》,与浙江宁绍台道冯定九交游。章、戴相见时,戴震已五十岁,章学诚三十六岁,时戴震已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三十六年(1771)撰《汾州府志》和县志,章学诚首撰《和州志》刚开始,始作体例。章、戴论学,可谓一是学界新秀,一是完全成熟了的饱学硕儒。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戴震过世后十三年,章学诚曾著《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追述此事。
章、戴分歧,由来已久。自顾炎武倡理学即经学,乾嘉学人以语言文字通经,章学诚力主“六经皆史”,对戴震的“以词通道”颇不以为然,章说:“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按:伏生、郑玄)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①意思是说,解语言文字并不能通道。章、戴论修志,分歧甚大,戴重在考订史地沿革,章重在言文献。初看仿佛没有什么区分,考订也要通过文献,重文献也为考订。其实,戴、章的分歧,有类于戴震和惠栋的区分,戴求其是,惠求其古。重文献的目的是考订史实,尽信书不如无书。考订沿革还必须与实际情形相结合。章提出重文献,是以一般历史科学的文献要求来要求地方志,未免不合方志需实情的体例,戴震重沿革实际上就是重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戴在《答曹给事书》中举出诸多文献有误的例子,已如上一节所叙述,在纠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将虎泽说成永宁州北,与虎泽近邻的美稷城在汾州府西北时,以实地指其文献之误:“自府而西北至永宁州之北,群山簇拥岩谷之险,绝无平地以容所谓虎泽者。”②由此可见,戴震重考订历史沿革的提法较章氏主文献表达得更科学。由于章、戴的一贯分歧,章说:“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③其实,戴氏著《七经小记·水地记》,研核《春秋》,校注《水经注》、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为人撰谱牒传记,已足说明戴氏不是不懂史学。章、戴时期的史学和后来的通史不大一样,那时的史学多指经史要旨、地方志,章氏《文史通义》内篇多言经书,以史解经,以经言史,外篇纯为修志之事。从这个情形去看,戴震恰恰是个史地学大家。而其史论则渗透在修志、撰谱牒、校《水经注》的实践中。至于戴震重史实考订,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章太炎曾要修“启寻方来”的通史,“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并说:“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①章太炎把语言文字看作研治古代文化和古代史的化石,颇具的见,而他认为,戴震精于文字音韵,自然是精于“无形大史”的人,故章太炎治史,反讥王鸣盛、钱大听治史“昧其本干,攻其条未”,反“觉定字(按惠栋)、东原,真我师表“。可见戴震确实是治经学而连同① 章学诚《校雠通义·外篇·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②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7 页。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记与戴东原沦修志》见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 年版869 页。①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 年版172 页。
史学的人。
据章学诚的记载,当戴震看到《和州志例》以后,就说:“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当章学诚作出辩白以后,戴又说:“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②这里主要之点是:一、修志不贵古雅。二、地方志体现地方习俗、地方文化的特色。三、地方志用于说明地理位置、地名沿革等问题时,尤须重于历史地理的研究,非要把地理的历史沿革搞清楚不可,如地史沿革有误,必然张冠李戴,整部地方志不是某处,而是他地,因而失去了价值。故戴震批评章学诚“侈言文献”。平心而论,戴震的这些看法大致不诬。修地方志不贵古雅,而要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恐怕修志的目的就在此。前面已提到,自周代起采风览观民俗,上古就有方国地史,都是地方志的滥觞,它们并非不古,却以处处体现地方文化特色见长,如可以与方志相比的汉代扬雄《方言》,著者并非不能雅,恰恰是著磅礴有势、富丽高雅的大赋的名手,但《方言》一收早已不雅训的“绝代语”(汉代仍可能出现在方言中),二收方国俗语,唯其如此,它才有价值,成了“悬之日月不刊”的名著。戴震崇尚汉学,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以研习国故经典为能事,但同时强调地方文化的意义,尤其在纂修地方志中,他主张完全从俗,全力捉住地方文化,在戴震的整个视野中,志书无疑是经典文化的补充,是民族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至于戴震“悉心于地理沿革”的主张,上节提到的《答曹给事书》中一系列的纠缪改错,是这一主张的一个注解。他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代人所作的《应州续志序》中也曾强调说:“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并因此对《应州续志》的作者“南丰吴君”提出建议,作了一系列的纠谬补逸(当时的学风是作序绝不为人护短),可见他在与章学诚论修志时提出的主张是深思熟虑之论。在戴震看来,也只有从俗并考其沿革以求实,才能使方俗史志发挥“雅”的作用,他说:“余曩因诗古文词所涉,检寻郡邑志书,其于经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废县,以及境内之利病,往往遗而不戴,或载之又漫无据证,志之失,大致尽然。”①戴震的治学经验反复告诫他,地史沿革不可不考。就以《应州续志》为例,连应州(今山西应县)古代在何处也发生了问题。旧《应州志》称应州为秦汉的阴馆县。阴馆又在何处呢?考《汉书·地理志》“雁门郡阴馆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说文解字》也说:“漯水(按:即治水,今桑干河上游)出阴馆累头山。”《魏书》、《水经》皆同。《寰宇记》则累头山和阴馆城相距还远着呢!因而需要确指阴馆在何处,戴震继考《水经注》、《十三州志》、《读史方舆纪要》、《一统志》,发现阴馆与那些和应州相近的地区相距甚远,以阴馆说明应州则过于粗疏。《十三州志》说:“剧阳在阴馆东北百三里。”顾祖禹说:“汪陶废县在应州西。”《一统志》:“汪陶在山阴县东。白狼堆在〔应〕州西北,巨魏亭在〔应〕州北,剧阳在〔应〕州东北。”戴震的结论是:应州大约是汉代汪陶、剧阳二县地,与阴馆无关。
《应州续志》又说:“北魏天平二年应州置善无郡,领善无、沃阳二县。② 《文史通义校注》(下),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本1985 年中华书局版869 页。① 《应州续志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8 页。顾祖禹也说:“沃阳废阳在应州西南,善无城在代州西北七十里,本汉县。”戴震考之《汉志》,沃阳有盐泽。《水经注》:“盐池西南去沃阳故城六十五里。”《十三州志》云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这些说明盐池、沃阳、善无、中陵该相距不远,但据文仍不能说明问题便进一步考之实地,中陵是乾隆时宁武的神池县(今山西神池县),善无在其北,沃阳盐他是唐代的安北部护的胡落盐池,乾隆时的偏关外归化城西的蒙古地,清代偏关五寨吃的盐仍从蒙古来,况且中陵、善无、沃阳的水流归地近内蒙的树颓水(按:或指浑河)注入黄河。经文献书证和地域实证相结合,戴将沿革弄得水落石出,指出沃阳距应州遥远。《应州续志》说曾在应州置郡领沃阳、善无是不确的。以上二例,再一次说明,戴震十分重视文献,文献功夫是历史科学的基本功,戴震岂有不重视之理。当文献不足征时,应考之实地,以求地史沿革究竟。文献是手段,考证史实,弄清原委是目的。而这些归根到底又服从于修志以“利民”这个总要求。
戴震认为,不仅修地方志如此,凡涉及历史科学的学问均应如此。乾隆三十六年(1771)戴震应邀到汾阳修县志时,有位叫温方如的向戴震请教,温氏研究汾州地区的金石文字,著《西河文汇》,方如持三寸搦管,在荒榛颓垣中寻访残碑,精神是可贵的,但未能远涉名区,仅杂取府州县志以证,而汾州府辖州县八,温氏还差两个县没有顾及到,于是又涉及到书名所及的地史沿革问题,温氏书名踵其师周某《西河遗事》、《西河诗汇》之类,因是寻访西河的金石文字和碑石,不得不考其沿革。所谓西河,先秦时府境于七国赵地,其西临永宁宁乡,直到北魏太和年间才正式置西河郡(戴震的考释已见上节)。温氏的书采编自宋以下,因是西河郡的金石、碑刻,“特以有涉于方志,观事存之”,“倘用是专事遗逸,为府州县补阙正讹”,同样是有意义的,因而考订沿革,正西河之名,以期搜集之全,就十分必要了。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方志、地区文集中,文献往往只是潜台词,是考有关史实的基础,一旦考订清楚,是不必堆砌在方志、文集之中侈言文献的,这正是醇儒之论,硕学之士的卓识,是很值得玩味,值得索其志趣的。
针对戴震不贵古雅从世俗,重地史沿革而不侈言文献的说法,章学诚说:“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所谓“是”,就是合乎对象的实情,合乎规律,但不一定合乎古雅。章说:“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戴震的“从俗”,如前所说是从当地实情出发,从地方俗文化的特点出发,即使是通俗、浅俗,深入方能浅出,又岂是“世俗人皆可为之?”章又说:“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但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①方志是历史地理科学,它是历史,但涉及地理史,戴震所谓沿革,正是地史的沿革和发展,至于“宁重文献而轻沿革”,等于说“宁重资料而轻由史实① 《文史通义校注》(下),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869 页。得出的实际结论”,如果修志不以可靠结论为和起点,仅是堆砌文献资料,就可以想象方志将成为地方资料汇编,连当时的实地实情的叙述也被挤走。章的这一修志思想,连冯定九起初也不能接受,章叙述了上面的一番话以后,冯发问说:“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善,岂仅为之数百年以内设邪?”章解释说;“史部之书,详近略远。”又说方志不过上百年,二三十年要重修,“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②。史书详近略远,也不足以补其汇集古今资料之弊,这显然是两回事,不能说古代资料少些而近现时期资料多些,就可纠补资料堆砌之弊。又说因百来年,二、三十年要重修,沿革明显,不用再考,如重沿革,则用不到续修方志了。事实是戴震力主由文献史实将沿革考订清楚,万无一失,以为起点,决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恰恰为后世续修楷式,为后世续修提供一正确的前提,续修志则可放手在前志基础上叙述近百年的新变化。
章学诚的这篇追记的文末,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戴震在与章学诚论辩过后,第二天将《汾州府志》拿给章看,并说,于沿革以外,与众不同者是列僧人僧事于古迹之中,因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对此,章氏认为“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至于在人物门类中取消僧人,章氏诘戴曰:“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并认为戴的做法是“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①。其实,戴震对《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的体例非常重视,反对结构“漫无叙次”,采用纲目体式,“分列纲目,以纲为断,目为按,令阅者因纲检目,因目证纲”②。例《汾州府志》纲目:沿革、疆域、山川是全书总纲。总纲贯彻重沿革的思想。“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疆域辨而山川乃可得而纪”,“山川次乎疆域,其奠也,本天地之自然,而形势在焉,风气系焉,农政水利兴焉”③。在门类排序上,居首的有:城池、官署、仓廒、学校、坛壝(wěi 坛的通称)、关隘、营汛、驿铺、户口、田赋、盐税。其次:人物,其关及一方历史的缩影。再次:古迹、杂考,“备稽古者之检之也。”最后:艺文。在体裁上,图、表、志、传、考、录诸体皆备。为章学诚所讥笑的“列僧人于古迹”一事,显然从僧人的社会意义方面考察,看其能否成为一方历史之缩影,并非据什么“血肉之躯”列目,戴震完全没有错。戴震的修志指导思想和楷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影响清代的修志,直至今天仍有参考意义。章学诚是清代史学的一代宗师,他的“六经皆史”说在史学史上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一面冲破经学藩篱,把史学从文献考订中解放出来的旗帜,但在与一代哲人戴震论史时,未能虚心听取这位饱学硕儒的充满经验的广袤性和思辨的深邃性的见解,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从总的方面看,章学诚还是能正确评价戴震的人,但也存有很深的成见。章说:“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①② 同上,870 页。
① 《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871 页。② 《汾阳县志例言》,见《戴震全集》一,1991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522 页。③ 同上,488 至490 页。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史馀村》。
此外,还需提及的是,戴震治史的别一领域是谱牒之学。梁启超曾说;“方志,一方之史地。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②与年谱相近的是事略行状、传记、墓志铭、碑传等。今本《戴震集》中有《族支谱序》,行状有《江慎修先生事略状》,传记有《于清端传》等七篇,墓志铭有《裘文达墓志铭》等十篇,碑传序记除《族支谱序》归入族谱家谱外,还有《山阴义庄序》、《汪氏捐立学碑》、《郑学斋记》等共七篇。这些治史篇,《江永事略状》可谓学术史,其余大都可窥见戴震重民利民的史学经济思想,从历史科学去看,有以下特点:一是注重文献考订,钩取史料,辨别真伪,如《族支谱序》写戴氏族的谱系,除指出春秋时宋国有戴、武、宣、庄之族外,明确了戴氏之称,缘于戴族,还表出鲜为人知的史料:唐颜师古注西汉史游《急就篇》:“戴公生公子文,遂称戴氏,是也。”但从前不知道有公子文。尽管如此,戴震对史料的处理仍很慎重,他说:“公子文至护公(按:唐天祐年间人),中间代系遥隔,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也。”①为此修史必求其是的客观态度,曾得罪了戴氏宗族。
二是继承《史记》的传统,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把历史人物写得很生动,例如为《汾州府志》写的《于清端传》即是,其余六篇传记也都有此特色。读后使人看到作者的文学才能。
三是很注重老百姓对历史人物的评述,系史于民。例如为《沧州府志》写的《王廉士(王敏)传》说:“敏狷洁多近义,是以人啧啧喜称道。”
四是为平民百姓立传,如《戴童子圹铭》②。《戴节妇家传》则为“穷巷里曲之妇人女子”立传。传为戴震曾为隆阜卖姜老人立碑,皆此类。
五是从史实出史论,作者随时发表自己的史评见解。例如《万光禄传后序》云:“余读《忠节录》??盖卒之以身死国,非偶然也。”《养浩毛先生传》一开头就说:“戴震曰:士之行,以孝友为先??士之行之可表著,安用舍是而好言奇特为哉!”③在诸多的史传著作中,除了从《江永事略状》看出师生学脉相连外,其余也不难看出作者和史传对象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史作打上了作者的人格烙印,作者也往往从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中汲取了丰富的人格滋养,作为哲学家的戴震直抒石破天惊的胸臆己见,不是有其笔下的中华历史人物铮铮硬骨的人格形象吗?戴震哲学也是从他的历史科学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滋养的。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324 页。① 《族支谱序》,见《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版216 页。
② 魏建功《戴东原年谱》认为,此童子戴震长子,早殇。
③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41 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