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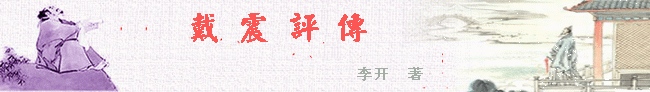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三、戴震自校本和参校殿本《水经注》校
《水经注》,是戴震一生中的大事,旧题汉代桑钦(后人以为三国时人)所著《水经》,至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水经》记述我国河流水道137 条,郦道元补充记述达1252 条,注文较原书多出20 倍,引书达437种,郦道元注完成于公元六世纪初,我国的雕板印刷术大规模兴起尚在十世纪初,前后相距达四百年。目前所知的郦注的第一个刊本是北宋成都学宫刊本,距郦注成书已长达五百余年,这五百余年内郦注本的流传全靠传抄,其间造成的讹错失漏乃至残损,是可以想见的。清代以研究古代文献为职事,且主张经世致用,《水经注》这部经注合一的最古的地理书,很快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戴震校《水经注》,据段玉裁《年谱》记载,开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这一年夏六月,戴震读到胡渭《禹贡锥指》中所用的《水经注》,引起怀疑,便检阅郦注原书。展转推求,方知胡渭致误的原因,正是唐宋间《水经注》在传抄过程中“残阙淆紊,经多误入注内,而注误为经,校者往往以意增改”①。例如“河水”郦注:“北河又东迳莎车国南”,“北河又东南迳温宿国”,戴震指出:“北河”皆当作“枝河”,证据是蒙上文“左右枝水”,故当作“枝河”甚明,而今本作“北河”,是后人所改。又如“济水”,《水经》经文“东至北砾溪南”,郦注:“又东南砾石溪水注之,水出荣阳城西南李泽,东北注于济,世谓之砾石涧,即经所谓砾溪矣。《经》去济水出其南,非也。”据《水经》所云,水在砾溪之南,济水之北有砾溪。又因注文重列为经,济水之南也有个砾溪水注入济水。经文又妄增一“北”字,误入经文的注文增一“南”字,成了北砾溪、南砾溪,胡渭从之,据经文和误入经文的注文云:“上有北砾溪,故此为南砾溪,‘石’字衍(按:指郦注中‘东南砾石溪水’中的那个‘石’字)。”戴震据郦注明言“东北注于济,世谓之砾石涧,即经所谓砾溪矣”一语,说明济水过砾溪之北,即济水之南有一砾溪,不可能有南北两条砾溪,以注文辨正经文,经文也不当云济水“至砾溪南”,恰恰应是“至砾溪北”。类似以上“河水”、“济水”之误,“书中类此者不胜悉数”①。
就全书观之,残缺甚多。戴震据《崇文总目》说:“郦氏书有四十卷,亡其五,今仍作四十卷者,盖后人所分以傅合其卷数。”②《崇文总目》的这个数字是据宋元祐二年(1087)的刊本。宋成都学宫本仅三十卷,元祐本四十卷,显然是据唐宋以来流传的手抄本与刊定本比勘增补而成的。据清代钱曾所见到的陆孟凫影宋本宋版题跋云:“《水经》旧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学宫,元祐二年春,运判孙公始得善本于何圣从(按:即何郯,《宋史》卷322 有传)家,以旧编校之,才三分之一耳,乃与运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镂板,完缺补漏,此旧本凡益编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帐小大,次第先后,咸以何氏本为正。”①① 《书水经注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1 页。
① 《书水经注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2 页。② 同上。
① 见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见《丛书集成初编》0049 号59 页。
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自校《水经注》时,能见到的版本主要有明朱谋讳《水经注笺》本、清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本、康熙五十四年的项絪刊本,及可能存在的抄本,把这些刊定本子和《元和志》、《寰宇记》等书引《水经注》“滹沱河”、“泾水”、“洛水”对照,皆缺失,故戴震怀疑这些古有今无的篇目“或在所亡之五卷内”。
针对以上种种复杂情形,戴震确定其文例,就郦注考定经文,使经注真正分开,别立经文为一卷,对注中前后倒乱不可读者,为之订正,以附于经文后,这样做,目的是还郦注的本来面目,并非为治《水经》,而是治《水经注》。段玉裁曾说,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校录的《水经注》一卷,经别于注,经、注不乱,此卷最为明晰。后来被召入四库馆任纂修,在官修校正《水经注》时,纲领文例不外乎乾隆三十年校录一卷时的办法,仅于讨论字句加详。对一卷本,段玉裁十分珍惜,曾抄写此本,并有自记一篇。
那么,戴震又是用什么办法使经注分开的呢?戴震治学最善于总揽全局,潜心于先发明条例,找到以我驭书的好办法,这正是近代科学重在寻找内在规律的方法。《戴震集》中有《水经郦道元注序》一文,是戴震自校本亦即曲阜孔氏微波榭刊本的序。序文中归纳《水经注》条例,然后循此条例识其大端,理校注文,佐以文献实证,使经文和注文分开。戴震归纳的条例有三:一是经文中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另再举水名,但注文内详及所纳群川,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屡为另行再举之。二是经文叙次名水所经过的州县,仅说出某县,而注文因时代的更迭,旧县或湮或移,固常称“某故城”,而经文没有称“某故城”的。三是经文云“过”,而注文云“迳”。对以上三例,戴震说:“以是推之,虽经、注相淆,而寻求端绪,可俾归条贯。”①以上三条是在自校本序中阐述的,可谓戴震对研究《水经注》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有了这三条,拨开了重重迷雾,打开了郦注的机缄,使经注相混的郦注归于纯粹。梁启超评述这三条说:“此三例戴氏所独创,发蒙振落,其他小节,或袭赵氏,不足为轻重。”②语言是文化的化石,它能揭开历史尘封的秘密。戴震据经文“涪水至小广魏”,而注文云“小广魏即广汉县也”、经文“钟水过魏宁县”,注文云“魏宁,故阳安也,晋太康三年改曰晋宁”指出:《水经》上不逮及汉代,下不及晋初,称广汉为小广魏,称阳安、晋宁(汉永和元年置桂阳郡时称为汉宁)为魏宁,同称“魂”,可见作者魏人,且其书实出一人之手。《旧唐书·艺文志》说是郭璞撰,《新唐志》说是桑钦撰,宋晁公武说桑钦为此书而后人附益,王应麟说郦氏附益,皆非是。更有甚者,《永乐大典》本《水经注》郦道元原序没有提及桑钦,尤可据证。
针对《水经注》的复杂情形,戴震作了篇次序目上的调整。戴震认为,郦注原书是依于地脉,次第井然的,“史言善长(按:郦道元字)好学,广览奇书,故是注之传,或以甚综核,或尚其文词。至于触类引伸,因川源之派别,知山势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阞(按lè地的脉理),取资信非一端。”①后来因为长期致误,即使如有清一代的阎若璩、顾祖禹、胡渭诸子,论述所及,也时有差忒,订正起来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戴震相信,只要根据① 《水经郦道元注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0 页。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243 页。① 《水经郦道元注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0 页。地形的实际走向,实地和文献相结合,是一定能分析胪举的。他说:“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所由致谬之故,昭然可举而正之。”②据这一指导思想,戴震“以某水各自为篇”,即以水名独立成篇,北方的水,以黄河为最大,故领先,然后以黄河以北、黄河以南的水按次排序,“因之得其叙”。南方的水,以长江为最大,故领南方之先,然后先北后南,长江以北、长江以南的水按次排序,也“因之得其叙”,戴震说:“惟以地相连比,篇次不必一还其旧,庶乎川渠缠络有条而不紊焉。”③循此体例,戴震排序得123 水,作为校正全书的篇目次第。至于卷数,《崇文总目》据元祐本分四十卷,清代传本实际上仅三十五卷,而虚分成四十卷,是否合其所分,找不到证据,故戴震乾隆三十年秋私校自定《水经注》时,合为一卷,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浙江金华书院“刊自定《水经注》”时,也是“不分卷数,为十四册”,“以今所存水百二十三,每水一篇,以河、江为纲,按地望先后,分属于河、江左右为次”④。戴震认为,这样不分卷,仅列123 水为目的好处是,可以不再在复杂的卷数合分问题上纠缠不清,“可以撇弃校订,专壹考古善长之书,合二本(按:《水经》经文本和注文本)无遗憾矣”⑤。以上据自校本叙述了戴震对校《水经注》的最重大贡献有三:一是在发现经文和注文相混以后,把握郦注全书,从中概括出离析经、注的三大条例。二是发掘内证,证明《水经》系三国魏一人所著。三是撇开今本四十卷分归旧本四十卷中仅存的三十五卷中去的问题,将实地与文献相结合,以实地水脉为准,列123 水为郦注全书篇目次第,合全书为一卷,或称不分卷。
乾隆三十七年(1772)戴震在浙江金华校注《水经注》而成的合卷本,实际上是戴震自校本的定本,后来的微波榭刻本即据此本。段玉裁《年谱》说,这一年“刊自定《水经注》,至癸已(1773),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都矣。后在都踵成之,今不用校语之本是也。”明谓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在浙东刊出定稿本《水经注》,“在都踵成之”显指继刻此定稿本,亦即由曲阜孔氏刻的“不用校语”的微波榭本。梁启超也据段玉裁的说法理解为“至(乾隆)三十七年刊于浙东”①。“在都踵成之”即使包括对乾隆三十七年槁本作修改,也只是小有改动,决不影响乾隆三十七年已有定稿本的判断。应该说,乾隆三十七年的自校本与三十八年秋进入四库馆后,由戴震领衔,经集体校定的官刻本(即三十九年刊行的武英殿聚珍版本)是有很大区别的。似乎戴震弟子段玉裁为借官刻提高老师身价,《年谱》说:“是年(1774)十月,先生校《水经注》成,恭上”,“高庙褒奖,颁行御制诗六韵??盖先生之受主知深矣。”一般读者也因四库馆校《水经注》由戴震主其事,故往往而言武英殿本为戴震一人所校,而忽视集体的努力。据记载,“戴氏之入四库馆,于馆中请公为后进,戴性又做不肯下人,诸公颇龁之,其所校刊,不尽从也”①。学术争议,面红耳赤,原无足怪,此处告诉我们:殿本是靠集体努力校成的。洪榜《戴先生行状》也说:“先生治是书将卒业,会朝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见段玉裁《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2 页。⑤ 同上。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影印本1985 年242 页。
① 庞鸿书《读水经注小识·叙略》。庞氏系光绪年间进士。
廷开四库全书馆,奉召与为纂修。先生于《永乐大典》散篇内,因得见郦氏《自序》,又获增益数事。馆臣即以是属校正,上其书,诏允刊行焉。”②洪榜也指出是“馆臣”们据戴震的发现,在戴震指导下校成的。但也无可否认,戴震用力最多最勤。梁启超说;“聚珍本(水经注)全列校语,最能表现出先生研索之勤。”戴震《殿本水经注卷首案语》又表明,虽戴氏用力最勤,仍以“臣等谨案”的名义进呈,与洪榜说一致,再次表明此官书赖群臣之力③。四库馆戴震等人校《水经注》,所用的体例、方法当然是一循戴震发现的那三大条例。段玉裁说:“得此三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讹,俾言地理者有最适于用之书。”④或许是戴震已有私校定本,更有这三件武器之故,才取得在四库馆主校该书的资格。
戴震等人的殿校本之所以取得郦学史上引人注目的成就,除用戴震三体例外,在资料和版本依据上则用了《永乐大典》本和可能引用了赵一清校注本的抄本。《永乐大典》修于明初,所据底本出于朝廷内库藏本,这时的藏本无非是宋、元的遗物。就《水经注》而言,大典本无非综合了宋、元的刊本、抄本而成。大典本的突出优点是有郦氏四百七十七字的原序,为他本多缺佚。此外,大典本也确有其内容上的特点。据四库馆谁校某书谁写定提要的定规,且与微波榭本《水经注》戴序、后记相对照多相同文字,并文中详述戴氏离析经注的三大体例看,“《水经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条的提要为戴震手笔无疑。另外两篇《水经注集释订讹》(清沈炳巽撰)和《水经注释》(清赵一清撰)的提要至少是戴震等人校《水经注》的同人的手笔。据此,戴震的《水经注提要》曾总结殿校本据大典本取得的成就:“凡补其阙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则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以致使郦注“三四百年之疑窦,一旦旷若发蒙。”戴震还指出,殿本因郦道元足迹未历塞外、江南,传闻尤多失实,故校注《水经注》时,又据实地考察的第一手材料用来“抉摘舛谬”,以实测所得之“脉络、曲折之详”订正讹误。正因为有优越的文献条件和凭国家力量所得的实测资料,使殿校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殿本以后的版本(都是私校本)尽管疏证上可能更加详细,但校勘上始终没有超出殿校本的水平。
殿校本在使用国家藏本大典本的资料上,尤其是采用乾隆帝命使官员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上,都不可能得而私。虽出戴震手笔,但终究是以国家书目名义出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的“以《永乐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条参校,”也不可能是在为戴震一人树碑列传。
戴震等人的殿校本所据的另一底本,可能是由浙江巡抚采进的清赵一清《水经注释》四十卷和《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后者是赵为订正明朱谋讳的《水经注笺》而写的。在戴自校本和殿本之前,朱笺本是除大典本以外最好的注本,被顾炎武称为“三百年来一部书”,戴校本和殿本都以朱笺本为重要依据。赵注本也以朱笺本为依据,赵注本卷首列参校版本多达二十九种,赵还说:“以上诸本予悉取之与明南州朱谋玮中尉笺相参证,录其长而舍其短。”赵的《刊误》十二卷正是研究朱笺的收获。殿校本与赵注本有相近之处,但这相近,个中原因有殿校本与赵注本同以朱笺本为依据之故,当然不② 见赵玉新点校本《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256 页。
③ 参见《戴震全集》一,清华大学1991 年版256 页。
④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473 页。
排斥可能直接引用赵注本,一说梁玉绳校刊赵书时引用了殿本以正之,故殿本、赵本相同处甚多。乾隆御制诗褒奖引用他的《热河考》、《滦河考》中的实测资料的殿本时说:“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中尉”即指朱谋玮,可见乾隆帝也是把殿本看作继朱笺本的。至于有可能直接引录赵注本,殿本作为国家校定的官书刻本,在体例上应是允许的。
十分重要的是,戴震主其事的殿校本可能引用赵注本时,毕竟只是用其个别形态的具体说法和资料,而涉及全书主旨大纲时,恰恰是用主事者戴震的校注《水经注》三体例。这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讲得很清楚,与微波榭本戴说的体例毫无二致。而赵注本体例之所以未被采用,除主事者戴震已有成熟并成功使用的体例外,赵注体例稍逊一筹也是原因。赵注本吸收全祖望七校本《水经注》成果,也是人所共知的。赵一清与全祖望本同乡挚友。相约同治《水经注》,朝夕商榷,全曾为赵书作序,赵书引全说甚多,两书相符者十之八九。全祖望除校勘和疏证上有不少功绩外,在区分经注上也有成就,他提出郦注原系双行夹写,注中有注,今混作大写,几不可辨。这一说法不管是全氏本人的发现,还是他先世的旧闻(全氏先祖全元立、全天叙、全吾麒等都校过郦注),都是值得称道的创见。全祖望七校本四十卷,乾隆十七年(1752)完稿于广东,但未等刻书全已死。后来遗著散佚。百年后,其同乡后学王艧轩才开始整理,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由薛福成从董觉轩之请而刻印之,故全书最先成而最晚出。赵校本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但一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才由毕沉从赵一清之子赵载元处购得原稿,刻印于开封,赵书始行于世。赵一清不仅在个别体例上引用全祖望,而且体例上也引用全氏的说法,在赵注本上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小字分别书写之,而又使语不相杂而文仍相属,以证明郦注与注中之注离析的正确。赵氏的尝试,基本上成功。但赵承全祖望,离析经、注和注中之注都不过以文义相属为文例,以大字小字分写之为区分后的标记,都没有找到象戴震三体例那样的带有区别性特征的体例,因而可以说全、赵的区分经注,区分郦注和注中之注的体例是软体例,戴的三体例是硬体例。故殿校本的基本体例未尝用全、赵而一仍戴氏自校本的做法。
殿校本和赵注本体例上大别而细节和个别说法上可能甚近,殿校本与戴震自校本体例上一致而细节和个别说法上甚远。这样就发生了三对矛盾关系:戴自校本和殿校本、戴自校本和赵注本、殿校本和赵注本。学术史上一度似乎没有具体研究这三对关系,有人却只是简单地将殿校本说成戴校本,然后又视殿校本近同于赵注本,因而说戴参校本殿本是抄袭赵注本①,形成了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聚论纷坛,莫衷一是。如前所说,殿校本非戴一人之功,非戴一人所校,无论功过都轮不上戴震一个人。而戴自校本与殿校本虽校书体例近同,但细节区别甚大,例如:在卷次上,殿本仍分40 卷,自校本根本不分卷。在校勘语上,殿本全载校勘语,说明经、注离析之由,戴校本不载校勘语,仅将经文与注文离析。在序跋上,殿本无,戴震手笔的《水经注》四库提要记述了殿本依据、体例、改正情况、引用资料等,私校① 起初是魏源、张穆怀疑戴震抄窃赵书,至清末杨守敬(惺吾)(1839—1915)便在《水经图注》、《水经注疏》、《水经注要删》中据赵、戴校本的相同之处,认为戴窃赵,铸成公案。晚近孟森(心史)、王国维也分别在《水经注研究》、《水经注笺》中据杨说指斥戴震窃赵。
本有序、后记,还有孔继涵序。在版本上,殿本是官刻本,私校本有自刊本(今已不传),正式刻本有微波榭本,是为民间刻本。殿本和微波榭本同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印。
殿校本和赵注本,作为官校本,前者在体例上完全可引用后者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戴震手笔或其殿校本同人手笔的赵注本《四库总目提要》,高度评价了赵注本的成就。既蓄意抄袭对方,又去高度评价对方,似乎也是不伦类的。戴震等人不仅将赵注本收入了《四库全书》,还对赵引用全祖望不成熟的体例一事作了长篇评述,肯定了赵“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建树,说:“一清此书,殆亦类此,但使正文旁义,条理分明,是亦道元之功臣矣。”最后还说:“旁引博征,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①最后一句,把赵注本置于戴震自校本之上了,甚至视为高出殿校本。
赵注本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付印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戴、赵公案,不仅说殿本戴袭赵,还说梁玉绳兄弟校勘赵书交毕沅付刻时又袭戴。至于全、赵间的麻烦,说毕沅做湖北总督时,索观赵的旧稿,赵的儿子其时在湖北做官,以巨资购买全祖望校本应付毕沅,故今传赵注本实际上是全祖望的。而林颐山则又斥现行全祖望本伪出,不仅袭赵,兼又袭戴,林说为王先谦所信,王的著名的郦注合校本竟将全祖望七校本排斥在外。如此等等。梁启超曾以各自“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说调停这桩公案①。胡适起初信从戴袭赵说,后来化了二十多年的功夫反复研究《水经注》的各种版本,最后提出,这根本不是什么抄袭,而是“学术史上所谓独立研究,而先后约略同时得到同样结果的一种好例子”②。胡适为戴震辨诬,也是为“要给自己一点严格的方法上的训练”③,竟写了十大集手稿。
胡适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戴震根本就没有见过赵一清本。乾隆开四库馆时,校书分东西两院,各成门户,互不相通,戴震以举人入东院,而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被浙江进呈后置西院,因而戴震不可能见到赵注本,且胡适通过比较,找到了许多有关戴震未见到赵注本的证据,例如书中有许多常识性错误,赵书无而殿本有;赵书指出朱谋玮本的错误,而殿本仍因袭之;赵氏据孙潜校本增补《水经注》卷十八“渭水中篇”的缺页共418 字,而戴震的殿本仍用《太平御览》等书中引用过的材料为据,辑补成113 字。 1944年,胡适还写成《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1984 年7 月修改,1949 年1 月10 日改定),为百年大案《水经注》公案翻案,胡适写道:这十组证据都是赵氏书里的特别优点,而都是戴氏书里全没有的。这十组或是校改了毫无可疑的错误,或是解决了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都是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平日“寐寐求之”的好宝贝。专治《水经注》的人,见了这些好宝贝,若不采取,那就真成了“如入宝山空手回”的笨汉了。
这就是说,这十组都是偷书的人决不肯不偷的,都是抄袭的人决不肯放过的。若单举一件两件,也许还有偶然遗漏的可能。多到了几十件,其中并且有几百字或几千字写的校语,①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611 页上。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影印本243 页② 《胡适手稿》第一集卷四,台北胡适纪念馆1960 年2 月影印本。
③ 《致洪业信》一文,《胡适手稿》第六集上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9 年8 月影印。决不会被《水经注》专门学者忽略或遗漏的。
况且这十组的校订,都可校正戴氏校本里一些无疑的错误,都可以补足他校本里许多无疑的漏洞。戴氏若见了赵氏的书,决不会放过这些最明白无疑的考订,决不会保存他自己的许多大错误、大漏洞,留作后人的笑柄。所以这十组赵有而戴无,赵优而戴劣的校订,都可以证明戴氏没有得见赵氏的校本。胡适将殿校本归于戴震一人,取较为通行的看法,当然有可商榷之处。又考证出戴震主校殿校本时从未见过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及《水经注笺刊误》,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但胡适的结论:戴震决没有抄袭赵一清本,是可取的,也是可信的。
今谓戴震有自校定本《水经注》,参较殿本大例方法完全是戴的发明创造及其应用,小例可能引赵。引赵部分有以朱谋玮注笺本为基础,实戴、赵同参用朱笺本,也有可能直接引用赵一清的,又为官校殿本体例所允许。抄袭之说,应属无据。蔡尚思说:“戴震的被看做剽窃却似冤枉。据天津藏的一个赵一清校本的抄本,可以证明在乾隆的殿本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人的研究的成果都有,实无所谓谁是剽窃者。”①① 《胡适手稿》第一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6 年2 月影印本。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