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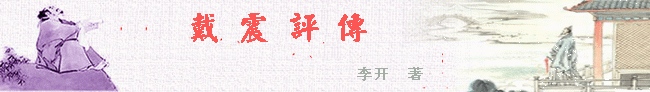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五、语言解释中的今音学
今音学研究唐宋以后的中古音,它以《切韵》系韵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如果说,戴震研究上古音的目的,是以古声纽,特别是古韵部说明上古的语言文字,以完整的上古音体系抉发语言文字的奥妙,从而获得通道的古代语言学范畴内的古音解释系统,那么,戴震研究今音学的直接目的还是为古音学服务。作为音韵学的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立而完整的体系,它既要研究古音学,又要研究今音学。在戴震的解释学体系中,“古音学——语言文字——辞,上古文献——道”是一解释系统,“今音学——古音学”是又一解释系统。显然,今音学和上古语言文学、上古文献上无直接联系的,如果说有间接联系,也务必通过古音学这一中介环节。
在戴震之前的明末清初,今音学研究几乎是空白,那时流行的韵书无非是元代阴时夫编的《韵府群玉》,许多人连《广韵》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乾嘉时代,音韵学家们的主要精力大都集中在上古音,只有江永戴震和钱大听对今音学有所成就,江、戴之后,几乎又度越了一百多年的空白,至清末陈澧(1810—1882)系联《广韵》的反切上字和下字,找到了中古的声类和韵类(40 声类311 韵类),对《广韵》的前身《切韵》音系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江永曾著《四声切韵表》,用等韵学原理研究《切韵》音系和上古音,他说:“依古二百六韵,条分缕析,别其音呼等第。”①戴震中古音研究亦继承江永,用等韵审音法。他说:“郑樵本《七音风韵鉴》为内外转图。及元刘鉴《切韵指南》皆以音声洪、细,别之一二三四等列,故称等韵;各等又分开口呼、合口呼,即外声、内声。??其说虽后人新立,而二百六韵之谱,实以此审定部分。”又说:“就一类分之为平上去入,又分之为内声外声,又分之为一二三四等列,虽同声同等,而轻重、舒促必严办;此隋唐撰韵之法也。”②戴震既以等韵审音研究上古音,研究中古音当然更寓不开用等韵审音之法了。他曾详论各韵的等呼,他说:“《广韵》上声二腫、湩字下云:‘此是冬字上声。’盖昔人论韵,审其洪细,为一二三四等列,如平声二冬、十一模、十五灰、二十三魂、二十六桓,全韵皆内声一等。??欣韵、迄韵并三等,惟上声隐韵、去声焮韵兼二等三等。”③戴震的意思是,等韵虽后人所创而日臻完善,但《切韵》时代已分平上去入(上古异平同入),已分四等。此为隋唐人撰音之法,故研究《切韵》可借用等韵审辨之。等的概念在戴震那里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被用来分析汉语语音,分析上古音和切韵音系都用到了等,等的运用在江永、戴震手中已越出了等韵学范围。戴震关于《切韵》时代分出四声的观点,被段玉裁接受。段氏认为,周秦汉初,声调只有平上入三种,没有去声,直到魏晋才产生去声而成四声①。关于等韵审辨法,近人黄侃曾评“等韵之弊,在于破碎;音之出口,不过开、合;开、合之类,各有洪、细,其大齐惟四而已。而等韵分开口、合口各为四等(按:① 江永《四声切韵表·凡例》。
② 戴震《声韵考》卷二,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③ 同上。
① 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一·古四声说》。
指江、戴主开合,再各分四等共八等)”②。黄侃认为,这是缘见《广韵》分韵繁多,不明所以,“因创四等之说以济其穷”③。张世禄指出,宋元时代的等韵与明清的等韵不同,宋元可分八等而明清只有开齐合撮四等,黄侃(包括章太炎)指责戴震分宋元八等为“破碎”是没有道理的④。按张说,戴震以等韵审中古音精细入微,且是从宋元语言的实际情形出发的,体现了戴震以审音为演绎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和经验的依据,其演绎是在归纳而成音理以后的演绎,从而使中古音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密合,与用等韵究上古音的情形不同。应当指出的是,章太炎、黄侃认为《广韵》存有古音,却肇始于戴震的今音学。戴震曾有以下著名论断:隋唐二百六韵,据当时之音,撰为定本,虽未考古音,不无合于今,大戾于古。然别立四江,以次东冬钟后,殆有见于古用韵之文,江归东冬钟,不入阳唐,故特表一目,不附东冬钟韵内者,今音显然不同,不可没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杂成一韵也。不次阳唐后者,撰韵时以可通用时附近,不以今音之近似而紊淆古音也。①音之流变有古今,而声类大限无古今。后来章太炎据此又说:东冬,之脂之分,皆由古音不同,非必唐音有异③。黄侃亦笃信戴、章之说,从《广韵》求出古本韵32 个(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古韵二十八部)和古本声19 纽。从戴震及章、黄《广韵》存古音之说看,戴震首创此说在思想方法上除使今音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外,今音学为古音学服务的目的十分明确。此外,既然以中古等韵八等审析《广韵》是可取的,章、黄的批评难以成立,则以等韵同时审析留存于《广韵》中的上古音,除前面已分析其思想方法上因主审音而必然循此以外,在具体实施中也确有其自然成功的因子。但不管怎样,以后代等韵审析上古音总是有较大误差的。值得注意的是,戴震能以宋元等韵而不象章、黄以明清等韵那样审析中古音(章、黄也是重审音的),却不能以上古音理审析上古音(如前所说,这是无法做到的),前者所以能够实施的客观原因是,明清四等与宋元八等有较近的联系,文献较上古详备,等等。从其内在的科学逻辑和思想方法去看,不能不说是戴氏的天才突破,以致达到了包括章、黄都无法理解的科学境界,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分析审验,完全证明戴震的审音之功达到了较为圆熟的境界,或者说戴氏对中古音的审音研究已从必然中获得了部分自由。但严格地说,宋元的八等韵还不是隋唐音,故隋陆法言《切韵》音系的研究仍可深入。陈澧曾说:“隋以前之音异于唐季以后,又钱、戴二君所未及详也。”①这种情形,在逻辑上又类似于“以上古音理审析上古音是悖论”一样,是无法成立的,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以宋元音理审《切韵》音系在逻辑上作了多大的迫近,在求取近似值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今音学的具体成就上,戴震著《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②,现代人② 《与人论小学书》,见《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 年版153 页。③ 见《黄侃论学杂著》153 页。
④ 张世禄《广韵研究》,商务国学丛书本131 页。
① 戴震《声韵考》卷三,第七页,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② 同上,卷二,第五页。
③ 章炳麟《音理论》自注。
① 陈澧《切韵考·序》② 载《声韵考》卷二。
谈《广韵》的韵目,大都依从戴震的考定。戴氏考定《广韵》时不过以明本楝亭五种本和泽存堂为据。原为日本藏《矩宋广韵》问世后③,足证戴氏考定之精④。戴震的考征取得的主要成就有:戴氏用表的形式将206 韵按四声排定,由表一看即知哪些韵有入声,哪些没有,那些韵有平声,上声,哪些没有,令人一目了然。试将戴震的考定与《广韵》的原韵次对照,就可发现,戴震订正了若干韵次。戴氏对206 韵的同用、独用据前人的研究和他本人的研究一一作了考订。由于以等韵审音,戴氏对各韵的等呼一一进行分析,他这样做,等于给《广韵》添加了一项原书所无的内容,对贯通《广韵》和等韵学极有作用。此外,戴震还考订了《广韵》的声类(大的韵类)的异同。总的说,戴震的今音学也是自成体系的,他的《广韵》研究形成了以206 韵为研究层次和研究对象的今音学体系,它既是音韵学中独立的自成体系的门类学科,又是研究者本人用以服务于古音学研究的学科。作为独立的成体系的学科,由于戴氏还仅以206 韵为对象层次,往后的研究有必要改以更深入一层的层次:以反切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清末陈澧完成的。
无论是因声求义、转语,还是古音学、今音学的研究,都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中的独立学科音韵学的内容,但从其间接的或者说深层的作用看,都是由语言文字的途径最终通道的,戴震也正是这样使用音韵学的有关内容的。例如《中庸补注》作了这样的应用:《中庸》“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戴震补注:“而,如若,语之转??人之为道若远人,不可谓之道。素隐行怪之非道,明矣。”①《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戴震补注:“蒲卢二字迭韵,形容之辞,盖古有是语。《夏小正》‘雉入于海为蜃’,说曰:‘蜃也者,蒲卢也,与蜾赢同名。’蒲卢取义可推而知。政虽利民,不得其人;皆适以病民,有随人转变之义。然则蒲卢,蜾赢也。夫子答哀公问政,止于此。下文承夫子论为政,而推广之,以论学。”
这是以音韵学(结合词义诠释等)识辞通道的个别实例,在这“个别”
的背后,却是一片广袤深邃的古音学和今音学的科学系统。戴震引用孔子以蒲卢释政治之语,曾对友人程瑶田讲述过,瑶田在《果裸转语记》中又引用戴说,并云:“秦晋凡物树稼早成熟谓之旋,燕齐之间谓之抠榆。昔吾友戴东原语余云,夫政也者蒲卢也。蒲卢转变捷速之谓,然则抠榆即蒲卢之转,戴氏之云与方言合矣。”②程瑶田的叙述,进一步证实戴震是在以转语实例释政以通道,戴震的语言学是一种语言解释哲学。
③ 《矩宋广韵》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闽中建宁府黄三八部书铺所刊。国内久佚,光绪十五年(1889)从日本收得。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影印本。
④ 对照戴震《独用同用表》和《矩宋广韵》,仅以下不同:戴:艳( 同用),《矩》:艳( ,酽同用)。戴:陷(??同用),《矩》:陷(??、梵同用)。戴:酽(梵同用)。从音理看,戴的考证反而更合理。陷(开口二等去声)与??(开二去)同用,不与梵(合三去)同用是合理的。酽(开三去)与梵(合三去)同用是合理的。《矩》以陷(开二去)与梵(合三去)同用尤不合理,而戴以酽(开三去)梵(合三去)同用是合理的。
① 《戴震全集》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125 至126 页。
① 《戴震全集》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133 至134 页。
② 程瑶田《果裸转语记》,见《安徽丛书》第二集。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