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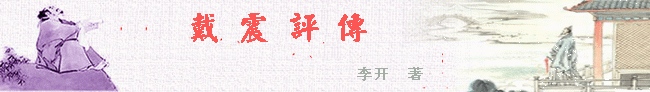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六、语言解释中的方言研究
方言,不仅对了解现实的语言状况有意义,尤其对了解古代的语言文化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现实方言是古代方国的绝代语,它是古代语言和文化的化石,章炳麟曾说:“今者音韵虽宜一致,而殊言别语终合葆存。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学,则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皇忍拨弃之为?彼以今语为非文言者,岂方言不合于文,顾士大夫自不识字耳。”①不论是以古证今,还是以今证古,都离不开方言,戴震力主“以词通道,”是不能不重视方言研究的。
戴震方言研究,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汉扬雄《方言》的研究,著《方言疏证》。另一部分模仿《方言》体例,续补《方言》,著《续方言》,今存手稿二卷。
戴震研究《方言》,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最初是通过《方言》与《说文》的比较互相补释,以致段玉裁借用戴震分写《方言》于《说文》之上的本子作《说文段注》的著述用参考书②。著《方言疏证》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秋进入四库馆以后的事。
《方言》自晋郭璞以后己不受重视,研究它的人很少。戴震从复兴古道的旨趣出发,有感于“宋元以来,六书故训不讲,故鲜能知其精核,加以讹舛相承,几不可通”,又恰好从《永乐大典》内得善本,“因广搜群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参订”,改正了281 个错字,补上了脱字27 个,删去衍字17 个,逐条详证,使《方言》训诂之学得以恢复本来面目,戴震疏证《方言》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俾治经读史博涉古文词者,得以考焉”③。以汉代训诂之书通经典文字,由语言文字而创通古道,完成识字达辞通道的一个全过程。然而识字而明语言文字之义,也是如同古音学、今音学须有其体系那样,也得作系统研究而自成专学的。戴震的《方言疏证》是研究扬雄《方言》的专书,也是方言学的专著。作为对扬雄《方言》的研究,戴震的《方言疏证》是清人的第一个校本,后来卢文弨“因以考戴氏之书,觉其当增正者尚有也”,①著《重校方言》,是清人的第二个校本。其后还有刘台拱的《方言校补》,钱绎《方言笺疏》等。
作为对汉代方言学的研究,戴震取得了那些成就呢?首先,戴震考订《方言》为汉扬雄所著无疑。扬雄著《方言》,本来并没有什么异议。只是到了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出《方言》非雄所作,理由有三条,一是《汉书。艺文志》和扬雄本传未提到此书。二是扬雄给刘歆的信里谈到严君平这个人,君平康姓“庄”,后人因避汉明帝刘庄的讳,始改为“严”,扬雄的《法言》并不讳“庄”字,可见扬雄给刘歆的谈及他著《方言》的信大可怀疑(信中讳“庄”为“严”,改庄君平为严君平)。三是刘歆给扬雄索取《方言》的信中云:“歆先君(指刘向)数为孝成皇帝言”,这意味着写此信时汉成帝已去世,否则不会称“孝”某帝,但此信的前面又说“汉成帝时”,① 《大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论汉字统一会》。
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9 页。
③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02 页。
① 卢文弨《重校方言·序》。
前后抵梧,可见刘歆给扬雄索要《方言》的信也大可怀疑。既然史书本传都未提及扬雄著《方言》,又刘歆,扬雄议及《方言》的往来书信颇为可疑,则扬雄为《方言》作者就很值得怀疑了。对洪迈提出的三点貌似有理的说法,戴震一一作了批驳。扬雄作品不见于《汉书》传的,不只是《方言》一书,其他一些作品也有为本传所不载的,本传不载及不能说明扬雄未著《方言》。本传不载及的原因,戴震认为,刘歆向扬雄索要这本书稿时,此书尚未完稿,扬雄亦未交出,故刘歆的《七略》未录此书,《汉书,艺文志》也因之不录此书。至于扬雄的信改庄君平为严君平,为后人窜改本文时造成,不能据此构成扬雄答刘歆的信是造假的说法。又刘歆信前面提到“汉成帝时”的那一段,为他人所加,但加进这段介绍性质的文字的人又很粗心,竟把刘歆在王莽当政时的信挪到汉成帝时去了,戴震认为,洪迈不加审执,洪“以疑古,疏谬甚矣”①。戴震的考证足以成为定论。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曾总结历史上的这桩公案,基本上肯定了戴震的看法。他说:“《方言》是中国的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它的著者是不是扬雄,洪迈和戴震有正相反的说法,后来卢文绍、钱绎、王先谦都赞成戴说,认为《方言》是扬雄所作。”②戴震取得的第二项成就,可谓对《方言》卷数分合的考订。罗常培序中提到的应劭在集解《汉书》时,曾说扬雄著《方言》,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据扬雄《答刘歆书》,译述扬雄著《方言》事,并说《方言》共有九千字。戴震著《方言疏证》时,据郭璞《方言注》统计有一万一千九百多字,增加了近三千字。对这个增加的字数,戴震设想:“岂劭所见与郭璞所注,使本微有异同欤?”③戴震的这一设想是有道理的,思想方法上是一种经验性的逻辑推证。文化史上凡一部书有了权威的注本后,就不大可能再有增减,《方言》的增字一般说只能在郭璞权威的《方言注》产生之前,应劭所见的九千字本子可能是扬雄的原本或字数近于原本的其他本子,郭璞见到的一万余字的本子只能是扬雄死后至郭璞作注前这段时间内后人增字的本子。戴震对郭注本字数的统计及由此对增字本的设想,既是经验归纳的,又是逻辑推证的,亦为后世研究《方言》的学者所肯定。
关于《方言》的卷数,刘歆向扬雄索要该书时的信及扬雄的复信都说十五卷,郭璞《方言注》序也说“三五之属”(3X5),但《隋书.经籍志》讲方言十三卷,《旧唐书》也讲“《别国方言》十三卷”,今天所见到的《方言》也是十三卷。到底是十五还是十三?戴震说:“其并十五为十三,在璞注后,隋以前矣。”①从今本《方言》十三卷看,后两卷与前十一卷的体例大别,收词猛增,严然非同出一人之手,极可能最后两卷仅为提纲,扬雄未及铸就就去世了,后来有人补上一些方言单词汇集,但未加详述方言及有关方言词的来龙去脉,至于卷数,据当代语言学家何九盈的推断说:“我以戴震的《方言疏证》为根据作了一个统计,全书收词条658 个,那么,十二、十三卷的词条占全书词条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十八。因此,我怀疑原书是由十五卷变为十三卷,可能这后两卷本是分四卷的,经过合并,就使全书少了两卷。”① 戴震《方言疏证》卷十五,万有文库本341 页。
② 罗常培《周祖谟方言校笺及通检序文》,载周祖谟《方言校笺及通检》,科学出版社1956 年版1 页。③ 《方言疏证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01 页。① 《方言疏证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01 页。②戴震“并十五为十三”的看法,与当代学者何九盈的推断也是一致的。除了对《方言》作者和书卷字数的鉴定外,《方言疏证》为研究汉代方言学奠定了基础。由于郭璞《方言注》以后是空白,故直接关于《方言》的研究资料无可征引,戴震的做法是,以《方言》夹注郭注为条目,引古代字书及有关文献疏证之,以明《方言》及郭注中有关词语的意义,用法、音义联系。有关音义联系部分,当然是以戴氏的音韵学说和转语说为基础的。例:《方言》卷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郭注:党,朗也,解寐貌),或日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戴震注:“知读为智。《广雅》‘党、晓、哲,智也’义本此。知,古智字。孙绰《游天台山赋》:‘近智以守,见而不之,之者以路绝而莫晓。’李善注云:‘之,往也。假有之者,以其路断绝莫之能晓也。《方言》日,晓,知也。’此所引乃如字,读与《广雅》异。注内‘党,朗’迭韵字也。《广韵》作‘ ,朗’,云火光宽明。”①由上例可知,戴震的研究法当然是纯语言学注释学的研究,戴氏的疏证主要针对《方言》条目,也涉及郭注。这一条的疏证,把《方言》中的“知”字按《广雅》说成“智”的古字,但又按李善注孙绰文将“知”说成“知道”的“知”,戴震并没有作结论,两存之供读者思考。对郭注内“党,朗”的说明,戴氏疏证指出为迭韵字,那完全是据戴氏本人熟谙的古音学。今谓“党”:上古端纽阳韵。“朗”字上古来纽阳韵。故两字迭韵。且按音转之理,两字的纽是旁转字。戴震的疏证奠定了解释、注疏《方言》的基本条例和格局,后来请儒卢文弨、刘台拱、钱绎的注疏都在这一格局的基础上作申发和补充。事实上不仅是对《方言》的注释,戴氏的《方言疏证》连同他的《屈原赋注》、《考工记图注》、《诗补传》等注释著作在内,奠定了清代朴学中的注释学的基础,或者说奠定了解释学中的文本解释的基础,使我国古代的注释学继《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郦道元《水经注》、《三国志》裴松之注、《文选》李善注四大名注释著作以后,进入了一个全面复兴和昌盛的时代。清代的注释学大发展,是以戴震创其业的。仍以以上举出的《方言》第一条为例,试将钱绎的笺疏和戴的疏证相比较,钱氏的笺疏仍是戴震奠定的格局,只不过引书大量增加,凡与该条有关的内容悉以存此,信息密度猛增。以“知”是“智”的古字这一点而论,戴震的疏证仅引《广雅》说明之,可是钱绎的《方言笺疏》除引《广雅》以外,又引《苟子·正名篇》、《白虎通义》、《释名》,钱的结论是“智与知声近义同”①。可谓多方比证,曲尽其意,可说比戴震的疏证更为具体详尽,但其注释学的基本思想,乃至注释的基本体例,都是戴震发其端的。
从语言学思想而言,《方言》本身是以西汉为时限的共时情状下语言性质为区别的,例如条目中有共通语、凡语、凡通语、某地方国俗语的区别。戴震的疏证引历代历时情状下的书证以证共时态的不同性质的言语说法,实际上是在从历史文献中寻找《方言》条目逐渐形成汉民族共通语的轨迹。这与扬雄著《方言》的目的是一致的。扬雄说:“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扬雄著《方②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吏》河南人民出版社38 页。另据何统计,十二卷102 条,十三卷149 条,共251 条。
① 戴震《方言疏证》卷一。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上册1 页。
① 钱绎《方言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 页。
言》的目的是存此方俗语,并以通语释之,以看出方俗语向通语的转变并促进这种转变,戴震引文献疏证各词语的用法,正好找出其向共通语转变和作共通语使用的轨迹。语言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戴震疏证的思路是把扬雄所作的共时语言的记录转变成历时语言的研究,转变成历史语言学。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戴震对《方言》的疏证恰恰是从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文献特征方面在客观上起到证实汉民族的存在、证实汉民族处于巩固和发展过程的作用。我们似乎不能以此推断在乾嘉年间戴震还有什么明末清初的知识界的那种民族意识,但他弘扬传统文化的赤忱,以中华传统文化、汉语汉字梳释古代文献的苦心经营,指点民族文化、语言的融合的历史过程中的费神苦功,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也不能不使人感触到他的强烈的汉语汉字文化的主体意识,而这种文化主体意识,又不能说与民族的潜意识绝然无关的,只不过这时的民族意识已不是民族的对立,而是趋于民族的和解和交融时期的产物,试举戴震立足于共通语释方言之例:《方言》卷一“咺、唏、、怛,痛也。凡哀注而不止日咺,哀而不泣日唏,于方则楚言哀日唏,燕之外鄙,朝鲜冽水之间少儿泣而不止日咺,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人少儿泣而不止谓之,哭极音绝亦谓之,平原谓啼极无声谓之,楚谓之噭咷,齐宋之间谓之啥,或谓之惄。”戴震疏证:“案:《春秋》成公十六年《公羊传》‘悕矣’何休注云:‘悕,悲也。’宋玉《风赋》:‘中心惨恒。’李陵《答苏武书》:祗令人增忉怛耳。’潘岳《寡妇赋》:‘怛惊悟兮无闻。’稽康《幽愤诗》:‘怛若创痏。’李善注并引《方言》‘怛,痛也。’枚乘《七发》‘嘘唏烦醒’注引《方言》‘哀而不泣日唏’。《说文》:‘哀痛不泣日唏,朝鲜谓儿泣不止日唏,秦晋曰咺,楚曰噭咷,宋齐曰喑。’盖本《方言》而小异其辞。《广雅》:‘ 、怛、惄,痛也。欷,,喨,悲也。’义皆本此。唏与悕、欷,哴与喨,古通用。”
今谓《春秋经》、《公羊传》、何休注、宋玉《风赋》、李陵《答苏武书》皆后世公认的用共通语写成的文献,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辉煌部分,是共同的财富。至于潘岳、稽康、李善注则更后,更是用共通语写成的文献了。《说文》是古代的规范词典,其目的是要使语言规范化的。如此看来,戴震首创以后世文献疏证《方言》,其立足点只能是以共通语释方言的,以华夏各族的共同文化财富释古代语言典籍的,而这些,客观上都反映了戴震以汉语言文字为其表达的共通语观念,及其以共通语为其主要特征之一的汉民族观念。
《方言》是古代语言学的著作,戴震如何把它用于“以词通道”呢?如前所说,戴震在序中就已指出可运用《方言》考经史古文辞。就以戴震的疏证本身而言,是用经史子集注释《方言》,如用注释学中的反推法看,又是以《方言》词语解释经史子集,如上例,正是用《方言》卷一中的那个条目来解释《春秋经》、《公羊传·成公十六年》、宋玉《风赋》和李陵《答苏武书》等等,只不过是以注释《方言》为基点的。直接引用《方言》注释古代典籍以求通道的,亦不乏其例。例:《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予之峨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① 《方言疏证》上册卷一,商务版万有文库本8 至9 页。
戴震注:“琢,塑(按:毁谤义)也。楚以南谓之诼。《方言》云。”②戴震用《方言》贯通了一个“诼”字,指出句意为“泛云不察民心,以谓君之不己察,而毁谮得行也”,再进一步指出造成“不己察”、“毁谮得行”的原因是屈原本人“原以正道事乱世之君,固易致疏远矣”①。
戴震不仅用《方言》诠释古代文献以求道,而且用来阐释他本人的哲学思想,具体做法是引用扬雄,以使自己的表达更为明确具体,使哲学思想更能言尽其意,更能为人所理解到切实之处。例:《孟子字义疏证.理》:“盖方其静也,未感于物,其血气心知,湛然无有失,故曰天之性。”“湛然”这一描摹“血气心知”的词语戴自注:“扬雄《方言》曰:‘湛,安也。’郭璞注云:‘湛然,安貌。’”
戴震还著有《续方言》。 1928 年冬刘半农在北京偶然发现该书手稿。
今见载于安徽丛书《戴东原先生全集》中,共二卷。戴震《续方言》与扬雄《方言》并不一致。《方言》记述活的口语,《续方言》从古文献中搜录。有采自何休《公羊传》注(“肪”至“于诸”共29 条),汉许慎《说文解字》(“ ”至“喌”共124 条),戴震还将这些条目和扬雄《方言》作比较,指出其中已为扬雄《方言》所收的条目。还有采自《苟子》和杨倞注的条目(衢道”至“聘,问也”条共20 条,其中8 条出自杨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引《苟子.正名》和《修身》中七条都是讲正名、同异等逻辑问题的,虽与体例不合,但可看出戴震将古代逻辑问题与语言学问题合而观之的学术思想,颇值得重视。此外,还有引刘熙《释名》的条目(惠”至“掌”38 条),戴震说:“从‘惠’已下至‘掌’皆刘成国所云也。”《续方言》全书引据的条目未分类,引文均按原书次序。
戴震著《续方言》,据罗常培的研究,“约在乾隆二十年(1755)专攻《方言》之后,三十八年(1773)人四库馆之前”①。罗氏所说的“专攻《方言》”,就是指戴震将《方言》分写于《说文》之上作研究用。在戴氏著《续方言》之前,有杭世骏(1696—1733)著《续方言》。杭著体大思精,仿《尔雅》义类排比类次,引书达数十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近时小学家犹最有根柢者也。”据罗的研究,“杭书之成,必在乾隆八年(1743)以前”,这样,至少比戴氏早十几年。和《水经注》公案颇有点相似,杭、戴二书同名都从文献集方言,许多条目也相同,或许戴著《续方言》鲜为人知,才幸免构案的吧!罗常培说过,戴震的采缉,虽始于杭世骏后,这实在是“闭户暗合,未尝相袭”②。校验戴书和杭书,戴书有而杭书无者二十二条,其余一百八十九条戴书与杭书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戴著一开始是存心补扬雄书的,后来知道杭州人杭世骏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只得就此作罢,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后来用到《方言疏证》中去了。如今在《疏证》中仍能看到这种迹象。例《方言》卷二:“ 、梗、爽,猛也”条,戴震注引《苟子》和杨倞京注补出了别一说法“ ”于《方言》:“《苟子。荣辱篇》‘陋者俄且们也’。杨注云:‘ 与同,猛也。’”论者常以戴震思想继承和光大了① 《屈原赋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66 页。
① 罗常培《戴东原续方言稿序》。
② 同上。
苟子,戴震熟读过《荀子》,此亦证据,《续方言》从《苟子》和杨注中集得20 条注续之,更是证据,由读《荀子》作语言研究旁及古代逻辑而搜辑方言用例,直到戴氏思想继承荀子,或可说戴氏本人实践其主张“以词通道”所由致此的吧!
杭世骏、戴震由搜辑古书方言例以续补扬雄的做法,在语言学史上有一定影响。徐乃昌等人赓续其事。“其所甄录者,自史传诸子、杂纂、类书以迄古扶残卷,旧籍解注都凡六七十种,皆大宗(杭氏字)、东原、东冶(程际盛字)之所未及。旁搜雅记,广罗逸典,囊括唐宋小学诸书, 轩所采,摭拾略备。然并征引有加,义例未改。”①戴震以古书注续扬雄的做法在科学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本人后来改为注释扬著而成《方言疏证》,在语言学的科学学思想上两者又是一致的。
① 罗常培《戴东原续方言稿序》。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