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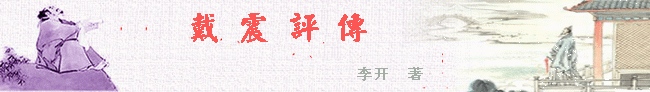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八、“权轻重”是新理学道德哲学中的辩证法
什么是权?在戴震的道德哲学体系中,权是体现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临事处置以新理学道德准则仁义礼谓之权,戴震说:“谓心之明,至于辨察事情而准,故曰权;学至是,一以贯之矣,意见之偏除矣。”①戴震注意到人们在衡量“千古不易”的事物和变动不居的事物间的难易的区别,前者“显然共见其千古不易之重轻”,后者有相当的难度,“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变也,变则非智之尽,能辨察事情而准,不足以知之”②要“知变”,那就需要“权”,需要运用朴素的辩证方法。
戴震的相互辩证方法“权”,后来曾被焦循大加发挥。焦循在阐述他的“依方辩对”的辩证法思想时,就曾发挥戴震的“权”论。他说“权也者,变而通之之谓也。”“《易》之道,在于趋时,趋时则可与权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无弊者而执之,以为不偏不过,而不知其为子莫之执中。”③焦循还认为,懂得“权”之辩证思想的人,高出传统的儒学万倍。他说:“能通其变为权,亦能通其变为时,然而豪杰之士无不知乘时以运用其权,而远乎圣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之也。”“通变而神化,此尧所以民无能名,舜所以无为而治”④。焦循还和戴震一样,把“一以贯之”作为懂得“权”之辩证方法的代名词,而与不懂辩证方法的“执一则不通”对立起来。焦循对“权”的阐释和应用,是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权”为朴素辩证方法的有力旁证。
前面曾反复讲到戴震强调自然性的人性本善和才质美,后天的学习对其保养才质起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先天才质能力“智仁勇”的“智”,还是后天学习以补才具参差而获得的“知”,都对道德准则仁义礼的实行起不可估量的作用,戴震把先天的自然性的发生认知能力与后天的知识理性都援引入道德论。但是,戴震也注意到以下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是学不尽道,知识与德性相分离。他说:“试问何为而学,其志有去道甚远者矣,求禄利声名者是也,故未可与适道。”除此以外,有一种也能学以致道,但不能守,“观其守道,能不见夺者寡矣,故未可与立。”还有第三种情况,学以致道,亦能守道,但不能遇事运用道德原则以知权变,只能说此等人精义未深。戴震说:“虽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变,由精义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圣智者,未之尽也,故‘未可与权’。”①在戴震看来,士人学子是不应该死读书、读书死的,尽信书不如无书,高于知识万倍的是懂得临机处置以道德准则的辩证方法,他简直是在说,“可与权”,懂得辩证法的人是圣人。当然,辩证方法的获得在戴震那里仍然是“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圣智”,也就是说从知识理性的积累到把握朴素辩证方法。唯独读死书而穿凿书本是最要不得的,要透过书本看到某些社会背景情况方能获取真知。戴震曾称赞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7 页。② 同上,322 页。
③ 焦循《雕菰集》卷十《说权》一。
④ 焦循《易话》上《通变神化论》。见《焦氏丛书》,光绪二年(1876)衡阳魏氏刊本。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2 页。阎若璩的读书方法“能识其正面、背面”①。戴震还举例说,盂子辟杨、墨,杨、墨之道不除,孔子之道不显,就会窒息仁义,结果会使天下“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时人读死书,就不懂得“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含义及为什么会出现此情形。戴震还特地举到孟子批评子莫“执中无权”,不会辩证地看问题,固执己见,结果“为其贼道,举一而废百”。戴震还以权之轻重说宋儒。程朱说“人欲所蔽”,去人欲即能无蔽,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轻重(是非),“执显然共见之重轻,实不知有时权之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其是非轻重一误,天下受其祸而不可救。岂人欲蔽之也哉?”②在戴震看来,乱世之因,不在于人欲之蔽人,而在于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可见在思想方法上,戴震取“权”字,取“轻重”之说,目的是要以较为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分清是非。当时还没有“辩证方法”的词语,戴震用古代的“权”字,“权之轻重”表述之,有类于用中国古代的勾股之法表达西洋的三角函数。除以“权”、“轻重”之说比况宋儒“灭人欲,存天理”是混淆是非外,还比况宋儒以超验之天理说道德,临事以理分去就,说正误,定是非,其结果必然混淆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轻、重比况之)和抹煞是非的。“自信之理非理也”,“盂子言‘执中无权’(按:指盂子批评子莫执中),至后儒又增一‘执理无权’者矣”③。意思是说,以超验之理莅事不变,不作任何辩证思考,当然就无法认清矛盾的对待双方的联结和对立,也就无法分清是非,成为固执一理而杀人。由此可看出戴震的一个极重要的思想方法:“权”喻指辩证的思考,“轻重”喻指矛盾对待双方。有关“权”和“轻重”本身的一些提法及用于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均可看作戴震对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专题论述和专门贡献,且这些辩证思想是在道德哲学这一特殊领域中被阐述的。
朴素辩证法的应用,必须就对象本身的客观存在作剖析方能得到关于客观对象的理或法则,“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①。容易迷惑人的是,宋儒也是“就事物求理”的,但宋儒先有其理,视理“如有物焉”,继而视超验之“理”,“散在事物”,故理“一本万殊”,“就事物求理”不过是“冥心求理”,不是对客观对象(事物及所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对象)作剖析,因而在宋儒那里谈不上正确的“权”,“况众理毕具于心,则一事之来,心出一理应之;易一事焉,又必易一理应之”②,仿佛也是在“权”事物的“轻重”(是非),但宋儒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以一“理”权万物,“至百千万亿,莫知纪极,心既毕具,宜可指数;其为一,为不胜指数”,于是只好提出个“理一分殊”以自圆其说,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月亮只有一个,但水面上的月亮有千万个。用超验之一“理”权应万物,充其量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戴震强调从客观对象出发权应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从思想方法上与程朱的“理一万殊”的唯心辩证法根本对立起来。
纵贯《孟子字义疏证》全书,是戴震“理存于欲”与程朱的“理欲相分”的对立,质言之,是理欲之辩,戴震以“权”之“轻重”的辩证法总结了理① 《戴震集·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9 页。
②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3 页。③ 同上。
① 《孟子字义疏证》,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4 页。② 同上。
欲之辩的实质,使朴素辩证法的应用奏出了当时的时代最强音,也明确交代了“于宋以来儒书之言,多辞而辟之”的原因。戴震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上一种流行的说法为祸于平民百姓时,祸莫大于无人去批判揭发这种错误,无人从流行的提法中觉醒过来,“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①,因此,戴震的工作就是要使民“觉”,《疏证》作为早期启蒙思想的位置,几经作者本人论定。他总结学术史上的论争,无不是一种危害百姓的倾向出来时,就有人会出来辨明是非,而且,思想史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后代的害民之论与前代的为祸之说有相似之处,后代的批判也会从前代的批判中得到借鉴,故梳理成“轻重”对立的思想史线索是完全可能的。如孟子辟杨、墨,唐代韩愈辟老、释等。如前所说,“权”之“轻重”是用以比况辩证的对待双方的。戴震在分析他与宋儒的对立时,既注意到分析这种对立的含义,又注意到与思想史上有过的对立作纵的贯串比较,在比较中,就矛盾对立双方的一些基本范畴作出必要的语言解释,并与辩证分析结合起来。例如,他说:“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曰‘主一无适’,此即老氏之‘抱一’、‘无欲’,故周子(按:周敦颐)以一为学圣之要,且明之曰,‘一者,无欲也’。天下必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而为又焉有理!老、庄、释氏主于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①“有欲有为”,几近于“生存和发展”的同义语。有欲方能有为,这是唯物的科学的认识,这本来是寻常之理,但“看似寻常最奇崛”,千百年来这一明白易懂的道理屡经扭曲,老、庄、释、宋学、明代王阳明学皆如此,戴震还其日常显见之理的本来面目,且从人本自然主义的道德哲学体系阐释之,这在科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恩格斯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②我国十八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正是从朴素唯物主义,带有人本自然主义特征的新理学的道德哲学、朴素的辩证法、语言解释哲学等方面努力去发现这一“简单事实”的,也就是说“有欲”才能“有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干其他事,“无欲无为又焉有理”?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一切先进思想的继承,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象戴震这样的“有欲有为”的唯物主义先进思想的继承。
由于用朴素的辩证方法分析问题,戴震对程朱理欲相分的危害性看得十分深透。从孔孟起,儒家历来就是提倡贤人政治的,对贤人的个人品格的含义,历来没有明确具体的说法,《论语》出现“贤”的用法25 处,多指道德或才能。例如《论语·雍也》以“贤”赞美颜回,但没有抽象出什么是“贤”。《孟子》的“贤”有72 处,其含义和用法与《论语》大体一致。戴震明确指出,贤人圣人就在于“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无私”(按:不过分中饱私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7 页。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7 至328 页。②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574 页。囊),而不是“无欲”。他说:“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有点个人的哀愁怨恨就非贤人君子了吗?否!这是多么入情入理的平正公允的说法,在君权制的时代,这样的说法实在是保护贤人,全面合理地看待贤人作风的说法。程朱以“理欲相分”为标准衡量,就会视天下无好人,“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辩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其结果天下无好人,坏人却不因“无欲”之说而归正,“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①此外,戴震指出,以超验之“理”为标准,其结果因无客观标准而人人“独执此以为君子”,没有一个人不以个人私见为“理之君子”,无不自信出于理而不出于欲,从而放肆地排斥他人的不同看法,“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②。戴震的看法是万分深刻的,它不仅属于道德哲学范畴,而且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实在是讲了经国济世之道。当一个社会只有空洞的超验之理的说教而不讲人的情性欲念,衣食住行“简单事实”时,确实就会人人自以为得到了绝对正确之理,而他人则“自绝于理”,其结果使超验之理成为杀人的工具。别说是不正确的超验之理,即使本来正确的道理,一旦膨胀放大开来,脱离了那“简单事实”,其危险亦同于本来不正确的超验之理。应该说,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历史上见得够多的了。
如同戴震单独阐述血气、人性、欲念等问题时那样,戴震在叙述理欲对待关系和理存于欲的道理时,也总是借助于古代圣贤权威,例如他说:“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侗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闻孟子、韩子(按:指韩愈)之说,人始知其与圣人异而究不知其所以异”①,如此等等。“权”之“轻重”的辩证法的运用,在戴震那里也是离不开指靠先儒的权威的。马克思在提及黑格尔用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观察历史,发现“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时曾说过以下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的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②戴震借助于先儒来演说自己的早期启蒙思想时,国内“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先儒的权威也没有什么“战斗口号”,戴震的思想,也只是以人的自然本能、本性为本的新理学道德哲学,远未涉及人的社会本质问题,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①但是,我们可以清①楚地看到,当戴震分析任何一个单独的道德哲学问题时,抑或分析朴素的辩证法本身的规律,以及综合运用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自然哲学、语言解释哲学来观察、分析和叙述思想史上对垒及其内在发展逻辑时,无不借重先代权威,戴震作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他的科学思路和叙述问题的方法,同样没有逃脱马克思所分析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领袖们所乐于应用和必然应用的一般方法。反过来说也一样,这一曾经为人类先进思想的最高代表马克思所概述过的一般方法,总是作为探索的重要依据和叙述问题的科学逻辑方法,自始至终贯串于戴震的新理学哲学中,我们不难看出,戴震在建构他的新理学自然道德哲学体系的同时,在科学的方法和方法学方面是有比较完整的建树的,其中朴学方法、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自然哲学方法、语言解释哲学的方法、复兴古道和借重先儒权威的方法等等,成为戴震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学的主干部分。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8 页。② 同上。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8 页、329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603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604 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