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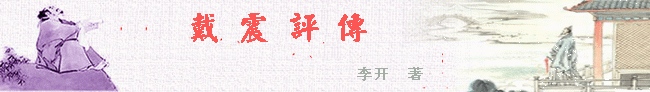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九、《孟子字义疏证》引起的反响
新理学道德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的问世,虽然它有颜元、李塨学说作为借鉴,有王夫之、黄宗羲学说作为思想史的继承,但在封建统治有如铁桶江山,思想钳制不见天日的乾嘉年间,自有其独特的思想品格和历史价值,这就是,它反映作者高贵的人格和为探求真理而战斗的自我牺牲精神,反映层层雾锁的封建统治下萌生的新的时代精神,面对一束新时代的曙光,聆听一支新时代的号角,或许它出现在不成熟的时代而来得过早的缘故吧,当时及后世的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对它的反映是不同的。唯其如此,代有争议,才是思想先驱,这正是戴震独具的历史性的品格和风貌。
围绕对戴震的评价,封建文化的卫道者和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之间,正统派和维新派之间的分野区分得一清二楚。封建文化的卫道者们故意抹煞《孟子字义疏证》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作用。他们仅仅把戴震说成乾嘉学派的代表。不错,戴震是乾嘉学派的泰斗,但仅就学术而论,他们的评价也是极不全面的,戴震不仅属于乾嘉学派,而且在若干领域内还是我国近现代科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例如近代天文、近代数学、数学史、古天文研究、上古音研究、中古音研究、文字学、汉语词源学、方志学、史地学等,以戴震的考证求实的学术精神而论,他实在是我国近代实证科学的奠基人。旧学的正统派仅仅把戴震说成考据学的代表,是不公正的。由于“五四”运动以后一度产生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不能正确评价有科学价值的考据学,故而更加不能全面认识乾嘉学术的科学意义,更加不能正确认识戴震了,一提到戴震就把他和几被否定的有实证科学精神的考据学联系在一起,考据学为什么要否定呢?考据就是寻找证据,证据就是学术水平(当然不能仅限于文献内的证据,还应重视事实上的实际证据)。考据学一般都要求在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归纳出结论。章炳麟论清代朴学是“审名实,尚佐证”。应该说,考据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如此看来,正统派往往推崇戴震的考据学,他们也就未必真正理解了考据学的精义。尤其没有理解戴震朴学中的近现代科学精神及其奠基开拓之功。对戴震朴学不能正确理解是一个方面,千方百计贬低其新理学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是另一个方面,卫道者们的老式言论确实是令人生畏的。
当时有个叫彭绍升的,是乾隆丁酉年间的进士。好佛学,长斋戒于佛前,仅未削发,但又很喜欢谈论孔孟程朱,并以孔孟程朱之学诠释释氏之言,在其著述中称孔孟与佛学没有什么两样,又说程朱与陆(九渊)、王(阳明)、释氏学说没有什么两样,还有罗有高、汪缙响应其说①。戴震曾以所著《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给彭看,彭有《与戴东原书》,信中最不满意的是戴震批判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先验本体论。针对彭的说法,戴震有《答彭进士允初书》,信中陈述朱熹信佛的事实,分析程朱与老庄释教的一致性,针对彭的最为不满的论点,戴震再一次以超验之理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来答复彭氏,戴震说:“然仆之私心期望于足下,犹不在此(按:指认清程朱与老释的一致性)。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① 江藩《宋学渊源记》31 页至35 页。
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②戴震俯瞰程朱理学问世至自己所处的时代,严酷的现实无一不潜藏着残忍的执词“理”字,冲破现实的黑暗,得首先烛照那杀人的“理”字狰狞面目,这正是戴震新理学哲学《盂子字义疏证》的精义所在,也是支配戴震后期思想和行动的基本线索。《答彭进士允初书》是对新理学思想的一个精要说明,它是戴震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文献,它与《疏证》的精神完全一致。后来孔广森曾把此文附于《疏证》之后,同郡歙县人洪榜,应戴震子戴中立的恳请,在乾隆四十二(1777)年,撰写的《戴震行状》中认为戴震功“不在禹下”,载《答彭进士允初书》于其中,后来洪的老师朱筠(笥河)见到后说:“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洪上书给朱,竭力争辩之,认为朱“尚未尽察所以论述之心”①,而朱是乾隆中式举人和进士,曾奉命视学安徽,朱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后来也就由戴中立在《行状》中删去了《答彭进士书》,后人也就没有再补入。
朱筠生前与戴友善,朱不欣赏戴震后期的思想,还只是口头上的。戴震逝世前一个月给段玉裁的信中讲到:“仆平生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②可见戴震是充分估计到《疏证》会得罪一大批人的。但出于历史的责任心,“不得不作”。戴震死后,在文字上首先发起攻击戴震的还是馆阁学士翁方纲(1733—1818),他写了一篇《理说驳戴震作》,评论说:“(戴震)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③方东树(1772—1851)则说:“程朱所严办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泅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①明末统治者将李赘迫害致死,给按的罪名正是“异端邪说”、“敢倡乱道”。《疏证》是明末清初诸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在特定的万马齐暗的乾隆年间的回响和新的呼唤。可以设想,尽管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疏证》问世后,戴震继续活下去,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
章学诚是朱骛的学生,他对朱筠,钱大昕只肯定戴的语言文字学而轻诋戴氏哲学本不赞同,认为这样做“不足以尽戴君”,于是“力争朱先生前”,认为他们对戴的评价“似买椟而还珠”,但章的力争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人微言轻,不足以动诸公之听”②。章学诚自称“真知戴震”第一人,不消说,他对戴震是有误会的(见第六章二),但总的看,他仍能较客观地评价戴震。他在《书朱陆篇后》一文中说:“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固不足为戴君累。”③又几乎是直接针对朱筠之说而发,章说道:“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②
① 江藩《汉学师承记》100 页。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1 页。《答彭进士允初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75 页。
③ 载《复初斋文集》卷七。翁方钢著。清光绪丁丑年刊本。
① 《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清光绪吴县朱氏刊本。
② 《文史通义》补遗续《答邵二云书》。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三。见《文交通义校注》,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 年版275 页。
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④后来,章曾写有专篇文章为戴申辩,但当时几乎是一边倒攻戴,终于因担心舆论压力太大而不敢示人。章在给史馀村、邵晋涵两人的信中都曾谈及此事,“别有专篇,辩论深细,此时未可举以示人,恐惊一时之耳目也。”①“已别具专篇讨论,箧藏其稿,恐惊曹好曹恶之耳目也”②可以断言,这些未以示人的“专篇”肯定是褒扬戴氏《疏证》的。
焦循(1763—1820)也是肯定戴震的哲学的。焦循著《论语通释》即是模仿《孟子字义疏证》而作的。他说:“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盂子字义疏证》。说者分别汉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诚详于汉,然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宋之义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③由上面的话可知,焦循不仅充分肯定《疏证》,而且注意到《疏证》与语言解释哲学的某些一致,以及以古圣义理作为权衡标准的思想方法。
戴震的语言文字学传人段玉裁,是戴氏一生中最亲密的学术同好,段氏虽不能完全理解《疏证》,但他在《年谱》中毕竟已撮述其大旨了。
一般认为,阮元是戴震的哲学传人。王国维著《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将戴、阮并举。胡适则视阮元为继承戴震的哲学家,他说:“阮元虽然自居于新式的经学家,其实他是一个哲学家。”④但实际上,阮元哲学并没有戴氏《疏证》的那种战斗锋芒,相反大大钝化以至于被磨灭。戴氏《疏证》言性理仁义,阮元言性命古训。他说:“余讲学不敢似学案立宗旨。惟知言性则溯始《召诰》之节性,迄于《孟子》之性善,不立空谈,不生异说而已。性字之造于周召之前。从心则包仁义礼智等在内,从生则包味嗅声色等在内。”①又说:“按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后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时,即已谐声,声亦意也。”②可以说,戴震“以辞通道”,继而建树新理学,最有力处控诉现实“以理杀人”,而阮元的学理逻辑则趋于“由道返辞,由辞返字”,与戴氏有相逆之处。故侯外庐认为阮元是文化史家,不是哲学家,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乾隆同治年间的黄式三说得上是完全阐扬戴震的人(见本章二节),但总的说黄哲学水平不高,难以深入,虽著有三篇《申戴》,但基本上停留在难以全面欣赏戴震哲学的地步。
全面评价戴震哲学的是清末的章炳麟。章氏出于反清的需要,认识到戴震哲学对现实的批判和抗争作用,加之章氏几可与戴震相媲美的学术修养,章氏对戴震哲学的评述是深邃的。例如,《疏证》多处批评荀子,但章氏认为戴学源于荀子,而荀子又是章氏特别推崇的大儒,这既说明了章氏尊戴,又说明章氏对戴学有颇值得玩味的独到的理解。从思想史的脉络看,荀子的④ 同②。
① 《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史馀村》。
② 同上,《答邵二云书》。
③ 《雕菰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学士书》。见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湾远流公司出版103 页。
① 阮元《揅经室再续集》卷一《节性斋主人小象跋》。
② 《揅经室一集》卷十。
③ 《中国早期思想启蒙史》,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578 页、583 页。
唯物主义、《正名》的类逻辑、名学逻辑与戴学的唯物主义,“ 密严瑮”的逻辑思想理应是一脉相承的,而当与思孟学派的内省的唯心论和孟柯的无类比附逻辑无任何共同之处,不能不说章氏析戴入木三分,是透过表象看实质的真知灼见。《章氏丛书》中评论戴学有数十处,其中最著名的有《检论·清儒》、《大炎文录初编·释戴》。《文录》中另有《思乡愿》上下两篇,以宋儒程朱为乡愿(同流合污的伪善者),文理逻辑一系于戴氏《疏证》,如说程朱理学“兼之老聃也,偏得之孙卿、庄周也。”文中痛斥程朱“矫情”,批判攻戴的方东树之流“不悟”,是“猥俗之论”。
戴震为阐发新理学,认定《疏证》不得不作。思想理论上的分歧是无法随便认同和调和的,加之学术见解上的一些分歧,几使戴震失去了同仁间的全部理解、体谅和支持。一代思想先驱在封建文化代表麇集的四库馆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连早年的好友纪昀、朱筠等无一不疏远他、冷落他,只有远在外地的段玉裁仍是他学术上心心相印的知交和朋友。面对冰冷的世界,戴震曾书写古诗条幅以鸣志: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象肃清高。三分割据纾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生涯岂料成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寄身且喜沧洲近,顾影无如白发何。今日龙钟人共弃,愧君犹遣慎风波。
落款为“东原戴震”,笔务雄健老辣,可证为戴氏后期所书。第一首为杜甫在大历元年(776 年)写于夔州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五①。诗中咏诸葛武侯盖世之才,然壮志不酬,汉祚难复。第二首是刘长卿的《江洲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②,大约是刘氏于唐肃宗至德三年(758 年)被贬南归之作,诗中感慨世事沧桑,人生浮沉,只有寄情山水,方可离弃忧患,免于自叹。
① 《杜诗引得》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473 页上、下栏。又见《全唐诗》第七册中华书局版2511 页。
② 《全唐诗》第五册,中华书局版1563 页。
为躲避周围的风霜刀剑,戴震搬到冷僻的范氏颖园去住。他在给段玉裁的信中说:“北官园范宅在海岱门之西,前门之东,更远人迹。”乾隆三十九年(1774)4 月24 日给段玉裁的信说:“仆足疾已逾一载,不能出户,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实不复出也。仆平生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此正人心之要。”这里,戴氏把“乞假南旋”和论《疏证》紧连一起,不是偶然的,戴氏不会不认识到晚年的不幸就是《疏证》闯的大祸。同年5 月21日给段玉裁的信说:“归山之志早定,八月准南旋。”不料这是与段玉裁的永诀之书。按章炳麟的说法,戴震的早逝,与《疏证》给它造成的不幸直接有关。章说:“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幸,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桑荫未移,而为纪昀所假,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于泯华戎之界,寿不中身,愤时以陨,岂无故耶?”①从章炳麟开始,戴震哲学才进一步为人所注意。“五四”运动时,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有不少人以戴震作为反封建的一面旗帜,胡适著《戴东原的哲学》,探求戴震思想发展的轨迹及其渊源。胡适认为,颜元、李塨“对于因袭的宋明理学作有力的革命”,并没有触动程朱的尊严,而至戴震才建立起“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摧毁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胡适早年对戴震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不容否认。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则盛赞戴震“《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并说:“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①梁还说,戴震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②。梁启超的评价,虽与当时的反封建的现实需要有关,但基本上符合戴震哲学的实际情况。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破裂以后,胡适等人逐渐为资产阶级右翼,鼓吹戴震奠基的考据学,引导青年“整理国故”,则又当别论,它已完全不属于戴震本人。孙叔平教授曾说,戴震在“五四”运动以前对封建礼教提出了“最勇敢的抗议”③。从其新理学哲学的内在逻辑,思想内容和批判锋芒看,这一评价是并不过分的,从戴震哲学的渊源的纵向追溯和横向几乎荒漠的共时比较看,这一评价仍是恰当的。思想史家杜国庠称《疏证》是“近三百年的哲学杰作”①,殆亦谓此。我们注意到,对戴震新理学的认识与历史的演进是同步的,历史按照荡涤封建礼教、恢复人性尊严和自由的必然性逻辑奔腾不息。曾几何时,林彪、四人帮重演“以理杀人”,但终究被席卷以去。历史反复证明,曹雪芹、戴震、章炳麟、鲁迅诸思想先驱批判封建礼教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虽各自打上不同的时代烙印,但至今尚未过时,当戴震愤怒地控诉“以理杀人”时,武器的批判已经发生,例如1774 年有山东充州清水教王伦起义,1775 年已有白莲教秘密组织。洪亮吉(1746—1809)和章学诚都说“官逼民反”。《疏证》问世后七十余年,中国大地上就发生了扫荡封建礼教,宣传平等自由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场面是诸合力的作用,历史的前进往往是进步势力反抗腐朽势力的阶级斗争,而其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构成则应是诸进步势力的合力。戴震,这位来自皖南山区的贫苦农民的子弟,为演出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悲壮活剧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新理学哲学思想成为绵延几个世纪的诸进步势力的合力中不可小看的一股力量。
① 《太炎文录初编》卷一《说林》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中华书局1954 年单行本31 页。
② 梁启超《戴东原图书馆缘起》,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五册。
③ 《中国哲学史稿》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17 页。
① 《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见《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370 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