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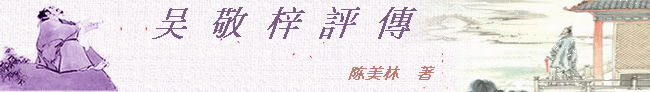
|
三 吴敬梓的思想局限
传主吴敬梓是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晚期、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的作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又极为崇仰魏晋六朝的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先后还受到时代先进思潮以及自然科学的影响和薰染,更由于家道中落、仕途坎坷,逐步从世家大族走向市井下层,随着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他的思想也逐步有所发展,在他的世界观中逐步滋长了进步的因素。对于他的进步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文艺创作,在上述有关各章节中已有所论及。但吴敬梓毕竟是封建时代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作家,在他的世界观中也自必留有封建意识的鲜明烙印,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每个作家的封建意识则有各自独特的表现,传主吴敬梓的封建思想的具体特性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门阀意识。这种门阀意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抒情的还是叙事的)都有明显的表露,也是他的作品产生局限的重要原因。
门阀制度是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而出现、并为巩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者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当然,此处仅就立功者本人而言,至后世则扩大为始封者以其积功所得的高官厚爵的遗泽所庇荫的家族后人,以致一些仕宦子弟每以郡望门第自诩。尽管门阀制度随着历史的推移已逐步陵替,但一些高门显宦子弟的门阀意识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如钱大昕所说: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弗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进士科,士皆投牒就试,无流品之分。??士既贵显,多寄居他乡,不知有郡望者,盖五六百年矣。惟民间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琊,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此习俗之可笑者也。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这正反映了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门阀意识落后于门阀制度的现实情况。甚至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之际,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家也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门阀意识的影响,例如顾炎武在《与卢某书》、《莱州任氏族谱序》、《裴村记》以及《日知录》卷十二"流品"等文中也流露了这种封建意识。因而传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存在着门阀意识,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传主吴敬梓的门阀意识最为强烈地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出身显赫、门第高贵的陶醉,以及对先人的功名仕宦和道德文章的赞美。
旧时代的文人为了抬高自己的氏族门第,总要在历史上找出自己的显赫远祖来。传主也不能免俗,自称为泰伯、仲雍的后人,并津津乐道。这也和屈原、司马谈、班固一样,只是述祖德之清芬而已,其中自然潜伏着程度不同的门阀意识。
在《移家赋》中,传主首先极力铺陈宣扬先人的仕宦功绩和道德文章。
远祖吴聪在"永乐时从龙"有功,授官正五品骁骑卫。吴敬梓对此极力铺扬说"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吴聪之后,因无子弟再立新功,自然失袭,以致吴凤"自六合迁全椒"务农,成为《儒林外史》中胡屠夫所说的"平头百姓"。凤子谦,曾自学成医,吴敬梓随即赞扬说"僦贷季以为师","治青囊而业医"。吴谦行医之后,家道渐丰,乃命其子吴沛专攻儒业,多次应举,但"七战皆北",最后乃以乡里私塾先生告终,吴敬梓又说他"乃守先而待后,开讲堂而雒诵,历阳百里,诸生游从"。从吴凤至吴沛,由务农、行医而教书,没有仕宦之人,吴敬梓自然也无法铺扬他们的政绩。由于吴沛教子有方,并以自己的失败教训告诫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诸子,终于四人考中进士,国对且是探花。吴敬梓对此极为得意地说:"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并且,还对他们仕宦经历一一铺陈,赞美表彰。吴国鼎是中书舍人,接近"紫禁",因此说"伯则遨游薇省";吴国缙是江宁府学教授,坐冷衙门,所以说"叔则栖迟槐署"。"遨游"与"栖迟"显然有张扬与潜郁之分,这正暴露了吴敬梓热衷功名的庸俗一面。任给事中的吴国龙,则被说成是"季抗疏于乌台",似乎是个敢于风议朝政的言官,其实却是个出仕两朝的"贰臣",原为明崇侦朝的户部主事,降清后于康熙时任工部给事中。吴敬梓并不隐讳,反说他"受两朝之眷顾",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至于亲曾祖国对,吴敬梓更是极尽铺扬美化之能事:"三殿胪传,九重语温;宫烛宵分,花砖月午",是写他考中探花;"张珊网于海隅",是写他曾任福建乡试主考;"悬藻鉴于畿辅",则指他提督顺天学政;"羡白首之词臣,久赤墀之记注",是写他由编修而升任侍读。总之,他的曾祖一辈,是他的家族鼎盛时期,因而也就成为吴敬梓追慕不已的一段家史,他曾加以总结性的描写:"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镼妆靓。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此后,祖父吴旦以下,功名逐渐下降,虽然叔祖辈中有两个进士,但总不如曾祖辈显赫一时,因而吴敬梓也就不再大肆铺陈他们的功名仕宦。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赞扬其先人的道德文章。对"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封建道德传统,传主颇为自诩。特别对于谦让孝悌等德行的赞扬更是不遗余力。既然他自称是泰伯、仲雍的后裔,泰伯曾"三以天下让","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所以在《移家赋》中对于始迁全椒的"转弟公",明明是失去千户爵的承袭资格,却美化为"让袭",以表彰其所谓"让德"。至于吴谦之所以"翻玉版之精切。研金匮之奥奇"(《移家赋)),则是因为其母病久,他"不忍听之庸医",乃"自习歧黄学,遂精针灸之术"(张其浚《全椒志·吴谦传》),学医乃是为了尽孝。至于传主的嗣父吴霖起更是孝子,母在则"六艺竞进以延年,五采戏前而色喜";母死则"肝干肺焦,形变骨立"(《移家赋》),孝行彰著。
此外,对于文章传家,吴敬梓同样也是沾沾自喜地大加赞扬,说他的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初奋发于制举,仍追逐于前贤",可见只是一个遵循孔孟程朱之道、沿着科举阶梯一心向上爬而未爬上去的秀才。至于探花公曾祖吴国对,则"常发愤而揣摩,遂遵循而得路",显然是依靠揣摩举业、遵循儒术而得官翰林侍读。传主还赞扬嗣父吴霖起极有学问,"网罗于千古,纵横于百代",其实只是一个"暮年黉舍,远在海滨"的教授八股举业的拔贡、江苏赣榆县学教谕。从这里可以看出吴敬梓极力赞扬的传家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只是儒术和举业,并未涉及其先人的学术研究领域。其实,他的家庭有着治《诗》的传统,代有著述。虽然这并不能不受儒家思想的支配,但并不全同于完全力应科举考试的儒术。因此从传主所钦迟和追慕的具体内容来看,实际上只是自诩门第的思想意识的表露,并未能摆脱时俗的见解。如他的友人王又曾就曾赞叹地写道:"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这倒十分切合传主的思想。
传主经常以出身这样一个家庭而自负,说自己从小受到诗文的教育和熏陶,所谓"少有六甲之诵,长馀四海之心"(《移家赋》),幼时钻研学问,壮时有心济世;"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移家赋》),说自己品德高超、志向远大,既不趋炎附势,又不谄媚阿谀,有学问、有操行。并且,他还以历史上姓吴的闻人来比拟自己的道德文章,这其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了一定程度的门阀意识。
他最喜欢把自己比做吴质。甚至他的友人王又曾在诗中也把他比做吴质。他之所以如此喜爱吴质,除了吴质和他一样都不见容于乡里之外,那就是吴质和他一样,又都是泰伯后人,具有门阀意识的吴敬梓引以自比也就不足为奇了。
传主在以吴质自况的同时,还自比吴刚。吴刚原是神话传说中于月中斫桂的人物,科举时代考试中式也被称为蟾宫折桂,因而旧时代文人常以吴刚斫桂来比拟功名成就;也有诗人将吴刚写作吴质,如李贺的诗作《李凭箜篌引》即云:"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此处的吴质即月中斫桂的吴刚。因而吴敬梓以吴刚自况,实际上也隐藏着以吴质自比的意义在内。他在《寄李啸村四首》中曾叹惜"浪说吴刚能斫桂,无由得见月中人",显然是以吴刚斫桂来比拟自己的功名无成,正如吴质在魏文帝征召之前沉沦下层一样。以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来自况,他已感到不敷运用,乃借用神话中的人物来自比,这种封建的门阀意识表露得已够充分的了。
吴敬梓还乐于与现实生活中吴姓的人攀亲认故,上元县学教谕吴培源(据光绪八年《江宁府志·秩官表》)字蒙泉,著有《会心草堂集》。在他任上元教谕期间,与吴敬梓、程廷祚等人诗酒唱和,颇有交往(参见《江苏诗征》卷十五等),是吴敬梓"生平所至敬服"的人(金和《儒林外史跋》),籍贯江苏无锡。安徽全椒吴敬梓却写有(赠家广文蒙泉先生》,说"吾宗宜硕大,分派衍梁溪",认为一家。这在吴敬梓看来也并非全无根据,据《一统志》,故泰伯城在无锡县东南四十里处的梅里,自泰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于此,以后才迁往苏州。吴敬梓自称为泰怕、仲雍后人,认无锡人吴蒙泉为本家,在他看来并无不可。
传主的门阀意识有时甚至表现得极为可笑,只要与"吴"沾上关系,他就拉来自比。在《秋病四首》中写道:"屯贱谁怜虞仲翔,那堪多病卧匡床。黄金市骏年来贵,换骨都无海上方。"明显地以虞仲翔自比,因为金文"虞"作"吴",虞仲亦作吴仲。虞仲翔名翻,三国时人。《三国志·吴书》有传,不引。他也是泰伯、仲雍之后,《元和姓纂》卷二:虞,虞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又武王封虞仲于河东,亦为虞氏。会稽余姚人赵相虞卿。秦有虞香,香十四代孙意,自东郡徙余姚;五代孙歌。歆生翻。
《姓解》卷二:虞,帝舜之后,有虞仲,史有赵相虞卿,??吴有虞翻。
不仅同是泰伯、仲雍后人,而且还有类似的身世:虞翻是浙东余姚人,传主也说自己"久发轫于东浙";虞翻不就曹操的征辟,传主也未赴京应鸿博廷试;虞翻被徙交州,传主也被迫离乡;虞翻"性不习俗,多见谤毁",传主也有"灌夫骂座之气",以至"竞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虞翻是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易注》,传主晚年也"治经",著有《诗说》。凡此,都足以使吴敬梓将虞仲翔引为同调并以之自况。吴敬梓门阀意识的这种表露形式,也为他的友人所注意。江西会昌人吴湘皋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最后竟以调侃的语气特别说明"余两人有同姓之谊,故质言以叙其端",就是明显的例子。
传主还以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来称美友人,这是由于他特别看重自己的门第,因而在赞扬别人门第时,也不免流露了自己的门阀意识。怀宁秀才李葂,字啸村,颇擅写诗,吴敬梓一再将他比之以李泌、李白:"邺侯风骨谪仙狂,白下空台咏凤凰"(《寄李啸村四首》);"叹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遇别李啸村》)。李泌是唐代七岁能文的奇童,后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数朝,以功封邺县侯;李白是众所周知的大诗人。用李泌、李白来比拟李葂,未免溢美过甚。
他还将建德诗人徐紫芝比之为徐陵,在为紫芝《玉巢诗草》作序时说:"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徐陵是南北朝陈代文学家,字孝穆,是当时宫体诗的重要作家,编有《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传主用他来比拟徐紫芝也是极为不伦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诗人之所以得到吴敬梓的极力褒扬,还在于他们的某些遭遇可能触发起吴敬梓的感慨。传主曾被荐举应鸿博之试,并已参加过学院、抚院、督抚三级地方考试,但却未赴廷试。李啸村也有同时被荐举的传闻,光绪《怀宁县志·文苑》所记:"雍正乙卯(1735 年)试博学鸿词,两淮都转卢氏见曾以葂名荐,为学使者放归。"徐紫芝也有被荐举的消息,郑相如在为他的《玉巢诗草》作的序中说:"凤木(紫芝字)入举场,三十年矣;宏博之科,今亦一与矣。"但检李富孙《鹤征后录》并无徐紫芝之名。可见李啸村与徐紫芝两人都有被荐举应鸿博之试的"动议",然而并未成为事实。这与传主吴敬梓虽曾参加地方级的考试而未能参与廷试的情况正有某些类似,因而传主特别垂注并推崇他们,也就并非偶然。
吴敏轩与王溯山相交也很深,《文木山房集》中有好几首诗、同写到他,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丙辰除夕述怀》、《青玉案·涂次王溯山》。他把王溯山比做王维和王伯舆,说"深情王伯舆"、"平生我爱王摩诘"。
李本宣字蘧门,江都人,流寓南京二十年。《文木山房集》中有《二月三日舟发通济河同李蘧门作》、《酬李蘧门》、《陈仲怡刺史留饮寓斋看灯屏同李蘧门作》、《腊月将之宣城留别李蘧门》,还录有李本宣和吴敬梓《夕阳》诗一首,可见李本宣亦颇有诗才。他还是个画家,作有《板舆花径奉母图》,遍征当时诗人题咏,所以传主将他比做小李将军,说"迥望秣陵城,小李将军画"。唐代画家李思训善画金碧山水,被称为李将军。其子李昭道也以山水画闻名,被称为小李将军。
黄河,即黄崙发,南京人,有《自怡集》。黄河曾为《文木山房集》写过序。传主将他比之为黄权。姚莹,字文洁,南京医生。有《环溪草堂集》。传主将他比之为姚合。
综上所述,传主吴敬梓总是找出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或"名人"来比拟自己的友人,这与他以历史上吴姓的"闯人"或"名人"自况一样,虽属封建文人通病,但对传主来说,多少也有门阀意识在作祟,既表示自己是世家华胄,又说明自己交接的友朋也非暴发新贵。
夸耀自己的氏族,看重自己和友人的门第,这固然是传主吴敬梓门阀意识的一种表现,而对族人不顾自己的世家大族身份去与盐典商人攀结亲姻感到无比的愤怒并加以斥责,更是他的门阀意识的顽固表现。
这种情况在明清两朝也是屡见不鲜的。据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云:东吴犹重世家,宜兴推徐、吴、曹、万,深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宜兴许氏,溧阳包氏,皆新发,而 欲自附巨族之后。乡人嘲之日:"彭马史狄包,疯痨膈哮(方音作蒿);徐吴曹万许,马赵温关鬼(方音作举)。"吴人嘴舌轻利,一至于此。
刘氏所记是"新发"攀附"巨族",而吴敬梓所写则是"旧家"低首于"暴发"。这也正反映了时移世转的实况。在《移家赋》中,传主吴敬梓以极为愤怒的感情痛斥那些败坏世德祖风,贻羞先人门第的族人,讥刺他们"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求援得援,求系得系。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货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这些典故,无一不表明吴敬梓对某些族人不顾门第与豪绅富商结姻极为痛恨,认为这是出卖祖宗、贻羞先人、败坏家风、趋炎附势的行为。他对这种行为的愤慨和斥责,流露了"恨铁不成钢"的感情,这也正是他的门阀意识的一种表露。
与此同时,传主吴敬梓还怀着强烈的门第优越感,对盐商典当尽情讽刺、着力鞭挞,咒骂那些商人"彼互郎与列肆,乃贩脂而削脯,既到处而辙留,能额瞬而目语",指斥他们贩卖起家,到处兜售,巧诈奸伪,唯利是图,见隙即钻,无空不入;嘲笑他们全都是"钱癖"、"宝精"。对于"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原为张融《海赋》语,见《南齐书·张融传》,吴敬梓摘引入《移家赋》)的盐商,传主更斥之为"山人面"。
雍、乾两朝,江淮盐商与山西票号一样,都是国内最大的商人。吴敬梓几度前往的扬州,则是盐商的集中地,他们资本雄厚,利润至大,家拥巨资、生活豪奢,如汪廷璋"富至千万"。他们之间竞相比富,有的以万金购金箔于塔顶散去,顷刻而尽(李斗《扬州画妨录》卷十五、卷六)。传主吴敬梓曾出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中,必然会与盐商有所交接,对他们的生活情景自会有所了解。他的至友程晋芳,其家也是由业鹾而成两淮殷富的。因而传主对于盐商的豪奢生活也曾亲眼目睹,一旦回顾自己虽然出身高门,然而却衣食不周,难免感慨万端。而族人中居然还有人对盐商典当的豪富表现出既羡慕又懊丧的态度,所谓"昔之列戟鸣珂,加以紫标黄榜,莫不低其颜色,增以凄怆,口嗫嚅而不前,足盘辟而欲往。念世祚之悠悠,遇斯人而怏怏"(《移家赋》),这就更加激起传主对盐商的憎恨,对族人的不满,对过去家门鼎盛的怀念,对如今门庭衰落的悲惋,流露了无可如之何的门阀意识。
传主吴敬梓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在他杰出的作品《儒林外史》中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对于泰伯祠的祭祀盛况,传主尤着力描写。当然,《儒林外史》之所以极其铺张地描写祭泰伯祠,原因不止一端,前文已有所叙及,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夹杂着作者表彰先祖、自矜门阀的意识。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景物环境的描写上,都有痕迹可寻。
从人物形象看,杜少卿、沈琼枝、四奇客无疑是闪烁着光采的新人,然而就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着门阀意识的印记。杜少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大老爷"则是"江西赣州府知府"。他本人对科举时文、举人进士固多嘲讽,然而他所蔑视的王进土只是"灰堆里的进士","不要说先曾祖、先祖、就是先君在日,这样的知县不知见过多少"!不过,当王知县丢官坏事、无处容身时,他却又接到家中来住,不怕别人因此前来闹事,说:"先君有大功德在于乡里,??就是我家藏了强盗,也是没有人来拆我家的房子。"只要略加品味,就不难发现无论先前拒绝去拜会,还是后来主动邀约来家,在对待王进士前后不同的态度上都表露了优越的门第感。不仅如此,杜少卿其它一些"豪举"也是如此。例如他送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应考,就因为是他家"太老爷拿几千银子盖了考棚","众人谁敢不依"?又如他对韦四太爷的敬重,对鲍廷玺的照顾,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他家"太老爷"的拜盟同学或受过抬举的人,所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这些都表明他对先人遗风、祖宗门第的念念不忘。
沈琼枝看不起盐商的富贵奢华,不愿做他们的小妾,敢于从扬州盐商宋为富家中只身逃到南京,依靠卖诗文、做女工生活,在污浊的社会中能岸然挺立,有信念有决断,诚为不可多得的妇女。但是,就在她身上也潜伏着传主的门阀优越感。吴敬梓特地安排她为斯文之后,是帮助萧云仙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常州贡生沈大年的女儿。更可说明问题的是,传主让她说出所以不肯为宋为富小妾的原因在于"??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故此逃了出来"。张耳故事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可见传主通过沈琼枝之口斥责盐商为"佣奴",显然是以赵王张耳夫人的意念出发的。这不能不说是传主的门阀意识的不自觉的流露。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市井小民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某些优良品德,如"四客"的自食其力、不畏权势等等,颇有进步意义。但是,对无家无业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做裁缝的荆元,传主在以赞扬的笔调描写了他们一番之后,随即抛开,不再关心他们今后的命运。唯独对原来"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的商人地主出身的盖宽,却怀着更为深厚的感情,写出他一生的不幸遭遇,对往昔泰伯祠盛况的不胜追慕,对眼前泰伯祠败落的唏嘘感叹,还特地交代了他的下场,被人"出了八两银子的束脩,请他到家里教馆去了"。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盖宽较其他三客有"根底",因而才获得传主如此饱含感情的笔墨。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鲍文卿这一形象上。传主赞扬鲍文卿自食其力、敬重斯文,特别表彰他知书识礼、安分守己,不敢与知县向鼎同座,怕坏了"朝廷体统",大力肯定他对不安本分、穿着士人服饰的同行钱麻子、黄老爹的斥责。传主显然把这样一个出自下层的演员,塑造成为一个"名戏而实儒"(卧闲草堂评语)的人物。可见传主的门阀意识对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实在是产生了某些歪曲的消极作用。
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小说的景物描写中也有所流露。中堂娄府的"焚香"方法、武英殿御赐的尚书虞府的料丝灯,杜少卿先人埋了九年零七个月的老酒,都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加以描绘。国公府的园林,富丽堂皇而又雅致宜人;可是盐商万雪斋的园林,在奢华之中处处露出暴发户的特色,"塘沿略窄"到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去;高翰林的园林,传主则让迟衡山与武书去嘲讽,迟衡山说:"园子到也还洁净,只是少些树木。"武书就借题发挥说:"亭沼譬如爵位,时来则有之;树木譬如名节,非素修弗能成。"武书这段话是从宋人卢秉的议论中借来。卢秉又是何许人?在《宋史·卢革传》中附有小传,记他曾"奉使淮浙,治盐法",不得"私鬻";他还比较关心人民生活,安徽滁州一带曾经发生饥馑,"滁、和民捕蝗充食",他据实上奏神宗,得以"罢献",从而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传主借用历史上曾在自己家乡管理过盐政的卢秉的言行,来鞭笞眼前新贵的不修名节,指责他们远远比不上"素修"名节的世家大族。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从门第优越感出发的。
总之,无论在故事情节的选取上,还是在人物的塑造和景物的描写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自高门第的门阀意识。也正因为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的作祟,而导致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存在着一些缺陷。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