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影像作家”保罗.斯特兰德
作者:龚 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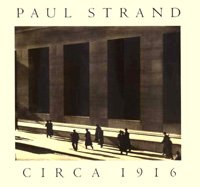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记录。斯特兰德马不停蹄地行走着,拍摄着,关注着。他的目光从城市而村落,从本土而异域,从纯粹的形式意味浓厚的摄影而社会文化内涵的生气灌注,我觉得斯特兰德是一个摄影者,也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影像现实主义作家”。
一
尽管照相机的背后从来都是一双有选择的眼睛,看到了这个,就意味着遮蔽了那个,因此我们不必对照片满怀期望,期望它保留了我们想看到的任何瞬间,或者还原为历史的现场。但底片的瞬间定格毕竟将某个特定的时空突现出来,以至于照片成为了某种“在场”,比如历史,比如环境,比如分秒的瞬间。在这些“在场”,照片获得了凝练和提升,就像布勒松的“瞬间”,那些时空里的人事,恍然为人生的一种意义。
同样表达瞬间,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的照片却是更加具有了一种形式感,仿佛这个瞬间是由来已久地存在着,从而这个瞬间变成了一种意义。
有意思的是,布勒松1935年在美国曾师从保罗·斯特兰德,学习摄影,看起来“瞬间”是他们之间的精神承传。现在我们似乎不大听到保罗·斯特兰德的名字,其实他是个走在二十世纪摄影前面的人,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i)在第一次看到斯特兰德的作品后,备受感动,他说:“我对摄影的认识在那天下午具体形成,因为我终于了解这种媒体于表现艺术上拥有多大的潜质。”于是,亚当斯的峡谷、河流、人物,不单单是一次快门的记录,如那幅《埃尔南兹山月》,墓碑和月空弥散着诡秘的氛围,那些如丝缎层叠的云层仿如静止的布景,这已然超越了自然的风景,而是亚当斯和他的相机共舞的表现了。
保罗·斯特兰德1890年出生在纽约,乃波希米亚和犹太人的后裔。十二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他人生的第一部相机。十四岁在纽约民族文化学校(Ethical Culture School)读书时受教于摄影家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正是由于路易斯的介绍,斯特兰德认识了后被尊称为“当代摄影之父”的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兹(Alfred Stieglitz)。从德国留学返美的施蒂格利兹,在1902年提出了摄影分离派(Photo-Secession),1905年在第五大街291号建立了一个空间,世称“291艺廊”,为了使“人们认识到画意摄影不是艺术的陪衬,而是表达个人的一种独特的手段”,施蒂格利兹在自己的创作中也逐步摒弃当时在欧美盛行的模仿绘画的“画意摄影”的影响,提倡“纯摄影”,即发挥摄影自身的特质,照片的影像要真实清晰,影调要丰富而层次分明,这种强调不仅是着眼于技术上的,更在于摄影者借助相机的一种自我个性表达,这种表达又是有赖于摄影本身的特点的,而非绘画的艺术表现方式。自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以后,摄影在二十世纪初尚属新兴艺术的时代,施蒂格利兹纯粹摄影理念的倡导,其意义当然超过了“怎么拍一张照片”的问题,而是对摄影艺术独立空间的一种拓展,换言之:摄影就是摄影,非其他。

斯特兰德以他直截了当的摄影作品,受到施蒂格利兹的极力推荐,既是“纯摄影”理念的一种实践,也同时影响了后来一大批摄影家,摄影艺术在二十世纪日益蓬勃。保罗·斯特兰德被誉为“美国摄影发展史上自阿尔文·兰登·科伯恩(Alvin Langdon Coburn)之后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摄影家”。
《华尔街,纽约》(Wall Street)(1915)。斯特兰德的早期作品。让人过目难忘的照片。石头垒成的坚固的建筑物,庞大巍峨,占据了照片大半,在早晨的光线中,立面呈现巨大的阴影。在强大的墙体旁,走着一些去上班的人,分不清男女,只有匆忙行走的剪影,或前倾,或低首,看不见他们的面影,只是尖锐细长的影子,在庞大的建筑物侧分外无足轻重,渺小孤单,或许这些人在华尔街这个资本市场中是一个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此时此刻,他们却显得那么落寞,不知道从何而来,到何处去。人在这一刻显得那么无依无靠,早晨的阳光似乎被建筑的阴影所吸收,而人只是“人造物”旁边的一个小钉子。斯特兰德拍下的瞬间,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行走在工业时代巨大的迫压边缘,人彷徨和无助,虽然晨曦是如此的明亮,只是明亮的同时,阴影也分外的沉重。《华尔街》仿佛前瞻性地预言了人类在现代技术/信息社会的一种命运。人,似乎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切,最终却依然孤独无依。仿佛照片上那四个长方形的凹陷,是窗户,或是其他,看久了忽然觉得很像棺椁。
《白色栅栏》(White Fence)(1916)也是他的早期作品,有着与《华尔街》一脉的锐利影像,白和黑,前景的栅栏如白色琴键,极具鲜明犀利之感,远处两幢屋子一明一亮,窗户的几何形清晰明快,呼应着栅栏的线条感觉。这是一幅讲究线条的摄影,影像质地纯粹,没有多余的零碎,日常的栅栏在照片中似乎脱离了它的功能,充满了单纯的形式意味。这样的场景似乎并不出现于某个农场——事实上它就是来源于一座普通的农舍罢了,它仿佛映现于一个梦境,枕着梦境的似乎正是这些白色的鲜锐的栅栏,它们像轨道一样载着你飞跑。
《双子湖》(Twin Lakes)(1916),不见通常的波光粼粼的景色,只有云,和似乎与天空接壤的阳台,一角屋顶一截栏杆,是突向天空而去的样子,凌厉的三角形状在长方形构图中突兀醒目,视觉简单,却如仰望苍鹰飞翔于悬崖峭壁的冲击力。
在这样的纯粹影像之外,斯特兰德也喜欢拍人,他的人物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他的人像一如既往地纯粹。人物似乎总是倚墙而立,面容坚毅地望着镜头,好像与干硬的墙面融为一体。

——如《盲妇》(Blind Woman)(1916),挂着“BLIND”胸牌的盲妇人站在石头墙前,嘴角坚韧,脸色肃然,是那种饱经沧桑的面部肌肉,她的瞳仁似乎森然地望着照片外面。照片非常纯粹,看到这样的照片,你情不自禁会去想照片里的人的命运,尽管我们终究无从知晓。
——如摄于1953年的《裁缝的徒弟,鲁塞拉,意大利》,已然是率真执著的年轻女子,站在干燥的墙前,简练,反差,富有张力,女子手里的圆草帽和旁边那棵挺立的小树,在单纯的影像中点染旋律。
这种饱满的具有力量感的单纯在《赶集的日子,鲁塞拉》(1953)中仿佛弥漫成一种悠然的温情。是南欧的一个小镇集市,小贩、逛街的人、闲话的妇人、把着自行车聊天的年轻人,一幅闲适的日常生活图景徐徐展开。这样的情景仿佛不是一向锐利的斯特兰德所拍摄的,光线如此柔和,场景如此人情冷暖,就好像听得见空气里嘈嘈切切的声音。
其实,这和斯特兰德的其他创作并不矛盾,他在人物摄影中流露出的一种对普通民众的关注一直贯穿于他的艺术创作中。他不是那种在象牙塔里的人,在二战期间就参加过左派团体,拍摄普通劳动者,以批判的眼光观察社会,是一个有社会理想的艺术家。他的创作领域也并不宥于摄影,纪录片拍摄是他影像人生的另一面。
二
1935年,斯特兰德与哈罗德·库尔曼(Harold Clurman)和查尔·克劳福德(Cheryl Crawford)一起去前苏联访问,认识了当地一些观点激进的艺术家,其中包括前苏联电影蒙太奇理论创始人爱森斯坦(Sergei Elsenstein)。回到美国以后,斯特兰特就着手拍摄了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纪录片。
其实,在这之前的1921年起,斯特兰德与画家查尔斯·希勒(Charles Sheeler)拍摄制作了美国第一部前卫影片《曼那哈塔》(Mannahatta)(1925年完成),这是一部关于都市高层建筑物环境问题报告的影片。1932年,在墨西哥政府的邀请下,他为《墨西哥人档案》(The Mexican Portofolio)做制作和影像资料的收集,还是普通人命运的主题,描写的是墨西哥市井百姓的生活。
从前苏联回来,1936年斯特兰德制作了《划过平原的犁》(The Plow than Broke Plains),描写美国南方腹地的工会情形。1937年,斯特兰德和利奥·赫尔维兹(Leo Hurwitz)共同创立了“边界影片”社(Frontier Films),把工作的重心都放在了纪录片制作上。就在这一年,他们拍摄了一部表现西班牙内战的反法西斯主题的《西班牙之心》(Heart of Spain)。另一部《坎伯兰河的人民》(People of the Cumberlands)也于该年完成。给“边界影片”带来更大盛名的是1942年完成的《国土》(Native Land),对美国本土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是影片的主题,它耗时四年,投入了斯特兰德及其合作者很大的心力。正是这一年,珍珠港事变发生,美国自此无暇国内战争,卷入国际风云硝烟。而《国土》也是斯特兰德的最后一部纪录片。
因为斯特兰德积极以艺术介入社会和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弥漫之时,1950年,他离开美国定居法国。
综观斯特兰德的纪录片创作,那种对民生的关注,对社会时事的敏锐,对周遭环境的关心和观察,一直贯穿始终。在影像的后面,始终是一双尖锐、敏感、热切的眼睛。他是注重影像之纯粹肌理的,但这些影像不单只是唯美的影像,而是他表达社会人生之思考的一种手段。
三
1947年,斯特兰德在纪录片之后重归摄影。直至他1976年3月31日去世。
但他的焦点始终对准普通民众,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绪,他们在时代中的命运。他去各地旅行,意大利、法国、英格兰,镜头延续着斯特兰德的人文关怀,他对生命和时代的思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开始了一系列的专题摄影。
1950年《新英格兰时代》(Time in New England)。
1952年《侧影法国》(France in Profile)。
1954年,斯特兰德和意大利剧作家塞萨尔·扎瓦蒂尼(Cesare Zavattini,《偷自行车的人》作者)合作拍摄的许多村落和家族照片的《一个国家》(Un Paese)摄影画册出版,就在扎瓦蒂尼故乡鲁塞拉(Luzzara)所摄。我们上面看到的两幅摄于鲁塞拉的照片应该就是属于这一系列专题的。那看着镜头的“裁缝姑娘”和集市上温暖的光线、悠闲的人群,记录着斯特兰德对土地与人的感怀。我想象他在村落和小镇上随意走着,眼光似乎是散漫的,但内在却如豹子般炯炯,内心随时与对象发生着或私语或呢喃,然后拍下这种交融而生的影像。
后来的观赏者如我们,藉此与彼时彼刻的斯特兰德交流。
1955年,《活生生的埃及》(Living Egypt)。
1968年,出版了他从1954年开始关注的迁移至苏格兰西部的希伯来家族的影像——《边远的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hrides)。
1976年,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加纳:非洲画像》(Ghana:An African Portrait)推出,这是他从1964年就开始拍摄的专题,这一次他把镜头聚焦在了进行改革独立和非洲主义运动的加纳。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记录。斯特兰德几乎马不停蹄地行走着,拍摄着,关注着。他的目光从城市而村落,从本土而异域,从纯粹的形式意味浓厚的摄影而社会文化内涵的生气灌注,我觉得斯特兰德是一个摄影者,也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影像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眼光始终是“向下的”,他深深凝视着广袤大地上的人,他对他们满怀尊重和体贴;他深深地思考着他身处的社会,在高楼大厦的时代他关注的并非“摩天”的灯光如何璀璨,而是高楼脚下的人的命运;他的脚步和他的镜头同在。
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兹在1917年给斯特兰德拍过一帧照片,照片上的斯特兰德像一个知识分子工人,如时下坊间所谓的“灰领”,衬衫领带,但衬衫的袖子高高卷起,像是才从工作台上转身,外套工装围裙,却是口衔烟斗,如喜欢在书房里漫谈的雅士那样。注意到斯特兰德的眼神也是如他的“人像”一样直视镜头,扎实、坚毅的。我觉得这幅照片非常形象化了斯特兰德的性格和创作风格,他就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自己理想的艺术家。
当然,那些隐没于时间的生动细节我们是无法知晓了,就如同照片后面同样隐没的声音、呼吸、气味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