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生活中何为重要
作者:陆晓星

陆:首先,祝贺您的小说《美的线条》(The Line of Beauty)获得了今年的布克奖,大家都知道世界文学大奖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是英国年度最重要的文学小说创作奖。这项创设于1968年的文学奖用于奖励当年以英文写作的最佳小说作品,可以说在整个英语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那么能不能告诉大家赢得布克奖对您意味着什么呢?
霍:可以。这是一项英国最大的,包括奖金额度上也是最为丰厚的奖项,是颁发给用英语写作的小说的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之一。大家对布克奖可能也有所了解。它是针对在英国、英联邦及其属地发表的小说颁发的奖项,当然美国除外。可以说这是一个英国文学奖,不针对美国。国际上也给予布克奖极大的关注。我对能获得布克奖感到很荣幸,因为从某种一定角度来看,获奖是相当偶然的。也许五位评委的爱好口味都大相径庭。有一百三十部小说参与评选,评委们得达成一致意见从中选出获胜作品。因此获奖机会是非常小的。我认为能够进入布克奖的最后角逐已经非常满意,当然最后赢得奖项是我的荣幸。不过,我认为不能将赢得这项奖看成是一件至高无上的荣誉,不能把布克奖看成一个有魔力的词,这个态度非常重要。当然,如果我没赢得布克奖,我今天便不会来到上海跟大家见面。但赢得布克奖仅仅意味着我成为了人们新近关注的对象。我的前几本书卖得都不错,但一旦你能进入某一图书奖的最后角逐,书的销售量就会翻上三番,甚至更多。我还不了解我小说的销量情况,但是人们说布克奖会把一个作家捧至完全不同的层次。不光靠英语版本,也靠小说的各种翻译版本。不过,现在切断言尚为时过早。会发生什么我无法预测。不过,获奖至少让一个作家有了一个比较舒服的“栖息地”。
陆:1994年的布克奖颁给了詹姆斯·凯尔曼(James Kelman),而他的书里面因为有很多脏话粗话而引起不小的争议,而今年获得布克奖的这本小说涉及到比较敏感的话题,而且一些描写也比较直露。以此观之,我们想问当代英国文坛的鉴赏品味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
霍:这些年来,英国文坛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1994年,我的小说也曾进入布克奖的最后角逐。那年的评奖就像一潭浑水,评委们意见极不统一。当年评委主席是约翰·贝雷(John Bayley),他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导师。那时有传闻说我会最终得奖,但最后还是没能得奖。其中一个原因,有人分析,就是因为我的小说涉及同性恋的内容,那在当时还是有些惊世骇俗的。这些年,情况有很大变化,人们的观念、态度改变了。年轻的几代人变得更开放,更宽容,人们更适应“同性恋”这样的概念,过去存在的歧视态度也没有了。尽管现状还不算完美,但和十年前比起来,已经有了很大改观。立法上的改变也是促进这一变化的一个原因,同性恋者在法律上的地位改变了,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自然也得以改善。现在内阁大臣如果是同性恋,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被迫引咎辞职。今年获奖的这本小说若放在十年前也许处境就不同了。
陆:保罗·莫内特的作品《成为一个男人》,关注了一个同性恋男子成长的困惑抉择,该作品在1992年就荣获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而今年您的获奖标志了布克奖三十六年历史上第一次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获奖。这意味着什么吗?
霍:在美国,同性恋这一话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更为政治化,我认为在美国,人们为同性恋的权益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斗争,而且要远远比其他国家规模来得大,更戏剧化。而且在美国,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也都更为政治化,这也许是由他们的性格、宪法和社会生活方式决定的。英国是个独特的王国,它是个岛国,它的宪法也不同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一讲到权益问题,对美国人来说它们立即变得无比重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便发生过许多为同性恋争取权益的斗争。而且美国有许多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它们都要比在英国发展得早,而且更完善。
陆: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E.M.Foster)1913写的颇具自传色彩的小说《莫理斯》(Maurice)也是关于同性爱,阶层等主题。这部小说对您有影响吗?
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以前没有人问过我。当我还在牛津读研究生时,研究过一些同性恋作家,他们当时都无法公开描写或发表关于同性爱主题的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写了我的论文。福斯特就是其中之一,大约在二三十年前,我对他很感兴趣。《莫理斯》是一部很勇敢的作品,尽管我不认为它写得特别出色,但是小说非常有意思,很能给人启发,而且我认为故事相当感人。在这部小说中,一位相当严肃的英国作家试图公开地就这一题材进行写作,这是文坛上的第一次,不过他当然无法发表这部作品,至少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莫理斯》的发表。也许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部小说一直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我是指,在我的前几本书中,我已经涉及到了同性恋的主题,我仍记得在我写第一部小说《游泳池图书馆》时,我试图以作论文时的主题为基础,我有意识地想谈谈当一个人无法公开谈论某话题以及能够谈论该话题时的意义。我当然也知道我无法完全无限制地描写同性恋,他们的作品,挣扎和喜好。当人们可以恣意写作任何他们喜欢的主题时,那些主题同时也就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试图拼凑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的生活,有些享乐主义似的生活。他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种压力,又都是非常苦涩的。我试图探索莫理斯的世界和现在这个世界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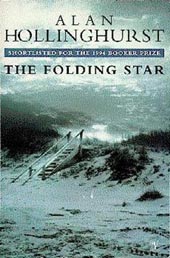
陆:在过去,如果同性爱在小说中被涉及到了,那它或是被抑制住,或是像编码那样隐藏在小说中,但是您的写作环境已经大为不同。比如奥斯卡?王尔德和您读的是同一所学院,但是您能够比他更公开地选择写作的主题。您对这一变化是如何看待的?
霍:我认为这一变化非常好,十分受人欢迎。奥斯卡·王尔德就像一名同性恋的烈士那样声名不朽,当然作为一位作家,他也永远为人铭记。他那时处于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而且一直到二十世纪后期,同性恋在英国的日子都很艰难。当然我是指在法律上合法化的这一方面,直到1977年局势才得以改变,因此1977年是个转折点。不过在那个年代,文学上并没有多大变化。当我在1984年开始创作我的第一部小说时,我的题材还是一个全新的主题,对我来说,更可贵的是这一题材并没有被文学理论讨论过。那一时期注定要产生变化。在多年来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看法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在那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同性恋在英国的法律地位上也有改变。每个人都更习惯这一概念,很多人都生活在这一新的时代,而人们的态度都得以改变。因此,现在这一主题没有以前那么吸引人,但是对于我来说,二十年前我还十分兴奋能就这一主题进行创作。现在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与这些变化相比,在文学中这一主题占的分量还是很小的,也许那些争取权益的运动也产生了一种迫切性,让它能以文学的形式发展起来。
陆:我看了一些评论性文章,许多都将小说简单化地说成是同性恋小说,由此为您的小说贴上了这一标签。但是我读了以后,我看到书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文化,社会阶层,美学等主题,并不单纯的是关于同性爱。您为何选择同性恋这样一个切入点,您将这么多层面的内容融合在一起想传递给读者什么信息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