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炸弹下的故事
作者:[英]杰妮·特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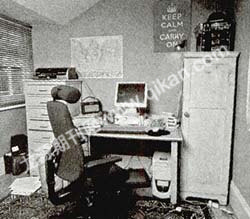
倒叙的结构,也给回忆以及它的那些反复无常的附属品浪漫与怀旧,安排了重要角色,虽然回忆并不可靠。我们看到凯在驾驶她的救护车,与此同时,朱莉娅和海伦初次相逢,并一见钟情,尽管其中的一个与别人有过约定。海伦,年轻的、更缺乏自信那一个,谈起她如何第一次和女性上床:那时战争刚开始,她只在伦敦呆了半年。“也许我该觉得不对劲,可当时一点都没有……后来,这么多不可能的事在那时都变得挺普通了。”对于海伦和朱莉娅,战时的伦敦街道和社会呈现出幻觉般的效果;通过两人的关系,沃特斯似乎想为她居住的城市写一首情诗,在这无序、脆弱、充满背叛的战争状态下,她却更加热爱这座城市。
海伦和朱莉娅热恋期间的一个夜晚,只有一束手电筒来照明,她们在午夜中漫步到城市的教堂——此刻教堂已遭战火摧毁。她们望着人们携带包和毯子钻到地铁站里,“他们可能是商人或小贩,从中世纪或战争中逃出的难民”。从桥上望去,河水沉沉地流淌,如此“漆黑”,“像一条隧道,像大地上的一条裂缝”。不知怎么,她们在伊斯特奇普迷了路,此时能感受到空袭警报带来的震颤;一道闪光使朱莉亚衣领上的针脚像是“从她的身体窜到空中,跳到海伦的眼里”。不久后,她们就首度拥抱在一起,躲在办公室门前一堆沙包辟出的一个很深的空间。两件打开的大衣合在一起像是道隔音墙,这一切比维多利亚小说中的色情更露骨,更现代。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恐惧”。只是纯粹的性而已。
邓肯的故事,虽然零散而不连贯,但还是让人吃惊的,他的故事是在道德层面寻求一种能推进整部小说的最后力量。罗伯特•弗雷泽是因为拒服兵役而入狱的。战争结束两年后,这个人物第一次出场,他一直在为慈善组织工作,帮助安置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
“你是不是在想,我和那些难民在一起,听着那些不想听的故事,知道别人在打仗,我却什么都不做,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感到厌恶,厌恶自己,不是因为我反战;而是因为仅仅反战是不够的……我厌恶,因为我身体健康。我厌恶,因为我还活着。”
弗雷泽是认真的吗?抑或只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谁也不清楚。
邓肯的故事标志着战争期间另一类型的错位。一方面,小说中的所有女性都在“冲锋陷阵”;另一方面,邓肯和弗雷泽却坐在苦艾丛监狱的囚室中。邓肯想,“在监狱里呆一个月,就像走过一条被雾气笼罩的街道:身边的东西你看得很清楚,可其他却是灰蒙蒙、白茫茫、无边无际。”他的内心独白就像是凯的夜间之行外化的翻版。犯人们没有防空洞躲避,也没有民防队员指挥;炸弹落下时,整个一段时间就没有警卫,犯人们互相辱骂,挥拳砸墙。有个囚犯想,如果能劝说德国人来轰炸这所监狱,那他可能会提前出狱了。“嘿,德国佬!”他叫喊道,“见鬼,这边!”。邓肯发现,如果空袭厉害的话,这喊声真是让你不安,“你会把齐格斯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磁铁,把天上的子弹、炸弹和飞机都吸引过来。”
读者们猜测邓肯可能是因为同性恋而入狱的;但真相要更复杂些。直到小说最后几页才真相大白,看到这个结果,会觉得一点也不合情理。但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有意义的,它把小说对性、遗憾、耻辱的挖掘与英雄主义和懦夫行经,还有战争有用与否联系在了一起。更进一步,这个结果也是合适的,它和学者们所谓的沃特斯作品的历史性有关联。战争期间,在米奇的驳船上举行了个晚会,“老实告诉我,”一个名叫宾奇,上了年纪的女同性恋,嘲笑凯说,“我们过的生活难道不曾让你们失望吗?……有时,我真的想找个可爱的小伙子安定下来——某个小小的自由党骑警,安静的人。”而此时,另一个人物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堕胎手术,由一个牙医操刀,干这行是他的副业。情况不对劲时,她大出血不止,又不敢去医院,因为她还没结婚,也因为堕胎是非法的。同这些女性一样,邓肯做了些在四十年代要受惩罚的错事,而现在(至少法律上)不会被惩罚了。因此,小说的宝贵之处,是代表了一系列尺度用来准确划分——按亨利•詹姆斯的分类——意识的“旧”和“新”。
由于小说采用了倒叙,故事的起点正好在结尾处,在那世界末日般的1941年第一次大规模空袭期间,在那个发生了一系列短暂的小爆炸、以及充满了令人窒息热量和强度的时刻。这些也为我们的主人公在小说开始时四处徘徊、俯拾碎片做出了解释。倒叙的过程也同样让原本可能虚无缥缈、令人压抑的故事在愉快的一刻结束,在大爆炸中,某些“清新、无瑕”的东西神奇般地被发掘了出来。小说结尾有些像《达洛卫夫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也有些像科妮莉娅•帕克的炸飞了的屋子(注:科妮莉娅•帕克,英国雕塑家、当代艺术家。《屋子炸飞》曾作为参赛作品。)。但却和马丁•艾米斯(注:马丁•艾米斯,当代小说家,代表作《时光之箭》的叙述手法独特,把“时光之箭”的走向反拨过来,使得时光倒流。)的《时光之剑》没有共同点,虽然两部作品都有共同的偏好,那就是目睹破碎的事物倏地返回,恢复原样。
这“清新、无瑕”的东西,出现在乱石、死尸、石灰,以及民防队员所谓的“一场惊慌”之中(其实是一只炸离了位的马桶,在黑暗中闪光),同样也把小说贯穿始终的的意象的图景连接在一起:从有关朱莉娅和海伦的那一段“与这一切灾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种温暖、生机和坚实……”可以看出来,不久之后,她们就成了恋人,徘徊在荒废、破烂的房子附近;也可以从“大自然战胜战争”的那个场景里看出来,正在喝茶的朱莉娅贴切地嘲弄道,“灾难中的新生活”这种想法听起来确实“没劲得要命”;要以空袭的时期伦敦为背景写一部当代小说可能也是如此。但是沃特斯化陈旧的主题为神奇。像一个有实力又有幸运的演员,沃特斯觉得自己与所写的东西好像有某种情感上的联系。
沃特斯生于1966年,正是二战结束后出生的那代人。书中所写到的生活可能永远不会是她自己的;但也不会离她很遥远。这些可能是她父母、邻居、祖父母的生活。大多数读此书的人会明白我的意思。大多数人也会明白那种感觉,当你看到旧时的照片、电影和书籍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便会涌上心头:那巴勒姆被炸毁的公车,在弹坑边缘摇摇晃晃;民防队员的声音悲哀而又温和,他引领你在帝国战争博物馆进进出出,虽然这个地方不脆弱易碎又令人感伤。回忆,滞留在那既遥远又清晰的脸庞和声音里,端坐在那遥不可及的边缘,诉说着每一天都无法逾越的距离。过去老是出现在眼前。但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