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二十九回 以道事君敢言晋职 遇礼而止解组归农
|
话说贾政年逾九旬,正欲具疏乞休。忽闻升了礼部尚书,又触着贾雨村当日偈言。心中忖了一忖,便问林之孝道:“此旨何处传来?”林之孝答道:“军机处的信,才送到内阁,报喜的人也就跟来,在门外尚未开发。小的出去,就打发他们哩。”贾政点点头说:“好。”
林之孝就退出门去。
贾政回到上房,王夫人先替道喜。贾兰带着众家人磕了头。
李纨、宝钗等带着仆妇丫环们,也行过礼。贾政、王夫人老夫妻甚悦。同到东府宗祠磕了头- 东府尤氏带着媳妇,也过来道喜。
赖管家领着家人仆妇,在阶上刚要磕头。贾政着贾兰吩咐免了。
周侯、薛宅早就来贺。各亲友无不送礼致庆。忙了有半个多月,才一一酬谢完了。
贾政次日入朝谢恩,即蒙召见。回家后述出面圣之事,方知这圣恩非无因而至的。那年贾政自山东办赈而回,圣上便把他名用纸御书,贴在无逸屏上。近因黄河累岁迁徙无常,各大臣条议具奏。贾政此时虽不在户工二部,然管过工部。
素闻贾环书来,备言利弊。现许各大臣自杼己见,遂据实条陈一折。大意以“水性赴下,而黄河之性更猛,挟沙石以俱流。而河南地势平衍,又系沙岸,最易冲决。仅资堵御,办料集夫,各处州县受其扰害,往往积日累月,将次合龙,费无限工力,耗不赀钱粮。一经溃决,皆归乌有。又复摊派通省,遂为河南一大害。
臣尝以千古善治水者,莫如神禹,尚弃数百里,分为九河,以杀其势,而不与水争利。何况此日之知能万不及一。徒藉捍筑,暂保片时,而不为经久之策。此河患之所以岁无息也。当查此日河势所趋,是否就下,顺厥性而导之,使东渐归于海,不扰通省之民,亦不塞难盈之壑。庶一举而永受其逸矣。“疏入,圣上大以为是。便触起书名在无逸屏上的旧事。恰值礼部尚书出缺,遂有此旨。
贾政到了任,约有两月,猛然想起贾雨村偈言来。取出一看,第二句写的“遇礼而止。”因念“天道日午则昃,月满必亏。盛衰起伏,相寻不已。自家官极一品,子孙鼎蔚,不趁此时退居林石,留有余地步以予后人,更有何疑?”主意定了,便与王夫人说知,王夫人亦深以为然。便不候贾琏及出差贾茂,那日进朝,于皇上召见时,便将自己年纪过衰,不能办事,若恋栈不肯辞位,恐贻误国事,则罪有所归,转不能沐皇上豢养天恩了。皇上优诏相留,未经许可。回府后,重行具疏入奏,恳请解职。
一连三次,皇上见其意诚、且怜其年岁实在衰迈,准令致仕。将那世职就给贾兰承袭。所遗礼部尚书员缺,即着贾茂升补。贾政磕头,面谢了圣恩。又赏了许多引年的食用等物,及过头鸠杖一根,准其在朝而杖,仿古制九十杖朝之义;加衔太子太保,以宠荣之,洵异典也。外赏上用大缎四端,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四对,珊瑚念头宝石背云迦楠数珠一盘,锦匣盛着。贾政又在午门谢了恩,递过职名在鸿胪寺,才坐轿回府。
周侯在书房中久候,贾政轿到,林之孝先即禀知。贾政便进书房来。周侯一见,连称“大喜!吾兄大人如此举动,全始全终,求之古人,亦不多得。小弟一早闻此信,心中替兄松快。专此候驾一谈。弟亦早晚陈情,与吾兄结一香山会,以继乐天之步。未知兄翁大人可容此俗客否?”贾政道:“弟因年逾大耋,恐误国是,遂有此举。兄齿尚健,且居散职,未兼部务,以见为藏,何所不可?”周侯爷道:“兄论甚是。但人各有志,也难执一耳。”贾政便叫摆酒,与周侯爷吃了饭,才辞去。
贾政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心无挂碍。直至红日三竿,方起来梳洗。把贾兰叫来,凡一切外头照应,皆着贾兰支付。非有要事,不必禀知。遂与王夫人商酌:将大观园靠西北面,离自家住的房子仅隔一栋房,只三间地面拆去,换个花园门,便可与稻香村相近。因把杏帘在望一带地界,皆用竹篱槿芭圈成一所,点缀三两处茅草亭子,有棕叶的,也有松溜皮的,颇涉野趣,不染纤毫俗尘。约有个月,工已告竣。中间小桥曲水,片石假山,无限树竹,皆是向来有的。贾政以为怡老之地,甚是欣然。
暑退秋来,忽报闵大人来拜。贾兰将帖子拿给贾政一看,上写着:“年家眷晚生闵鹏骞拜。”贾兰禀道:“闵师爷于四月升了工部右侍郎,今才到京。从朝上就来拜老爷的,会也不会?”贾政说:“岂有不会的理?”换了衣服,就到书房来。闵师爷迎出门,先作了一揖,说道:“老先生步履如常,精神照旧。为何便退居林下,岂不使朝廷少一辅弼?”贾政也还了—礼,道:“这顶纱帽有何穷期?古者七十致仕。以九十余岁一白叟,犹列朝班,岂不顾而自笑?先生尚觉弟致仕之疏以为早吗?”
二人说着话,走进书房。行了礼坐下,连辉端上茶来,喝过。闵侍郎道:“非论早晚,因见老先生健壮犹昔,晚生喜而出此言。为出为处,原无二致。这有什么着色相哩?”贾政道:“先生屏藩吴下,何时荣补冬官?弟真可谓退居畎亩,竟不知有此信。尊柬一到,小孙才为言及,多少缺礼处,先生统望包容。不识此日贵第可仍在旧处否?以便弟亲往一叙,用志旧雨。”闵侍郎道:“晚生仍寓旧舍,离此不远,最易盘桓。但晚生樗散余才,外任已不能胜,补此内职,经管工料,恐更稽察难周。望老先生朝夕训之,得免覆餗,便是晚生之幸。”贾政道:“先生何过谦乃尔!此地非说话处所,可到我新创一所闲坐地方逛一逛,何如?”闵侍郎道:“可好。”七十四儿引着,二人携着手,就曲曲折折,走入稻香村来。
大观园是闵侍郎熟境,那知一转竹桥,将到杏帘在望,迥非昔比:一带茅茨草舍,别有山林风味。一步一折,随步移形,几不知在城市。此时秋光满目,刈稻剥枣,陆续不绝。把个闵侍郎一片名心,涣然冰释。通身松快,足不知倦。
来到稻香村,也不是旧日规模。出檐灰棚十数间,并无青砖碧瓦,画栋雕楹。
然高敞爽垲,炉烟茶沸。真是别有天地。闵侍郎道:“老先生福人,生享如此福地。晚生何福,而得到此?这就是托老先生之福了。”贾政说:“先生过誉处,弟何敢当?”吩咐看茶。这个茶是贾政自饮的顶高龙井,一旗一枪,实系火前。
七十四用小茶盖碗沏了,同连辉端上。闵侍郎道:“晚生品茶多矣,初未尝得此仙味。满碗松花,未足道也。”贾政道:“此是龙井火前,较雨前尤细。水过熟则味逊矣。先生可谓得茶中三昧。”便叫备饭,说:“闵大人不是外客,就是寻常菜亦可待得。”七十四答应去了。
闵侍郎道:“晚生下朝,并未回家,实在饿了。老先生赏饭,晚生愿领,只求简而速,则善甚矣。”贾政道:“山肴野蔌,原无异品。先生要丰也不能够。”
说着,大家一笑。刚端出酒杯小菜来,只见贾兰又回禀道:“孙儿丈人闻老爷要会一会,孙儿来此请命。”闻嘉谟连年升了左副宪,与贾政时常会的。闵侍郎一闻此言,便道:“这个岂有因晚生在此,不会至亲之理?”便向连辉道:“连管家可去快请。”贾政道:“也好。”就叫贾兰去邀,便陪到稻香村来。
不多时,闻副宪进来。贾政同闵侍郎接出相见,彼此问候。
就同到屋内,坐下喝了茶。贾政就吩咐看酒,闻副宪道:“到此就扰,有此等不速之客么?”贾政道:“只恐不堪适口耳。如不嫌此菜根气,便日日过舍,以消闲昼。何如?惟恐国家有大议,非二公鸿才,谁敢专决。这是因私误公了。”
闵侍郎道:“老先生言及此,真令人俗不可医矣。”闻副宪道:“别管他,且敬一钟再议。谁许做此皮里阳秋之论。”贾政也只得笑了。
逊过座,三人就促膝而饮。头碗菜是碗炒蕨,味微苦而趣甚清。闵侍郎道:“老先生连用的食物纯乎高尚了!”第二碗杂素,是闻副宪最喜的,连吃了几箸,赞道:“妙绝!”贾政道:“菜非珍错,仅致剪韭献芹的微意罢了。诸位兄翁勿哂。”后来上尾鲜鱼,一盘果鸭,做法皆与往日不同。
贾政三位知己相对。话到深处,贾政因自述道:“弟承先人余荫,得蒙主眷。
少厕贤书,壮登仕版。经籍虽未研求,然居心待世,事事矜持。后来侧名卿贰,委任封疆,弥复谨慎。恐蹈愆尤,以负国恩而隳宗绪。今已九十二矣,才获致仕归农。可保终身无憾。嗣乃鼓腹康衢,与击壤之野人同歌化日,已自欣然。况逢二三知我,樽酒纵谈于片石孤松之下:转想半世尘劳,真如戏剧。绿野、耆英,古人不我欺也。“闵侍郎、闻副宪二人听了,同声说道:”盛德高风,洵堪千古。
弟辈得附香山之末座,则幸甚。“
后又端了碗南瓜上来,闻副宪心中自道:“此物索然无味。既端来,自有别致。”因举箸尝了一尝,便大赞道:“好极!闵先生,你快来吃。”遂同闻副宪便吃了数口,说道:“果然好。”又上了碗虾米白菜,更自洁净得味。闵侍郎便问南瓜做法,七十四把厨子尤瑛叫来,才知是鸡鸭猪肉,各样切碎,加上作料,挖空南瓜,用锡钴盖严,炭火煨熟,除去肉馅,单盛南瓜,所以味美而不见其迹。
闻、闵二大人甚喜,赏了厨子四两银子,不过取贾政一乐的意思。此是宦派,毋谓其真爱食南瓜也。不多时,二位吃过饭,嗽了口,又烹一壶好茶喝了。天已将晚,才辞回去。
贾政逐日吩咐熟习农事的老佃,预备诸样农器,明春在稻香村的闲田上耕种,修个菜园,灌园自娱。
冬初,贾琏、贾蓉到家,见贾政、王夫人,磕了头请安。将安葬的事细禀一遍,并坟上添盖许多房,治好些地,及沿途的应禀事件,备悉说了。贾政便将自己年迈请休,蒙恩准令致仕的话也说了一遍。贾琏说:“老爷年纪虽届杖朝,而精神康健,得以优游林下,侄儿辈曷胜欣慰。”正说着,薛蟠、薛蝌同来请安道谢。
贾政便叫请进上房,同王夫人一齐见了礼,再三谢沿途的照拂。
王夫人又问薛姨妈安厝的事情,落几点眼泪。说了回话,薛蟠兄弟到宝钗房内坐了坐,贾政留住,叫贾琏陪吃了饭,才教回去。
贾蓉自回东府。
这科武会试,全哥儿乡试时改名元煜,中了会魁。殿试技艺出众,策对轶群,就中了武状元。报到周府,喜的个周侯只是哈哈大笑。贺客盈门。荣府的外甥,薛宅的女婿,皆贴着报单,厚给了赏钱。大家欢喜。这报子连夜赶到浙闽制军辕门来报喜,周廷抡大悦,重赏报子。探春知儿子中武状元,心中甚喜。周制台连忙写折谢恩,周侯爷早已面圣谢了。周元煜钦点头等侍卫,圣眷着实加优,便就在京供职。
腊尽春回,土膏将动,乌庄头岁底交差。贾政教他二月间将善种地的人着一两个来京,是贾政亲口吩咐,庄头敢不留意?正月底,就送了两个人来。一个叫刘必显,一个叫叶子富。约四十上下年纪,林之孝禀了贾琏转禀,贾政那日正在稻香村内看阅农器,听见甚喜,就叫带他二人进来。林之孝把他领人,替贾政磕头。贾政问了姓名,便将阶下农器指着问他,并问其如何使用。
那二人一一指说,贾政未能骤解。适值贾兰在侧,说道:“他二人只能用此器而不能举其名,且乡下人的称谓亦多于古语不合。老爷若问其名而考所用,有毗陵陈椒峰先生所著《农具记》,最为详博。孙儿查出,与老爷一看,便明晰了。”
贾政甚喜,就叫:“你取来我看。”上写道:《农具记》:农之为具不一;而负牛之具曰犁。犁,利也,利发土绝草根也。《山海经》曰:后稷之孙叔均,始教牛耕。陆龟蒙《末耜经》云:耒耜通谓之犁,即《易》所谓斲木为耜,揉木为耒也。其制有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镵,曰犁璧。斲木而为之者,曰底,曰压镵,曰箭,曰辕,曰梢,曰犁,曰建,白槃。如是,而犁之事毕。
服牛之具曰轭。驱牛之具曰鞭。衣牛之具曰衣。牛于牧养中毛最疏,畏寒,每冬月编织冗麻衣之,如短褐。汉王章尝卧牛衣中,晋刘寔口诵手绳,卖牛衣自给。牛衣之制,最近古也。如是而牛之事毕。
耕田之器则有若耙,以耘也。有若臿,师古曰:锹也。有若锋,古农法云:锋地宜深,锋苗宜浅。有若搭,农家不尽有牛耕,尝数家为朋,工力相易,日可劚地数亩,以其齿劚士,如相答,故名。有若田荡,均泥之器,插秧用也。有若长镵,后伛而曲,上横木如拐,两手按之以起拨,杜少陵歌长镵者是也。有若钱,《诗》曰:“庤乃钱镈”,钱与铲同体而异名也。有若镈,《诗》又曰:“其镈斯赵,以薅荼蓼。”镈,迫也,迫去地草也。《考工记》凡器皆有国工,独无镈。 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不必国工也。有若耨,制与镈略同。有若耰锄,贾谊云:秦人借父耰锄是也,制又与耨略同。
如是而耕之事毕。
灌田之器,则有若桶,箍木为之,粪其田也。有若杓,亦箍木如盂,置之柄首,佐桶为用也。有若瓦窦,置塘堰中,致水使出亦使人也。有若筐,有若篮,郭璞云:一器也。所以实灰土,使肥田也。如是而灌之事毕。
藏种之器,则有若蓨,若蒉,器之从草者也。有若种,箪形,如甓,用贮谷种。庋之风处,不致郁浥,器之从竹者也。有若谷盅,编竹作围,长短无定,入谷中以通气,亦器之从竹者也。有若畚,晋王猛少贫贱,尝鬻畚,此也。南方以蒲竹为之,北方以荆柳为之。有若稻包,种之将布,浸之以水,俟其萌,而以草束为裹,俗曰稻包,无定制也。如是,而藏种之器毕。
布种之器,则有若瓠种。……贾政看到此句,忽见李贵持帖禀说:“闵大人有紧要事来会,小的已请在书房坐下了。”贾政便叫贾兰出去,急陪至稻香村来。
贾兰答应走出。贾政因《农具记》看的得意,便接着又看,上写着:窿瓠贮种,穿两首以木箪为贯,泻种于耕犁,随掩遏覆土。深则虽暴雨不至抱挞也。有若秧马……忽见贾兰陪着闵侍郎从外进来。贾政放下书,连忙接下阶去。闵侍郎瞧见阶下列着许多农器,便笑道:“老先生真欲明农子,但恐朝廷尚贤,未必能遂家食之愿耳。晚生来特报一事:今早见谢中堂,密言老先生有奉起用的恩旨,先来报信。老先生可谓受知独深矣!”贾政笑道:“弟年已衰迈,朝廷上纵需才孔急,亦断无再计及小弟的理。此言恐未必确。咱别管他,且请到草庐一谈,消此春昼何如?”
二人说着话,进了门,便就叙礼坐下。连辉送茶喝着,闵侍郎看桌上有本书,取来一看,是《农具记》,便指着说道:“此椒峰陈先生所著,注疏精确,考据渊博,诚古今不多得之笔。且托胎《尔雅》,而于昌黎《画记》外,另开畦径。
其中最警策者,‘臿’与‘长镵’二段,别有逸趣。再如‘稻床’及‘风车’数节,皆有玩索。至于‘桔槔’一制所云‘长木为箱,三面如墙,堵仰而缺,置小板数十如斗,而以木贯之如索,水间以架相承,岸横辊轴,二寸,木制如椎者十七八。又立横木,众人俯之而以足践椎,首尾旋转如辘轳,以引水而上田。’曲绘田家风景如画,此是何等笔墨!“贾政听了,连声说道:”先生可谓博考了。
此书弟尚未看完,不敢妄为评骘。“说话时,林之孝已将刘必显二人带出园去。
贾政要留闵侍郎小酌,闵侍郎说:“晚生尚有别事,须见甄巡制,就此别过。
明日再来道喜。“便就辞了。贾政要送,再三挽住。便叫贾兰送出大门,上轿而去。
贾政回到屋内,便叫七十四烹壶好茶。正喝着,忽闻枝头数声莺语,甚是好听。心地洒然,十分得意。便把《农具记》接着重又看去。见其“收获之器,如稻床、连耞等制”,惟风车一段,尤为奇古,颇觉得意。饮了数杯,又看了一遍,默然想道:“此书所记,可谓详博。但南方田具为多,施之北地则有不合。即如瓠种一器,北方则多撒种,继盖以粪,再掩之以土。或有用耧耩者。瓠种之制,从所未见。北方打场,多用石岫,间有连耞,亦不时用。况现在农器已多不符。”
遂将此书置于案侧。
适值王夫人着人送出饭来,数样皆是野蔬,一盂香稻米饭。
贾政甚喜,为王夫人能体己意,不似当年肉食气味,转为一饱。
连辉又斟上茶,才要去接,忽传有旨。只见林之孝忙走进来,禀道:“军机处有密旨,速传老爷同兰少爷一同进朝听旨。小的细问来人,不知何事。”
话未说完,只见贾琏同贾兰走来。贾琏道:“适才传言,老爷奉旨起用,可是真吗?”贾兰道:“现奉军机处传行,着孙儿同老爷入朝听宣,不与闵侍郎所言相同了?既经奉传,老爷当急入朝为是。”贾政道:“我已退闲,如何有此密旨?不知连日朝中可有何事。”贾兰道:“昨在衙门,正集议颁敕高丽,听说河抚有折入奏,并未发抄!亦不晓得何事。”贾政道:“既知不的,我闻君命不俟。
我虽解组,不可过迟。“便进上房换了衣裳,坐轿同贾兰急进朝来。
贾政一到,即有军机处司官带他祖孙二人,直到军机。宣了旨,才知是黄河今岁安澜,河臣奏到,因贾政前议行之有效,降旨褒嘉赐宴,晋职少傅,以彰懋眷,贾政谢了恩。传贾兰来随侍贾政,更属格外特恩。贾兰亦磕了头,跟着贾政领了宴,方才回府,阖府的人方放了心。贾政仍旧料理为农为圃器具,命刘、叶二人分职其事。
这一日,正在上房与王夫人闲话,忽然想起芝哥儿,一去海外,将及三载,杳然无信。虽属王事驰驱,王夫人未免伤感。未知贾政做何排释,且听下回分解。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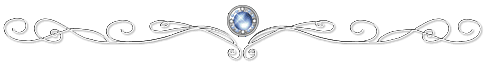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