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二十六 南 游
|
雍、乾之际的最有声望最得民心的地方大吏有二人:尹继善和陈宏谋。尹继善是满洲人,姓章佳氏,隶厢黄上旗,父亲尹泰,也是官至大学士,所以旧日文人的话是"两世平津";尹继善的女儿又嫁了乾隆的第八子永璇,国戚皇亲,家门贵盛。他的府邸就在京师西城大护国寺和什刹海之间的定府大街,府内有园,名曰绚春。 尹继善在雍正元年成了进士,只过了五年,便升任封疆要职、其时年纪不过三十多岁。他为人才干明敏,性情宽和,在雍正朝,仕风吏习专务苛刻的时候,他能不逐流俗,据记载说,有一次雍正对他讲授为官之道,叫他效法李卫、田文镜、鄂尔泰三个(这是雍正最赏识宠信的得意之人),尹继善却奏对说:"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他以精辟深刻的知人之衡鉴,对这三位宠臣巧妙地进行了批评,有胆有识,应对得体,连雍正也莫奈他何。
尹继善在雍正六年,就官授内阁侍读学士、协理江南河务;秋天,署江苏巡抚(次年"真除"),--这正是曹頫一家落职查抄的那一年。九年,尹继善已署两江总督。十年,协办江宁将军,兼理两淮盐政(任至十一年调职)。乾隆八年,再署两江总督,十年,实授(任至十三年)。十六年,复调两江(任至十八年)。十九年,又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实授(任至三十年)。一生四督两江。 尹继善初到南京,曹家正好刚已北返;不过他的总督衙院,就与曹家"老宅"相邻,自己又兼着两淮盐政,也是做着和楝亭一样的官。在南京一住,才日益体会到曹家祖孙数辈、历时六七十年之久、在江南一带的深得人心,远非一般俗常仕宦可比,而他家在文学事业方面的成就与影响深远,尤为大出原来的想象之外。尹继善对曹寅,本已久所心慕,至此,宦地相同,官职联属,自己也十分喜爱诗文书史,于是有意无意之间,都在学步楝亭,也作东南半壁的风雅主持。 在这种心情之下,尹继善自然留意于访询曹家的现况,子孙的下落。 中进士以前,尹继善曾在怡亲王府做过记室;后来曹頫是雍正交与怡王"照看"的。尹继善早年就已可能与曹家相识。大约到乾隆十九年再署两江总督时,他乘着搜罗人才的机会,决意务要跟寻楝亭的后人。而雪芹此时,编述《石头》一记,已经有了脂砚抄阅再评本。意在问世传奇的雪芹,正也想为书稿谋一个乐为出资刊板的东道主。两相凑泊,事不难成,尹继善爱才好士,礼聘情重,雪芹又可藉此重游童年故地,一举数得,就答应了前来请聘之人。 雪芹前往江南,似非一次,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南京好像已有他的足迹,所以二十二年敦诚寄怀诗句,正劝他不必远游--"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这显然不是一种并无缘故的闲文琐语,而这一年,乾隆有意改变对待汉族旗人的政策,准许包衣人开户出旗,可能是雪芹生平中的一次颇有关系的事件。但到了二十四年秋天,他由于生计的艰难,为了著作的传布,还是不得不下决心,再度前往。这时,有人对雪芹也加紧注意,在形势不利的考虑下,敦诚弟兄也同意了他的南游的打算,如此可以暂避风波,保全书稿,因此反而赞助雪芹料理南行的一切准备。 一到江南,雪芹的才华立即受到了尹继善的赏重,并以楝亭有此嗣孙引为欣慰。初时,宾主相得,情好甚笃。常在扬州的肖像画家云间陆厚信(字艮生)者,来游南京,曾入尹府,见到雪芹,十分倾慕,为他绘了一幅小照,并写下了五行题记,其辞云:-- 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 这就记录了一时的景况。
可是,雪芹的处境到哪里也是复杂的。这次南来的遭遇,有几件事使他更叹命途之乖舛。 正如敦敏赠雪芹所说的,"可知野鹤在鸡群",他的才华出众,易为人知,也易为人妒,同事中间,小人之辈,谮毁之言,久而遂多。尹继善虽然爱才好士,扬风■雅,但全是正统一派人物,眼见雪芹的一些言谈行径,渐渐心有不乐之意。尹继善是正人,倒出于一片好心,从他自己的正统观念出发,以为雪芹落到此等境地,是因无人"导之于正",他就要设法挽救雪芹,而雪芹对于这种"挽救",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根本不能接受。这么一来,各无恶意,皆本素怀,可是误会既多,彼此都无法谅解:别人本是一片热心为他好,而雪芹看来那是不能苟从的道路;雪芹如要自行我素,不肯污于流俗,就必然被人视为狂妄无状,负义忘恩。一个不能为世人所理解的伟大的哲士文豪,越是伟大,越是孤独,越是寂寞,--"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正是雪芹的最巨大、最深刻的悲哀。 雪芹本是为《石头》一记而仆仆南游的,不想最后事情也就出在这部书上。 这几年来,皇帝的主要的精力是花费在武事军情的调度上,但是使他颇为心烦的也还有文字科场,--"文治"方面的事情。乾隆二十年,胡中藻"诗狱"事件发生,中藻被杀。二十二年,段昌绪因收藏吴三桂叛清檄文、并加圈点评赞而伏刑,彭家屏因收藏明末野史,并其子皆处斩监候,家产籍没,家屏旋以撰《大彭统纪》赐死。更奇的是,到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命大学士蒋溥去向张照的儿子张应田家里查取张照的文字笔札,斥之为诗意怨望,文字狂诞,为一"丧心之人",竟说:"迨至再跻显秩,叠受殊恩,苟有人心,则从前肮脏(注:肮脏(kǎngzǎng),幸直刚正、不屈不阿之貌。曹雪芹写妙玉,曾用此词义,今人不解,乱加曲说。其实此词自古以来即如此音义,我曾引郑燮、潘逢元词中"飘零肮脏""风尘肮脏"为证,见《新证》页1055。乾隆此例,尤为显确。)激厉之词,亦当猛有铲削,而必将此刊刻流传,其居心又可问耶!"所以,对于"人心"的问题,一时颇为风雨满城,谈虎色变。 这时期乾隆皇帝不但"外头"事多,"家里"也觉烦心,皇八子永璇年少,不守礼法,最伤脑筋,他的师傅孙灏在二十三年已然得咎;二十四年秋天,永璇的岳翁尹继善也因为册送子弟乡试而不遵旨先自奏明,也受了指摘。到二十五年春天,为了加强管教,乾隆不得不亲"幸"永璇府第,意在察看。在清代,各种制度规定甚严,皇帝亲临臣子的住处,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所以史官必书。这次临幸永璇府,就是史册可征的。 正因如此,从早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极堪注目,那就是:乾隆有一次亲至某满人家,发现了《石头记》,并挟其一册而去(注:参看第三十二章。),以致某人大惧,急谋删改进呈云。--显然,这是《石头记》未有刊本、流传未广时候的事情。 从年代上推考,只有幸永璇府这一事件正相合符。 当乾隆查出身有"内病"的永璇竟尔偷看这种"邪书",自然十分震惊恼怒,决心要弄清这部"淫词小说"的一切原委。当这事的风波很快传到了水璇岳家尹继善那里,不觉目瞪口呆,--因为著书人就在他的幕席之间!由是,风声汹汹,人言啧啧 ,顿时大为紧张。尹继善毕竟还是厚道长者,不肯出卖楝亭的后人,就透消息给雪芹,让他赶紧托故离职,潜身他往,庶几可望避免多所株连,将关系的复杂程度尽量缩小。 于是,无可回避的雪芹,收拾行装,决意北返。 幸而永璇有力,多方弥缝遮掩,设法将事搪塞过去,一时未至酿成大案。这就无怪乎敦敏在重阳节后意外地与雪芹重遇时,立即写出了"秦淮残梦人犹在,燕(yān)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这种万分感慨、无限悲凉的句子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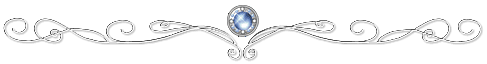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