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郑铁生:序言二(2)
|
我之所以举上述的例子,是想说明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的确是下了功夫,读了许多书。假如说争鸣的对方有一桶水,那么你就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否也有一桶水,争鸣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尽管作家审美视角与学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只要是学术研究,就为争鸣铺垫了好的前提。
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批评
理性原则是学术批评的规范。也就是说理性的学术批评,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坚持某一理论的个人,只批判理论本身;批评该思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批评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评其学术思想对该领域和社会的影响等。我在1998年曾发表过一篇评论红学家胡文彬的论文,其中特别写了一节关于学术争鸣的问题,对今天我们红学界的学术批评仍是有意义的。摘引如下:
红学界的 “霸气”主义早已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胡先生指出:他们“只准别人附和,不准另有异议,缺乏学术上的民主作风,大搞红学界内的‘霸气’主义,结果是谁也压服不了谁。相反扩大了矛盾,加深了隔阂,从学术之争发展到不正常的人事之争。还有的人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横扫一切,全盘否定别人的研究成果,以为自己最革命最正确。凡此种种由来已久,至今尚有余风。”历史上像这样“风”刮得最典型的莫过北宋古文运动后期。王安石当政废除诗赋取士而改试经义,并把自己主持编写的《三经新义》,以及他那部《字说》作为学校教材,致使文坛一度沉寂冷落。苏东坡继承欧阳修为端正文风而斗争的传统,对王氏新学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尖锐的批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为匡正文风,敢于力排时俗,直言相争,但并不由此贬低王安石,反而明确指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王安石也并没有因苏东坡的批评而引起彼此之间意见抵牾,而构怨积恨,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相反,在苏东坡落难时,爱才心切,胸无芥蒂,出于公心,相助于危。而当王安石罢相后,苏东坡路过江宁,拜访王安石,两人聚会金陵,同游蒋山,留连累日,唱和诗文,倾注友情。古代有苏东坡、王安石如此高尚的人品,近代有蔡元培和胡适的红学相争,但彼此推崇,共创新文化。从古至今学术之争是必然的,但讲究人品的高尚则是一贯的。所以红学界特别应当“提倡理解和宽容,对人要理解、要宽容,对学术也应该如此。”这是胡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讲述此问题的期盼吧。⑥
回顾八十年前蔡元培和胡适的红学论争,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除了学术见解不同之外,他们执着于学术探讨,营造争鸣的友好氛围,体现崇高的学者风范,都实在令人赞赏和钦佩。不能不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的素养、学习他们理性的范式、追崇他们为人的道德。
(一)学术观点的分歧
1917年1月辛亥革命元老、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胡适于1917年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授。胡适在北大,颇为蔡元培所倚重。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杀青后,蔡元培亲自为其作序,并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的出版为胡适在中国学术界赢得了声誉。他们两人的交往更为密切,除经常见面外,还不断书信往来,彼此关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蔡元培对《红楼梦》研究非常认真。《石头记索隐》一书,虽然不算太长,只有四万多字,但他却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是一部倾注心血的结晶。1917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是民国初年风行一时的一本“索隐”性质的红学著作。
《石头记索隐》提出:《红楼梦》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把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同清朝的人物、事件一一比附,如以贾宝玉影射胤礽,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宝钗影射高士奇,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维崧,刘姥姥影射汤斌(潜庵),等等。此外,他还将其索隐派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总结出了一套索隐的方法,即他本人所说的“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⑦。经过这种索隐法梳理之后,正如蔡氏本人所言:“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
针对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观点,1921年3月27日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 文章写成后,他还亲自送给蔡元培,听取意见。《红楼梦考证》批评蔡元培等人的“索隐红学” “走错了道路”,是“绝无道理的附会”,是猜“笨谜”,“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胡适说:“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我这篇文里,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⑧
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时,校长蔡元培正在国外考察教育。蔡元培将如何对待胡适的批评,是胡适和许多学人关注的事情。1921年9月,蔡元培回到北大,胡适将刊有《红楼梦考证》的亚东版《红楼梦》送了一部给蔡元培。蔡元培复信说:
《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⑨
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写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同样,蔡元培也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胡适听取意见,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承索《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奉上,请指正。”⑩
(二)学者的风范
蔡元培和胡适二人辩论内容本身存在着分歧,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我们姑且不论,仅就双方的态度和方式是在平等友善、随时沟通的气氛中进行,不失学者的风范,就令人钦佩不已。
胡适在《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中,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来表明自己论辩时的态度和立场:
讨论这个学说(指柏拉图的《名象论》)使我们感觉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是不得已把我们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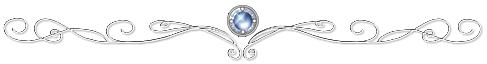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