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郑铁生:序言二(3)
|
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
在两人论争期间,蔡元培帮胡适借到了其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为胡适解决了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一些问题。胡适为此很是兴奋。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一)》,就是根据《四松堂集》对《红楼梦考证》所作的补充与订正,又写出《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文章末尾,胡适对蔡元培为他提供《四松堂集》特意表示了谢意: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两天,蔡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里借来的。……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之日。我寻此书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我手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对考证派另一位主要人物俞平伯的著作表示欣赏:“阅俞平伯所作《红楼梦辨》,论高鹗续书依据及于戚本中求出百十一本,甚善。”同样,胡适也把《雪桥诗话》借给蔡元培,让他了解其中所载曹雪芹情况。两人的这种雅量和胸怀是后世许多学人无法企及的,堪称学者的风范。
胡适晚年在回顾这场争论时曾颇有感慨地说:“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并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蔡元培晚年回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往事经历时,总爱提及胡适,显然他将引进胡适视为自己发现人才而自豪。
(三)辩论的成果
批评和论争是发展学术的必要方式。学术上的是与非,是在学者们的研讨、争论中才能辨清的。经过胡、蔡之间的论争,“索隐红学”很快在读书人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学术地位。胡适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形成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学派。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学术规范,为一门学科打开了局面,有力地推动了红学研究。1964年8月毛泽东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这个评语是客观的。
学术界普遍把《红楼梦考证》视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截至今日,胡适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论断,虽经百年时光的冲击、洗刷,依然是站得住的,有着里程碑的性质。从此新红学考证派为研究《红楼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其后的研究多是以此为起点进行的。
三、与刘心武先生争鸣的意义
我与刘心武先生争鸣,其意义首先在学术探讨,彼此补益,促进研究。
刘心武先生说:“我个人的研究方法,属于探佚学当中的考证派,我考证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现在进行这些考证,我觉得不好笑,因为脂砚斋鼓励了我,脂砚斋就说了,‘大有考证’。”
何谓探佚学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为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所作的序文中说:
他所用的论据: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笔、隐喻、暗示和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脂批”。从今天看,两者都是第一手材料。但是这一工作,却仍十分困难。因为伏笔、隐喻之属,需要猜,猜,就难保证十分准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处,要分析、辨别,才能用来印证。……但由于资料有限,而明确的资料更少,这就使得有些结论,猜测推论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满足。在这里,其意义便只限于提出问题,给出可能的设想……
姚先生说得很中肯,探佚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不仅先天不足,而且有一个界限。在界限之内,是探索曹雪芹创作思想的研究;超越这一界限,就容易滑进索隐的泥坑。探佚学只能止步于某些片断的探索上。而实际上这个界限很难把握,操作起来往往是“以贾证曹”与“以曹证贾”同时进行,交错使用,连环互动。以致当今考证与索隐合流,其实二者早就有扯不断的联系。对此表述最为简洁醒豁、深刻全面的,还是新红学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讲过的一段话:“索隐派凭虚,求工于猜谜;自传说务实,得力于考证……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正是这样做的,他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所以,蔡义江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研究可称为新索隐派。这是我们同刘心武先生之间的分歧之一。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研究是当今多元文化格局在红学中的反映,所谓“平民红学”这个提法尽管不准确,但它向从事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专业人士”发起一场挑战。这种文化现象说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胡文彬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指出:“红学家们应该从刘心武的现象中看到,在普及《红楼梦》方面,红学家还做得不够。为什么刘心武的讲座很受欢迎,那就是大众在对《红楼梦》知识的了解上还是有很多需求的。”又说,“研究者不应该只做学术,还应该想想怎么把学术的东西简单化,让更多的大众了解红学。”
刘心武文化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其讲授的内容所带来的隐性的负面影响,常常不会为大众群体所识别。所谓的“秦学”是经过多次的渐变而生成的,追溯其胎记,可以找到胡适“自传说”的胎痕,经周汝昌推向极至,又经过变构,及延至刘心武开创“秦学”。八十年光阴,潮涨潮落,轮番转换。恰如“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在肯定了文化的“道路是向前的”的同时也指出:“人类的思想和气质的全部广泛的历史领域证明……文化是以活生生的形态流传于世界的。它有时阻滞和停留在途中,它常常偏入歧途,这歧途把疲惫的它引向后退 ,引向它久远以前走过的地方”。他的话恰恰击中“秦学”的要害,“秦学”的问题集中表现在:
(一)刘心武的“秦学”是新索隐派“红学”,但它比同类型的索隐派对广大观众有更大的误导作用,是因为他将索隐、探佚故事化,以文学的感染力打动读者或观众。
(二)“秦学”与曹家本事合流,使广大观众更加信以为真,以为是在还原“曹雪芹的构思”。因为广大观众毕竟不是学者,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何况又是名作家说的。
(三)“秦学”解构了《红楼梦》的精神、意蕴和哲思,却以电视讲座这一大众化的消费形式去推广,以猜谜这种通俗的民间方式表达,颇受观众的欢迎。在悄悄而不为人所注意地向观众偷换《红楼梦》真正的审美价值。我将分章加以阐释,以期与刘心武先生互相切磋,碰撞出真理的火花。
最后,我认为同刘心武先生争鸣的过程,也是清理我的学术思想、锤炼我的思辨能力、提升我的写作水平的过程。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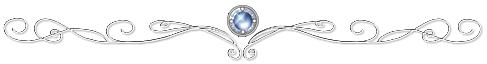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