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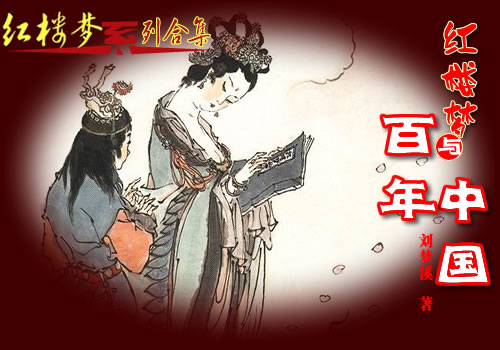
|
|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3)
|
这里,王国维不仅指出了叔本华哲学的“不能两立”的矛盾,而且认为叔氏的理论不能被事实所验证,甚至对释迦、基督是否真正解脱,随后也表示绝大疑问。他特地引录了自己的一首七律:“平生苦忆挈卢敖,东过蓬莱浴海涛。何处云中闻犬吠,至今湖畔尚乌号。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第2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其不相信解脱之意甚明,所以才有“终古众生无度日”这样的句子。研究者过去评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只看到在一些观点上受叔本华影响的一面,而没有重视静安先生此时对叔氏学说已发生动摇。《静安文集》的自序说得明白:“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此意于《叔本华及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参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自序。这番话系1905年秋天所写,当时静安先生正处于思想的转折期,已经从叔本华再次回到康德。因此《红楼梦评论》中的思想成分并不是单一的,对叔氏思想固有“可爱者不可信”《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之矛盾,具体剖解《红楼梦》这部作品,王国维也没有完全执著于叔本华的观点,而是以自己的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为根基,常常别有会心。
王国维明确提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就是他的会心独得之处。特别他把《红楼梦》置于传统文化之中,与《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作品加以比较,批评了几成套数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的充满乐天色彩的戏曲小说,进而对“吾国人之精神”亦有所反省。这用的既是比较文学的方法,又是从文化背景出发的评论,就小说批评而言,已达到相当的理论深度。叔本华在分析悲剧发生的原因时,谈到三种类型:一是由极恶毒的人造成的,如莎剧《奥赛罗》中的雅葛、《威尼斯商人》中的歇洛克;二是由于盲目的命运,即偶然性的错误所致,如《罗密欧与朱莉叶》,以及索佛克利斯的《伊第普氏王》等;三是由人物的相互关系和彼此地位的不同造成的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52页。。这最后一种尤值得注意。因为它不需要布置“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也不用恶毒已到可能的极限的人物;而只需要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把他们安排在经常发生的情况下,使他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他们为这种地位所迫明明知道,明明看到却互为对方制造灾祸,同时还不能说单是那一方面不对”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52页。。我国最常见的,就是这最后一种悲剧,可以说天天都在发生,只不过人们习以为常,觉而不敏罢了。王国维的深刻处,在于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自已地写道:
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
王国维揭明这种悲剧的特点是:随时都可以降临,每个人都会遭遇,而且身受其害,却又无法说出,所以是天下最残酷的悲剧。《红楼梦》就是这样,既没有蛇蝎一类人物左右全局,又不是由于出现了非常的变故,不过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结果却产生了大悲剧。这在美学上,更具有典范意义。叔本华说这种类型的悲剧在编写上困难最大,即使优秀的剧作家,也难免采取回避的态度。
可惜他没有读到《红楼梦》,否则一定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或许《浮士德》的例子就不值一举了。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可谓知音之谈——既是叔本华的知音,又是《红楼梦》的知音,其在美学上和小说批评方面的开创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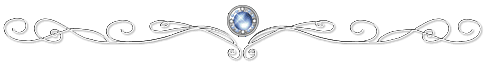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