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缘引(1)
|
“满纸荒唐言”,又对荒唐做文章,固然只是游戏笔墨,而却不能陶情适性。看官,笔者有自知之明,绝非贤哲之士,只是狂狷之徒。年应常珍而杖于朝,顾乃不识时宜,不作长铗之歌,不知地癖之利;且也,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草随风偃,入不能挥毫属笔,炫玉求售。其未曾绝粮于陈蔡,不能不感谢当涂的眷顾。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作者自幼就爱看小说。在古典小说之中,作者认为写得最好的共有三部:《红楼梦》第一,《西游记》第二,《水浒传》第三。《红楼梦》何以列为第一,待后再说,现在先谈《西游记》。
《西游记》也许有人认为谈神说怪,文学上毫无价值。余虽未曾研究文学,而看过文学之书并不少。《西游记》能够流传那样的久,那样的广,绝不是因为读者爱听鬼怪之事。《西游记》所描写的妖怪,各有各的法力,毫不重复,而其目标均集中于要食唐僧的肉。要食唐僧的肉是《西游记》的统一性;妖怪各显神通,无一雷同,是《西游记》的变化性。案吾人心理无不要求统一,即对于继续发生的现象,希望有一个中心观念,把各种现象统一起来。统一不是单调,单调是“类似”继续不已的现象,可令吾人发生厌倦,而引起不快的感情。世上多数现象都不是由单一部分构成,而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结合而成。部分愈类似,统一愈显明,故单就统一言之,“类似”确能适合吾人的心理。但是吾人心理除要求统一之外,又希望“变化”。“类似”只能满足吾人心理所要求的统一观念,同时却侵害了吾人心理所希望的变化观念。“类似”反复不已,部分将减少其印象力。部分的印象力既已减少,则部分所构成的整体亦必随之丧失印象力。故要保持现象整体的印象力,必须部分有复杂的变化。
一切情绪无不要求刺激之有变化。吾人听了一种音乐,倘令尽是低音,必定感觉沉闷,而发生沮丧的情绪。其声若有变化,由低而高,吾人的情绪虽然随之兴奋,而发生快感。但高音继续太久,吾人的情绪又觉躁急,而回归到不愉快的心境。《西游记》写到妖怪捉住唐僧及其徒弟,快要烹食之时,读者的心情不禁为之紧张,随着发生的竟是猪八戒的诙谐言辞,吾人心理突然轻松,往往捧腹大笑,这是《西游记》成功之处。读者只以神怪的心情去看,必谓《西游记》不登大雅之堂,要是以文学的眼光去读,必感觉《西游记》是一部幽默的著作。吾国任何文学均缺乏幽默感,《史记》的《滑稽列传》,不是幽默,只是讽刺。讽刺可令听者矫正其过失,也可以引起听者的反感。幽默不问言者之情绪为何,听者必为之绝倒,而解除心情的紧张或郁悒。猪八戒吃了人参果,而竟问行者、沙僧“甚么味道”,这已经脍炙人口,而成为一种俗语。唐僧四众行至平顶山莲花洞,遇到金角大王及银角大王二妖怪,行者令八戒巡山,八戒见山凹里一弯红草坡,便一头钻得进去,轱辘地睡下,那孙行者便变了啄木鸟把他弄醒。八戒找路又走入深山,见山凹中有四四方方三块青石头,猪八戒对石头唱个大喏,“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做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习哩。他道:‘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什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他问甚么洞,也只说是石头洞。他问甚么门,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他问里边有多远,只说入内有三层。——十分再搜寻,问门上钉子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此间编造停当,哄那弼马温去!’”(第三十二回),下面所写,尤其幽默,我不欲再引原文了。“那怪将八戒拿进洞里……老魔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八戒就绰经说道:‘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罢。’二魔道:‘哥哥,不要放他,把他且浸在后边净水池中,浸退了毛衣,使盐腌着,晒干了,等天阴下酒。’八戒听言道:‘蹭蹬呵!撞着个贩腌腊的妖怪了!’”(第三十三回)。老魔叫小妖把猪八戒解下来,蒸得稀烂,等吃饱了,再去拿孙行者报仇。旁有一小妖道:“大王,猪八戒不好蒸。”八戒道:“阿弥陀佛!是那位哥哥积阴德的?果是不好蒸。”又有一个妖道:“将他皮剥了,就好蒸。”八戒慌了道:“好蒸!好蒸!皮骨虽然粗糙,汤滚就烂。棬户棬户!”(第三十五回)老魔一口吞了孙行者,唬得猪八戒埋怨道:“这个弼马温,不识进退!那怪来吃你,你如何不走,反去迎他!这一口吞在肚中,今日还是个和尚,明日就是个大恭也。”(第七十五回)“二怪说:‘猪八戒不好蒸。’八戒欢喜道:‘阿弥陀佛,是那个积阴骘的,说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剥了皮蒸。’八戒慌了,厉声喊道:‘不要剥皮!粗自粗,汤响就烂了!’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格。’行者道:‘八戒莫怕……不好蒸的,安在上头一格,多烧把火,圆了气,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了气,就烧半年也是不得气上的。……’八戒道:‘哥呵,依你说,就活活的弄杀人了!他打紧见不上气,抬开了,把我翻转过来,再烧起火,弄得我两边俱熟,中间不夹生了?’”(第七十七回)。
猪八戒的幽默,只看上文所举数例,就可知道。然此不过数例而已,并非猪八戒的幽默全部。现今文人常把幽默(humour)与讽刺(satire)混为一谈。《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所举淳于髡等三人之言多系“反语”(irony),而寓讥诮或讽刺之意,不宜视为幽默。东方朔若不遇汉武帝,而遇明太祖,其挑拨诸儒,必判为造谣生事;其拔剑割肉,必受到扰乱朝仪之罚。在吾国,知道幽默的似只有吴承恩所描写的猪八戒一人。读者要研究幽默文学,可买一部《西游记》,细心地看。若不知幽默的本质,误把讽刺作为幽默,听者将斥你尖刻。
次谈《水浒传》,“迫上梁山”是《水浒传》的统一性,但是真正迫上梁山的,似只有林冲及武松两人。其他好汉或自愿落草,或为梁山所迫。故其统一性不甚显明。至其变化性并不比《西游记》为弱。同杀虎也,武松打虎(第二十二回)与李逵之杀四虎(第四十二回),写得完全不同;同是淫妇通奸,王婆说“十分光”(第二十三回)与石秀瞧到“十分”(第四十四回),亦是两样写法;武松亲自杀死奸夫淫妇与石秀怂恿杨雄杀死奸夫淫妇,毫不雷同;两次劫法场,其救出宋江(第三十九回)与救出卢俊义(第六十一回),写法并不一样。同一事件,写法均有变化,所以吾人读之,不觉厌倦。案梁山泊好汉共有一百零八人,施耐庵写林冲,写鲁智深,写武松,写李逵,均费了不少笔墨,又写得有声有色。苟一一均用这个方法去写,单单三十六天煞星,文字就要增加十余倍,而且免不了许多重复。所以写到最后,纵是重要人物,也只能草草了之。卢俊义在梁山泊之上,位坐第二把交椅,观《水浒传》所述,他不但不是豪杰之士,而且非草莽英雄。吴用下山卖卦,谓卢俊义有百日血光之灾,应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燕青尚知“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装做阴阳人来煽惑主人”。卢俊义“自送吴用出门之后,每日傍晚,便立在厅前,独自个看着天,忽忽不乐;亦有时自言自语,正不知甚么意思”,这哪里是英豪的气概?虽然快到梁山泊之时,取出箱内四面白绢旗,写下四句打油诗,表示他“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又准备下一袋熟麻索,要缚梁山草寇,“解上京师,请功受赏”(第六十回)。以一人之力何能战胜群雄?这未免太过自负了。大凡太过自负的人,往往不能知彼知己,而至失败。既为张顺所擒,送上梁山,宋江用软功方法,留住卢俊义约有两个多月,才放他下山。卢俊义回到北京,燕青告诉他,娘子已和李固做了一路,若入城中,必中圈套。卢俊义竟然大怒,喝道:“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第六十一回)其不明是非也如此。只因家巨富,“是河北三绝”,“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第五十九回),故落草之后,就坐第二把交椅,而为梁山泊的副领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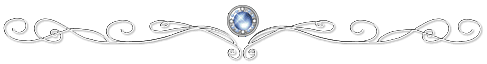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