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六章 人物造型的核心布局(6)
|
与睡者史湘云相反的是清醒者妙玉,连同其副本形象惜春。这是一种旁观者清的清醒,在惜春是“勘破三春”,在妙玉是看破红尘,然后的选择便是遁入空门。正如昏睡是一种极端一样,看破也是一种极端。建立在看破基础上的清醒是一种极端的清醒,所谓水至清则无鱼,极端的清醒与可爱的昏睡一样令人不无担忧。这种清醒在惜春虽然有与宁府诸色划清界线之意,但她面对侍画遇难时也同样冷漠无情。清醒到如此无动于衷的地步,实在令人怀疑是否真能清得了。所谓“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怀疑。“独卧青灯古佛旁”与“终陷淖泥中”的两种结局,只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而已。这样的空和洁,或旁观和清醒,如同一片耀眼的雪白,一不小心就会为污淖所染。如果说,贾宝玉形象区域是一片土黄色,林黛玉形象区域为一片鲜红色,薛宝钗形象区域呈现一种金粉色,史湘云形象区域展示的是天蓝色,那么读者在妙玉形象区域中看到的则是这么一种洁白,白得过于醒目,从而有点危如累卵。
同样的遁入空门,在妙玉形象区域和在贾宝玉形象区域就完全不同。贾宝玉的入空是由色而空,因此具有叛逆、挑战和毁坏、遗弃的意味,而妙玉和惜春的入空则是由空而空,在实质上是退却和逃避。贾宝玉的遗弃不是被俗世所弃,而是他抛弃了俗世;而妙玉惜春的遗弃则全然是被动的,不具备挑战性的。表面上看,她们通过遁入空门而保全了自己,但实际上却是放弃了自己。自我在她们的人生选择上不是以先行自身的精神前提或存在前提体现出来,而只是作为一种生命的结局或人生的归宿从内心退隐出去,至于寺庙在她们则与其说是通向灵界的空门,不如说是返回子宫的驿站。所谓“无为有时有还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无必须以有为前提,空必须以色为前提,出家必须以在家为前提,如此等等。从这样的道理出发,读者可以发现,妙玉惜春式的清醒乃是别一种形式的昏睡。湘云的昏睡是因为混沌未开,而妙玉式的昏睡则是开了混沌,“七窍开而混沌死”。由此可见妙玉式的昏睡首先不在于最终的悬崖撒手,而在于他的乐于成为当下在世的侍者,敢于面对寓于人世的沉沦。就此而言,他与林黛玉的那一缕情丝成全了他。相形之下,妙玉惜春却空得无情无色,从而最终难成正果。在整个小说中,妙玉的意义仅止于其命名的谐音藐玉,亦即对情爱的不屑一顾;而惜春的意义也仅止于息春,即大观园之春的终结。这样的不屑与终结,构成了妙玉形象区域的人物基调,从而与湘云的昏睡、宝钗的行为、黛玉的悲歌、宝玉的顽相互相映照。
依次展示了上述五个核心人物的形象区域之后,有必要进一步论述的是这五个区域的关联和运作。按照这五个核心人物的性格命运,似有三组关系值得细究。第一组是以玉命名的宝玉、黛玉、妙玉的连锁关系,第二组是宝黛木石前盟和宝钗金玉良缘的对立关系,第三组是宝玉和湘云、妙玉的两极关系;这三组关系的缔结形成和维系了大观园女儿世界,同样,这三组关系的分化则导致了这个世界的瓦解和崩溃。
以玉相连的三个核心人物的命名,正好表明了三种有关性爱的不同姿态,宝玉者,对情爱的珍惜和悉心照料也,亦即前文所说的侍者形象;黛玉者,对性爱的期待也,尽管这种期待由于还泪神话对性的象征性抽象而侧重于情感和精神的“意淫”,但毕竟还是一种对爱的追求和渴望;至于妙玉者,则如前文所说,乃是对性爱的藐视和远离,虽然在宝玉生日时妙玉忘不了送上贺帖,但这不过是一个观者的表示而已。这三种姿态标记了爱情在小说中的基本形式和指向,不是“滥淫”式的而是“意淫”型的,不是世俗的相好而是心灵的默契,不是指向世俗的、结果的、而是指向对爱情本身的期待的。在此,作为观者的妙玉虽然不卷入这场情爱,但她的存在却暗示和标记了宝黛之爱的“空”的性质。这种空虽然由色而空,但毕竟经过了还泪神话的抽象和净化。很有意思的是,性的内容在还泪神话中是以神瑛侍者之于绛珠仙草的浇灌这一极具象征性的动作表达出来的。正是浇灌这一象征,使空灵的“意淫”获得了色欲的基础,使充满诗意的爱情获得了生命前提。由色而空,在整个爱情故事中具化为由浇灌到还泪。由此又可以发现,黛玉之于爱情的期待不是作为当下的在世行为而是作为先行人物自身的生命前提出现在故事中的。因此,当我说宝黛爱情是向着期待的爱情时,同时也意味着这是一种向着生命本身的爱情。由色而空、由浇灌到还泪的过程将生命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期待,而爱情则由于这样的期待性质变成了一种性爱的乌托邦。在此,爱情的是否兑现不在于世俗的结局如何,也不在于期待有没有被满足,而就在于期待的过程本身是否成立。向……期待的爱情必定充满了操心和烦神,以至于泪雨涟涟;因此这种爱情的实现方式便注定不是洞房花烛夜式的圆满,而是焦首煎心般的残缺。妙玉的妙字与藐字的谐音,在玉字命名的连锁意味中,不仅表明了该人物本身的遁入空门,同时也提示阅读者注意宝黛二玉的爱情之于世俗的藐视和超越。这是以玉字命名的核心人物的连锁关系及其隐喻意味。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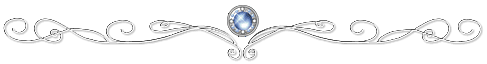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