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六章 人物造型的核心布局(7)
|
解读了这组关系之后,对第二组关系的解读也就可以顺理成章。所谓木石前盟,乃是贾宝玉命定的一场先行于自身以由色而空地实现自身的生死之恋;所谓金玉良缘,则是贾宝玉被抛入人世后而被强加的家族联姻。应该承认,贾宝玉在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时,他开始时并不是十分明了的,并且还受到过薛宝钗之丰润肌肤的诱惑,但他最终还是省悟了这种导向生命自身的爱情和作为被抛弃状态面对的身外之物亦即婚姻的根本区别。不管他在尘世沉沦得有多深,但其顽石本相是难以改变的。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的细节可谓意味深长: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
这与其说是宝玉在梦中喊骂,不如说是作为灵魂的顽石在梦中发言,而且还特意选择了薛宝钗像妻子似地坐在宝玉床边做活计的时刻。这个绝非偶然的细节表明,即便宝玉在沉沦中接受诱惑,作为灵魂的顽石也绝不会答应。或许正是在诱惑和本性之间的辗转反侧,才使宝玉痛恨自己那付臭皮囊。当下在世的贾宝玉就这样同时面对着先行于自身的木石前盟和寓世沉沦被抛弃的金玉良缘,这种状态给整个故事提供了无限的戏剧性,而贾宝玉本身的混沌未开又好比一个丧失了记忆的孩子,来到一个在他全然陌生的世界。《红楼梦》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如果可以把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看作是小说的主题故事的话,那么贾宝玉之于妙玉和史湘云这两极人物的关联就好比是故事的副部主题。妙玉的遁入空门,使她高高在上;湘云的蒙昧天真,使她昏睡于地;一如五行图式所示,妙玉水命,位在北上;湘云火命,位在南下;而贾宝玉居中无极土,其意味正好构成天、地、人的上中下结构。天是先行的,人是当下的,而地是沉沦的。经过一番生存的运行,当下的经由沉沦归于先行的自身,先行的被推入沉沦,而沉沦者则被先行所放逐;也即是说,人入空门,上天者入地,地上者被逐出伊甸园。在这组人物关系中,其意味在于此在结构的完整和残缺。贾宝玉居天地之间,既有先行于自身的存在前提,又处于当下在世的向……生存状态,并且是以一种寓世沉沦的方式,最终由色而
空,完成了自我的存在行程。相形之下,妙玉和湘云却呈现为二种不同的残缺形式。妙玉由空而空,由先行的前提进入前提的先行,结果空由于缺乏色的充分化而颓然落地。同样,湘云则于沉沦之地昏睡不醒,无以听见先行前提的召唤,及至大观园这一伊甸园瓦解,她的放逐就成了必然。或许“寒塘渡鹤影”的处境会使她有所省悟,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这种故事曾经在李清照的词境中有所写照,虽然“凄凄惨惨切切”,但毕竟有了“人比黄花瘦”的由衷感叹,一如林黛玉在《桃花行》中的吟唱:“帘中人比桃花瘦”。顺便说一句,史湘云和李清照在性格命运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所谓“寒塘渡鹤影”,几乎就是李清照在南渡时的心境写照。
正如读者可以在《怀古诗》和《五美吟》中读出小说的史识一样,在贾宝玉和妙玉、湘云的形象联系中可以领悟出作者的人生哲学。在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对立中,作者否定了婚姻的世俗性,但在妙玉和湘云的两种生存极端和贾宝玉的此在状态的对比中,作者则肯定了当下在世和寓世沉沦的必要性。可见,对世俗的鄙弃并不意味着对在世的否定,而是强调了一种去……存在的明确性。存在的诗意不是以放弃生存的方式体现,而是从向尘世的挑战中获得。古人所谓“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朝市”,其意同也。在此,生命并不因为先行前提的规定或者说审美的指向而封闭和退隐,而是由于这样的规定和指向而得以开放和张扬。正是由于这种开放和张扬,贾宝玉最终的悬崖撒手才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否定,一种挑战性的遗弃,一种把整个污浊的世界从自我存在中抛出去的心胸和气魄。相反,自以为空的妙玉却“云空未必空”,“终陷淖泥中”,而昏睡于地的湘云则“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两位少女的灵魂最终都无以着落。
小说中这五个核心人物的这三组结构关系,在形象塑造上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故事层面上构成了叙事的动机和主题,而在这三组关系的互相运作中则导致了大观园世界的解体和终结,并且以“飞鸟各投林”的方式。林黛玉作为“世外仙姝寂寞林”泪尽而归,薛宝钗以“山中高士晶莹雪”的形象如愿以偿,妙玉由天落地,由空而色,湘云由睡而醒,因醒就逐,最后群芳散尽之际,贾宝玉撒手入空,具体图示见上图:
在他们的结局中,除了湘云的放逐,其余正好分成两组散开,一是黛玉归天、宝玉入空,一是宝钗致俗、妙玉落世。归天者,仙也;入空者,佛也;致俗者,守寡耶;落世者,风尘耶?如果说这一切都命定如此,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说各自的归宿缘自各自的选择。命由天定,行却自为。人生仿佛一场游戏,角色是规定的,动作是自选的。茫茫此生,不过一个筋
斗翻过而已。行色匆匆之余,只来得及“哎呀”一声。作为《红楼梦》人物世界的核心布局,给读者留下的也许就是这么一声“哎呀”的惊叹和感慨。“哎呀”!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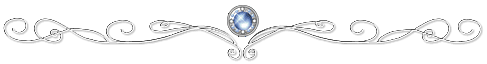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