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动人而又扑朔迷离
|
像我这样一个爱读《红楼梦》却又对“红学”一窍不通的人本来不应对“红学”流派问题置喙。《红楼梦》就够复杂的了,“红学”就更复杂。关于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行止,关于曹雪芹是胖还是瘦,肤色偏黑还是偏白的“曹学”研究,似乎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既渺茫又艰难却偏偏吸引着学子们的如此兴趣。关于《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同样令人惊叹。还有“京华何处大观园”的讨论,大观园是不是随园的讨论,肯定者指其必是,怀疑者惑其未必,肯定者、怀疑者与反对者都洋溢着一种热情,似乎大观园原址的确认与开发是一个比勘探石油或查访失散亲人还要令人动心动情牵肠挂肚的大事。
更不要讲索隐学派了。宝玉影射顺治皇帝,通灵影射玉玺,宝玉喜吃胭脂影射玉玺常盖印泥,“爱哥哥”——二哥哥说明宝玉姓爱,爱新觉罗氏也。香菱影射陈圆圆,薛蟠影射吴三桂。袭人即龙衣人影射李自成。晴雯影射史可法。晴是明上加一主字,是说上有明廷偏居南方的主君。整个《红楼梦》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蔡元培语),是一部呕心沥血、曲曲折折的反清复明之作。不信的人越听越觉得匪夷所思,信的人越钻越深越分析越有理越研究越有根有据其乐无穷自有天地非庸常人所能体会所可辩驳。
是不是有些考证太琐细甚至太没有意义了?或者是不是可以反唇相讥,一些“新红学派”太缺少做学问的功底与勤劳而满足于《红楼梦》社会意义时代背景的泛论?是不是索隐索出了猜测臆断“强迫观念”的毛病因而离开了文学作品的文学特性走火入魔?抑或拒绝索隐的人是否受了洋理论的影响反而放弃了索隐测字猜谜这一富有中国传统中国特色的心智活动的诱人乐趣?这些问题,笔者都不准备在此文中多谈。问题是,作为一个写小说与读小说的人,面对《红楼梦》这部了不起的小说,不能不想到它在小说文本以外曾经引起至今仍在引起的研究兴趣。除了《红楼梦》,古往今来,东方西方,好小说多矣,却不知道有任何一部其他的小说能这样粘着那么多聪明的、热情的、坚持不懈的——我甚至要说是偏执的考据与索隐的目光。对《红楼梦》的考据与索隐,已经成为一种我国文人的风雅与癖好,成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红学”如此这般,可以说是有着象征的意义的。《红楼梦》写得是这样真切动人而又扑朔迷离。《红楼梦》的版本又是这样基本一致却又各有千秋,同同异异,妙妙奥奥。《红楼梦》的作者,他的生平与创作,特别是关于这部传之万代的杰作的写作缘起与写作过程留下的资料又是如此之少。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简直是对于读者、对于评家史家出版家的一个挑战,一个嘲弄,简直令万物之灵的人与敝帚自珍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古往今来,中国有那么多作家作品,中国人知道那么多自己的作家与作品。偏偏是,人们对自己最最喜爱的作品《红楼梦》的有关一切、对它的作者曹雪芹知道得是那么少——如果不是一无所知。这是怎样的遗憾与怎样的吸引、怎样的诱惑!新发现一点关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史料,就像天文学家在茫茫太空发现一颗新星一样地诱人、令人兴奋不已。而这种兴奋,不正是说明我们已知的是多么贫乏得可怜吗?可怜的人们!越是不知就越希望有所知,越是有所知就越证明自己的无知。人类是多么悲壮,多么执拗,多么可喜可叹!这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呀!
是的,在这一点上,《红楼梦》的一切与我们的宇宙相通汇了。《红楼梦》好比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乡。地球家乡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都知道它却又都不能穷其究里,我们都议论它却又常常莫衷一是、各执一词。至少是谁也不能宣布自己已经完成了终结了铁定了对我们最熟悉的地球——家乡的认识。而有关《红楼梦》、围绕《红楼梦》的一切,那就是地球以外的宇宙空间了。我们正在欢呼人类在认识宇宙空间方面的进展,我们骄傲地称之为新的征服,虽然每一步征服都进一步使我们体会到那未被认识未被征服的领域的辽阔。这也是一种类型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曹雪芹呢?唯心主义者大概会想到那位很实在的木匠的儿子耶稣的在天之父了。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曹雪芹就像教徒希望更多地了解天父一样。也许我们能了解的,和他们能了解的一样多。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上帝造物的神话,但在巨大的世界的物质本源特别是人类的惊人的创造力的本源之前,不是也可以赞叹世界是不可以穷尽的、真理是不可以穷尽的吗?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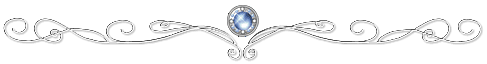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