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谒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对杜甫这两句诗,后人始终激赏不已。此外,诗人还以凤凰、高马自命:“凤凰从东来,何意复高飞。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饥。”(《述古三首》)“高马勿捶面,长鱼无损鳞。辱马马尾焦,困鱼鱼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三韵三篇》)以喻其志节操守。而王夫之则根据《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首诗,指责杜甫:“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余波。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薑斋诗话》)在这首诗中,杜甫极言当时在长安的穷困潦倒之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东汉向栩生性卓诡,有时骑驴入市,乞丐于人,但这只是佯狂之状,而杜甫则正像颜之推所说的那样,不幸在当时有些称誉,以至“见役勋贵,处之下座,以取残羹冷炙之辱”(《颜氏家训·杂艺》)。不过杜甫写这首诗,并不是效穷途之哭,而是在干禄求进,想以此博得韦济的同情,获得推荐汲引而已。这和他“独耻事干谒”之语,确实大相径庭。但若像王夫之那样,说这是诗人心术、气量败缺处,则未免厚诬前贤了。
潘德舆认为:“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养一斋诗话》)不仅杜甫,就是倜傥不羁的李白、生性倔强的韩愈,集中都有干谒之作。韩朝宗喜欢识拔后进,曾向朝廷推荐崔宗之、严武等人,所谓“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致“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李白《与韩荆州书》)。可见当时干谒风气之盛。韩愈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杂说》四)尽管马有千里之才,但只有先得到“伯乐”赏识,然后才能得到社会承认。故有进取心的士子,热中干谒,也就不可避免了。一方面为维护操守,以干谒为耻;另一方面为施展才能,又不得不走干谒之路。正是这种社会现实,造成诗人矛盾的言行。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在此,杜甫自言学优才敏,足以驰骋古今,并得到韦济的赏识:“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但是,杜甫不甘以词人自居,而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怀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希望。可是事与愿违,“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回首驱流俗,生涯似众人”。始终不遇于时。诗人向往的是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世界,但实际上却落入“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的境地,以致发出“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的悲愤之声。满腹牢骚,满腔愤激,冲口而出。看来,韦济对杜甫的“真知”,也只是赏识其诗而已,并无引荐之意,于是杜甫产生了怨望:“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并出现离开长安,从此摆脱羁縻、不问世事、遨游江湖之上的想法,故结句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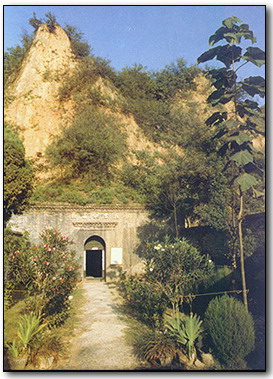 河南巩县一窑洞,相传杜甫在此出生 河南巩县一窑洞,相传杜甫在此出生
董养性认为这首诗“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而无干望请谒之私,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踬之中,英锋俊采,未尝少挫也”(《杜诗详注》引),未免誉之过甚。如果再联系同时所作的其他干谒诗一起看,更觉其言不实。正像赵翼所说的那样,杜甫在困居长安这一时期,“几于无处不乞援”,“若不胜其乞哀者”(《瓯北诗话》)。其中有些诗(如《投赠哥舒翰开府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词语卑下,情隘意慼,有不少违心之言。不过,前人对此往往采取谅解的态度,认为士当穷困之时,急于求进,干谒贵人,在所难免。如王嗣奭说:“是时李林甫、陈希烈当国,忌才斥士,无路可通,(哥舒)翰独能甄用才俊,不得已而欲依之以进也。”(《杜臆》)仇兆鳌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少陵之投诗京兆(鲜于仲通),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杜诗详注》)但像哥舒翰那样的人,其攻伐吐蕃,明明是杀人邀功,逢君之恶,杜甫在《兵车行》中曾作过尖锐的揭露批判,而在投赠诗中却极力称颂其功绩,待到日后安史叛乱、潼关失守后,又加以指责,前后乖戻未免太甚。白璧之瑕,众目共睹,这是谁也无法为贤者讳的。其实杜甫本人对此既不讳隐,也不辩解,置之集中,不加删削,这比起后来某些人文过饰非,篡改史实,欺世盗名,格外显得可贵。杜诗能成为诗史,杜甫能成为诗圣,有着众多原因,这应是其中不应忽视(但却常常被忽视了)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