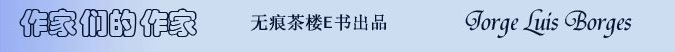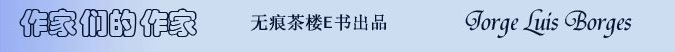|
作者:舒建华
80年代初,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席卷中国文坛时,中国外交官和翻译家黄志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拜访了博尔赫斯。在谈到"文学爆炸"时,博尔赫斯就预言:《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国际评论界把博尔赫斯称为"魔幻文学祖师爷",因为他在30年代就写过《叙事的艺术和魔幻》。对此说法,博尔赫斯对黄志良正色地说:"我不赞成'魔幻现实主义'的提法,这纯粹是评论家的杜撰。作家凭想象创作,虚虚实实,古已有之。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2000多年前贵国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
博尔赫斯青年时代就潜心研究过《庄子》,用的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思1889年的英译本。庄周梦蝶的故事使他大为神往,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向他的老师、阿根廷著名作家马塞多尼奥讲解,并在许多作品中提到它。《庄子》另一让博尔赫斯着迷之处是《天下篇》中惠子讲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博尔赫斯把它与古希腊芝诺飞矢不动的诡辩相提并论。在早年的《阿喀琉斯和乌龟永恒的赛跑》中,博尔赫斯写道:中国有个传说,说梁朝的皇帝有一根神奇的权杖,每传给继位的新君时,权杖就缩短一半。虽然随着君王更替,权杖会越来越短,但它永远存在。这个传说不见中国正史。中文版《博尔赫斯全集》的编者加了个注,说大概是博尔赫斯把惠子的妙论和秦始皇万世基业的宏图糅合在一起了,大概是博尔赫斯的创造。
博尔赫斯在40年代的《卡夫卡及其先驱者》(收入1952年出版的《探讨别集》)一文中说:"每一个作家都创造他的先驱者。"这样,庄子也成了被博尔赫斯创造的先驱。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博尔赫斯列举了卡夫卡的几位先驱,第一位是芝诺,第二位是中国"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证据是《获麟解》。博尔赫斯的这一高论遭到钱钟书先生的调侃(见钱先生六七十年代修订的早年写的《论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据翻译家罗新璋先生说,90年代当博尔赫斯在中国走红时,有一次钱先生不无得意地说,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引用博尔赫斯的。
博尔赫斯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文坛出现是《世界文学》1961年第4期的一则报道,当时译作"波尔赫斯",在"反映论"和"镜子说"火红的时代,报道引用阿根廷坎托对博尔赫斯的评论,说:"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
1981年《世界文学》杂志刊出了王永年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的三个短篇小说,这是博尔赫斯的作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在80年代,在中国,博尔赫斯是寂寞的,那时候,谈得最多、学得最多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和许多读者一样,现在还会背诵《百年孤独》开头的第一句话:"多年以后,当奥莱连诺上校面对行刑队的时候,一定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在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小说的结尾中,也有一个类似的场景,一个人面对行刑队的排枪。
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他没有写曲别针一样的时间,他很简洁:"四倍的枪弹打死了他。"
90年代末,作家余华,当年迷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个浙江青年,发现了博尔赫斯用的这个量词,他说,用"倍"代替"颗"的效果,就是想象,无穷的想象,任何一个我们想象得到的数,在这里,都要乘以四。那么,博尔赫斯的简短和宁静中,将是怎样的一场枪林弹雨。
(2000-03-14)
(中文版《博尔赫斯全集》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