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09章 老巴布意外到来
|

|
|
|
早上大约十一点时,贝合尼耶老妈来敲我的门。原来是胡尔达必要她来喊我起床。我跑到窗口,海港锚地风景壮丽非凡;大海非常清澈透明。阳光射下来,使它看起来像没底的镜子,海底的岩石、海草及苔藓历历可见。曼屯的海岸线相当优美,繁花遍地,将这片纯净水波包围住。卡拉凡的别墅有红有白,就像夜里刚绽开的鲜花;整座海格立斯城堡像束漂在海上的捧花,城堡的老石都散着花香。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动人的大自然景色,它是如此温柔惹人怜爱。天气非常晴朗,海滨游客悠闲懒散,一片水气笼罩海面,群山葱郁。这幅景色对我这个北方佬而言,是难得一见的,令我忍不住想触摸。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男人奋力拍击海面。哦!他的双臂轮流击水,我若是诗人,一定会流下眼泪!那可恶的人好像充满怒火,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他对这片平静的水波如此忿恨。很明显是这片海水勾起他的怒意,一直没停下来。他手持一枝短木棍,站在一艘小船上,船上有一个胆怯的孩童发着抖划桨前进。男人对着大海不停地乱打,他这种粗鲁火爆的举动,使几个驻足海边的游客非常愤怒,可是就如许多人在这类情况下会有的反应,他们自问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何必多事?于是就让他继续击水。这个野蛮的人究竟受了什么刺激?这片平静的海水,即使被这个疯子激荡起伏了片刻,也很快又恢复宁静了。
这时我听到胡尔达必的声音,他通知我正午用餐。他衣服上沾满了石膏泥灰,可见他在刚砌好的水泥墙边转过一圈。他一手撑在一根一米长的丁尺上,另一手拿着一条铅线。我问他有没有看到打水的男人。他说那是杜里欧,他打水是为了吓鱼,然后赶它们入网。我这时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居民叫他“海上屠夫”。
胡尔达必同时还告诉我,今早他问过杜里欧,昨晚他用小船载着绕了海格立斯半岛一圈的男人是谁。杜里欧说他不认识这个男人,这个奇怪的男人在曼屯上船后,付了五法郎,要到红岩岬头去。
我很快穿好衣服和胡尔达必会合,他告诉我午餐时会有一位新成员:老巴布。我们本应等他到时才入坐,可是他一直没出现,我们于是就在鲁莽查理塔布满鲜花的平台上用起餐来。
“岩洞”餐厅送来热腾腾的普罗旺斯鱼汤。这间餐厅的鲤鱼是这一带海岸最新鲜美味的,汤里还放了一些酒。露天用餐,加上景色怡人,使我们在胡尔达必采取防卫措施后的紧绷心情稍微放松。事实上,阳光普照时,拉桑就不似在星月微光的夜里那么令人害怕。啊!人的本性非常健忘,而又容易大惊小怪。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一想到我们整夜都保持警觉并武装巡逻城堡的道路,大家都觉得可笑。(至少瑞思及我是如此;还有艾蒂,她浪漫优郁的天性只是表面的。)
就在那时,老巴布出现了。而老巴布出现绝不会使我们失去微笑,心情低落——我很少看到比老巴布更滑稽的人。南部的春季阳光强烈刺眼,老巴布戴着一顶黑色高帽,穿着黑色礼服、黑背心、黑裤及黑眼镜散步;头发花白,两颊泛红。没错!没错!我们在鲁莽查理塔的棚架下笑得很开心,而老巴布也和我们一起笑;他生性就是很开朗快乐的。
这位老学者来海格立斯城堡做什么呢?是说出原因的时候了。为什么他会放下他在美洲的收集品、工作、图画和他在费城的博物馆?是这样的,读者应该还未忘记,瑞思在美国被认为是个前途无量的颅相专家,可是他对玛蒂的单恋使他突然厌弃学术。和艾蒂结婚后,她一直鼓励他,使他觉得学术仿佛即将重拾热情。刚好他们在蔚蓝海岸度蜜月时(也就是去年秋天),人人都在谈论艾柏先生在红岩的新发现,从1874年起直到现在,地质学家及史前文化专家都对在红岩岩洞里发现的人类遗骸抱着浓厚兴趣。朱利安、希维伊、吉拉汀及戴乐梭都来此研究过。法兰西科学院及国民教育部都很重视他们的发现。这些发现很快造成轰动,因为这些发现证明最早的人类在冰河时期前住过这里。当然,许久以前就有证据显示,第四纪时地球上已有人类。可是根据有些科学者表示,这个时期长达二十万年,如果能确定人类在这二十万年间出现的确切年代,大家一定很感兴趣。人们不断地在红岩挖掘并有许多惊人发现。可是此地最大的岩洞,当地人称为“巴玛大洞”,却没有被人挖掘过,因为这是艾柏先生的私人领地。艾柏先生在离岩洞不远的海边拥有一间餐厅。他决定自己挖掘这座岩洞。众人纷纷传说他在巴玛大洞发现了珍贵的人类遗骸(这件事已经不只科学界知晓),多具保存完整的骨架被埋在含铁的土里,它们的年代和第四纪的哺乳动物同期,甚至可上溯至第三纪末。
瑞思及艾蒂立即赶往曼屯。瑞思整日翻寻“厨房垃圾”(这是科学界的术语),甚至自己挖掘巴玛大洞的腐殖土,测量人类祖先头颅的尺寸;他年轻的妻子则乐此不疲地待在离岩洞不远的中古世纪城堡。这座巨大的城堡建在一座小半岛上,半岛靠着几块悬崖的落石与红岩相连接。这个热内瓦的古战场有着浪漫无比的传说,艾蒂愁思满怀地靠在平台高处,眺望这世上绝景,觉得自己像是史考特残忍冒险故事中的古代高贵仕女。那时城堡正待出售,价钱一点也不贵,瑞思就将它买下,这使他妻子满心欢喜。她请来水泥匠及挂毯、帷慢工人,三个月内,便使整栋古老建筑彻底改观,成为这位爱好《湖边女士》及《拉梅摩的未婚妻》的女读者的爱的小窝。
当瑞思看到从巴玛大洞新挖出的骨架及在同一地层发现的大象股骨时,非常兴奋。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电报给老巴布,告诉他长久以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巴塔哥尼亚寻找的东西,可能就在离蒙地卡罗几公里处。可是老巴布没收到这封电报。曾答应这对新婚夫妇会在几个月后踉他们会合的他,那时已搭上回欧洲的轮船。显然他已听说了这些发现,知道在红岩有宝藏。几天后,他在马赛下船,到了曼屯,和他的侄女及瑞思一起,在海格立斯城堡安顿下来。很快地,那儿便到处都可听到他愉快的笑声。
老巴布的好心情令我们有种戏剧化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前晚我们心情都很烦忧之故。老巴布有点返老还童,而且跟老奶奶一样爱打扮。但他很少变换衣服的式样,永远都一副严肃正式的样子(黑礼服、黑背心、黑裤子、头发灰白、两颊泛红),只是随时都很留心,要永远给人一致和谐的感觉。老巴布就是穿着这套衣服和南美潘帕斯草原的猛虎奋战;现在也是穿着同样服装在红岩的山洞里挖掘,寻找古代大象的遗骸。
艾蒂将他介绍给我们,他礼貌性地含糊了几句,接着便咧口大笑,连精心修剪成三角形的灰白颊髯都在抖动。老巴布狂喜万分,很快就告诉我们他高兴的原因。他在拜访巴黎自然博物馆后,证实了在巴玛大洞发现的骨骸,并没有比他上次从“火焰之地”带回的骨头更古老。法兰西科学院也同意他的看法,并肯定老巴布带到巴黎的大象髓骨是属于第四纪中期的。巴玛大洞主人告诉老巴布,在巴玛大洞发现的骨架和他发现的著名骨架,是在同一地层挖到的。他笑得合不拢嘴,好像听到什么笑话似的——在我们这时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够资格被称为学者的人,还会对这个第四纪中期的骨骸感兴趣吗?他的骨架——应该说是他从“火焰之地”找到的骨架,是第四纪初期的古物,比巴玛大洞所发现的早了一万年。听清楚了吗?一万年哩!而且他非常肯定,因为他所找到的骨架怀中还抱着穴居熊的肩胛骨。(他总说那是‘我自己的骨架’,他的狂热使他将自己穿着黑礼服、黑背心、黑裤子、灰白头发及红润脸颊的身体骨架,和在“火焰之地”发现的原始人骨架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的骨架是和穴居熊同期的,可是那个巴玛大洞的骨架……嘿嘿,孩子们,顶多和哺乳动物同一时期。不,还没那么早!只和双鼻孔犀牛同时期。所以,我们没什么好找了,先生女士们,双鼻孔犀牛时期而已!我老巴布向你们发誓,我找到的骨架是属于你们法国人所称的瑟利时期……你们笑什么,一群驴蛋!我还不肯定红岩的象骨会不会是莫斯特时期的,或许可能是更晚的索留特累时期,或是,或是更后来的马格德林期①呢?不,不,这太妙了!马格德林期的古代象骨!我快受不了了,我简直要疯了!我快生病了!啊,我一定会快乐死的!可怜的红岩!”
①编按:分别是1e Chellerien-le Mousteen-le Magdalerien,为旧石器时代的分期。
但是艾蒂无情地粉碎了老巴布的狂喜美梦。她向老巴布宣布,嘉利王子在买下红岩的殉情洞后不久,就有了新发现。这个新发现一定很惊人,因为老巴布去巴黎的那天早上,嘉利王子曾经路过海格立斯城堡,手上抱着一只小箱子。他把箱子拿给她看,并说:
“您看,瑞思夫人,这是一个宝藏!一个真正的宝藏哦!”
她问是什么样的宝藏,可是他的回答使她很生气。他说要等老巴布回来后给他一个惊喜!不过最后嘉利王子还是说了,他说他刚找到最早的人类头颅。
艾蒂的话还没说完,老巴布的愉悦心情就烟消云散了,满布风霜的脸上罩上一层怒气。他叫着:
“这不是真的!人类最古老的头颅是老巴布发现的!是老巴布的头颅!”他又吼道。“马东尼!马东尼!把我的箱子拿来这里,这里!”
正巧这时马东尼扛着老巴布的行李经过鲁莽查理庭院。他遵从老巴布的命令,将他的箱子提到我们面前。老巴布拿出他的钥匙包,跪在箱子前把它打开。这只箱子装了一些折叠整齐的衣物。他从中拿出一个帽盒,再从帽盒中拿出一颗头颅,放在桌子上,放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间。他说:
“人类最早的头颅在这儿!是老巴布的头颅!看哪!就是它,老巴布总是将他的头颅带在身旁!”
然后他拿起头颅,开始抚摸,他双眸精亮,再次笑着咧开厚唇。老巴布的法语很差,说起话来带着西班牙语及英语腔——他的西班牙语说得相当流畅。读者稍加想像一下,便可见到、听到这是怎样的一个状况!胡尔达必及我再也无法克制,捧腹大笑起来。比这更可笑的是,老巴布说完这些后,停住不笑,反过来问我们为什么如此开心。他的怒气使我们笑得更厉害,连玛蒂也在擦眼睛。老巴布和他的人类最古老的头颅真是太可笑,我们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虽然我们正在喝咖啡,但我觉得一颗有二十万年历史的头颅看起来一点也不吓人,尤其是如果它们的牙齿都保存得像这一颗这么完整的话。
突然,老巴布变得非常严肃。他用右手举起头颅,左手食指压着那颗人类祖先的额头,说:
“由上往下看这颗头颅,我们可看到很明显的五角形,这是头颅顶骨隆凸显著发育及枕骨突出所造成的!由于颧骨过度发展,所以脸庞非常宽广!而我在红岩发现的穴居人头颅上又看出什么了呢?”
我无法告诉各位他在穴居人的头骨上看出了什么,因为我不再听他说话了,我在看他。而且,我一点想笑的欲望也没了——老巴布看起来可怕极了,他的举止、他的科学知识、他的快活都虚假得不得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觉得他的头发在动!没错,像顶假发一样动着!一个想法,一个有关拉桑的想法不断地在我脑中起伏,占据我的思绪,就在我将要冲口而出说些什么时,有一只手握住我的手臂——胡尔达必把我带开了。
“桑克莱,你怎么了!”这年轻人以无比友爱的口吻问我。
“朋友,我不会告诉你的,因为你又会嘲笑我……”
他起先不回答,领我往西边大道走去。他环顾四周,看到左右无人后,对我说:
“不!桑克莱,不,我绝对不会嘲笑你的。你觉得到处都看到他,一点也不奇怪;如果刚才没看到,可能是现在……啊!他比石头更强,他比什么都强!我怀疑他不在外面……但愿那些用来防止他进入的石墙能帮助我将他围在里面……因为桑克莱,我觉得他就在这里!”
我握住胡尔达必的手,因为我也有这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拉桑的眼睛正在看我,我听得到他的呼吸声。从何时起我有这种感觉?我也说不出来,但这种感觉好像是随着老巴布一起来的。
我很焦虑地问他:
“老巴布吗?”
他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
“每隔五分钟,你就用左手握住右手,然后问:‘你是拉桑吗?’如果你回答了之后,还不能太有自信,因为你可能被骗了,他可能在你尚未知情的时候,就进人你身体了!”
胡尔达必说完这些话后,留我一人站在西边大道。后来杰克老爹来找我,递给我一封电报。在读它之前,我和他说,虽然他跟我们一样前晚都熬夜,可是他的气色真好。他解释道,他看到他的女主人终于寻到幸福,使他高兴得年轻了十岁。接着他问我为什么我们要他守夜,为什么胡尔达必来后,城堡中发生了那么多事;还有为什么我们如此警戒城堡的入口,不让外人进人。他还说,如果不是可怕的拉桑已死了,他会以为我们怀疑拉桑回来了。我对他说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如果他够勇敢,就应像其他佣仆如士兵般执行我们的命令,别去追究原因,更别和其他人讨论。他点头向我行礼,然后走远。很明显,他心里很困惑,而因为他负责守卫北门,倒觉得让他想着拉桑也不无好处。他曾经差点被拉桑害到,这点令他永志难忘,如此他会更小心看守。
我没急着打开杰克老爹交给我的电报。可是我错了。我一打开,看了第一眼,就发现我巴黎朋友发来的这封电报很重要。我曾请他帮我监视毕纽尔的举动,他告诉我,毕纽尔前一晚离开巴黎前往南部,他搭的是晚上十点三十五分的夜车。我的朋友还说,他相信毕纽尔买了到尼斯的火车票。
毕纽尔到尼斯做什么?我自问。在愚蠢的自尊心的驱使下,我什么都没跟胡尔达必说。这使我后来很后悔。我拿第一封他通知我毕纽尔没有离开巴黎的电报给他看时,他大大嘲笑了我一番,这使得我决定不告诉他毕纽尔离开的消息。反正对他而言,毕纽尔不重要,我也不愿“加重”他的负担!我自己知道毕纽尔的事就够了!这样决定后,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鲁莽查理庭院去找胡尔达必。他正把铁条固定在压住井口的厚重橡板上。他告诉我,如此一来,即使这口井是与大海相通的,如果有人想试着由井道进入城堡,也无法掀开木板,而必须打消这个念头。胡尔达必浑身是汗,卷起袖子,领口大开,手上拿着一只大榔头。我觉得他耗了太多力气在做这件容易的事,我便忍不住告诉他我的想法——就像一个弄不清楚状况的蠢蛋!我根本没想到这个男孩之所以拼命做工,是为了忘却一直在他心中燃烧的悲伤!半小时后我才了解到他的痛苦。我发现他躺在小教堂废墟的石块上,被睡眠击倒的他躺在这硬床上沉睡。他说了一句梦话,但我足以体会到他的心情,他叫着:“妈妈……”胡尔达必正梦着黑衣女子!他也许梦到自己像幼时一般拥抱她;跑得满脸通红到榆城小学的会客室见她。我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很忧烦地自问,是否该让他继续睡在那儿,而他在睡梦中又会不会不小心吐露秘密?但是,这句梦话已舒解了他的心怀,接下来我听到的就是如雷的鼾声。我相信从我们离开巴黎后,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睡着了。
我趁此机会离开城堡。没让任何人知道,很快我就带着电报,搭上火车去尼斯。此时我趁机读了《尼斯日报》头版的本地社会新闻栏:
桑杰森教授已抵达卡拉凡,将在阿瑟·瑞思先生府上待几个星期。瑞思先生刚买下海格立斯要塞,在美丽的瑞思太太协助下,他很开心能在这风景如画、充满思古幽情的地方热烈招待他的朋友们。我们刚知道教授的女儿——刚和达尔扎克先生在巴黎举行结婚典礼的玛蒂小姐,也和这位索尔本大学的名教授一起来到海格立斯堡。在外国旅客离开之际,这些新客人从北方来到尼斯,他们是对的!蔚蓝海岸的春天是全世界最迷人的!
到达尼斯后,我躲在车站餐室玻璃后面,窥伺从巴黎开来的火车。毕纽尔搭的应该就是这班车。就在这时,我看到毕纽尔下车了!啊!我的心坪然一跳,因为他没有告诉达尔扎克他会来这里。对我来说,这实在很奇怪!而且,我的判断是对的:毕纽尔躲躲闪闪,低头走在旅客中,速度好快,像小偷一样溜到出口。我紧跟在他后面;他跳进一辆有篷马车里,我也跳进一辆同型马车。他在马塞纳广场下车,走向防波堤散步道,在那儿叫了另一辆车;我一直紧紧跟着他。他的举动愈来愈可疑。后来毕纽尔搭的马车走上滨海大道,我也小心地走上同样的路。这条大道千折百转,左拐右弯,他没有发现我的行踪。我告诉马车夫如果他能紧跟着这辆马车的话,我会给他一笔优渥赏金,他做得非常好。我们后来到了宝瑠车站,毕纽尔的马车就停在站前,这使我有点吃惊。毕纽尔下了车,付钱给车夫后,走进候车室。他在等火车。怎么办?如果我跟他搭同样的车,他会不会在这小车站空旷无人的月台上发现我?不管如何,我必须试试看。即使被他发现,我大不了假装很吃惊的样子,然后光明正大紧紧跟着他,直到我知道他此行的目的。还好,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毕纽尔并没看到我。他搭上一班往意大利边境的慢车。总而言之,毕纽尔的行动指向海格立斯堡。我上了他后面那节车厢,而且监视每一站乘客的举动。
毕纽尔一直到了曼屯才下车。他显然刻意不搭从巴黎出发的火车直接来这里,而且挑了一个不会在车站碰见熟人的时刻抵达。我看着他下车,他将外套领子竖起,帽檐拉到眼睛上。他环顾车站一圈,肯定没人注意他后,快步走向出口。出去后,他搭上一辆等在人行道旁的老旧肮脏驿车车。我坐在候车室的一角监视着他。他到这儿做什么?他坐这辆破旧的车去哪儿?我问了一位站员,他告诉我这是去索斯贝城的驿车。
索斯贝是位于阿尔卑斯山最后支脉间的偏僻小城,风景相当优美,离曼屯有两小时半的车程,没有任何铁路经过。那是法国最偏远、最不为人知的一个角落,是政府官员最怕被调派任职的地方。此外,阿尔卑斯山的猎步兵营也在此。可是通往这小城的道路也是最美丽的一条。因为到索斯贝,不知要经过多少座山,绕过许多高耸悬崖,一直走到卡斯第庸卡黑山区的一座偏远山谷,有些地方景色粗旷荒凉,有些地方则是绿意盎然、繁花遍地、肥沃馥郁。从高耸入云的山顶到碧绿水波处,梯形山谷种满了难以计数的橄榄树,随风摇曳。几年前,我曾和一群英国旅客来到索斯贝,搭着一辆八匹马拉着的大马车。这次旅程留下的是令人晕眩的感觉。直到现在,只要提到这个名字,这种感觉就又回来,程度并没有减轻。毕纽尔去索斯贝做什么?我必须查清楚。这辆驿车坐满了乘客,已出发上路,发出了废铁及玻璃震动的声音。我和广场旁的另一辆马车做成交易,也去攀越卡黑山谷。哎!我已经开始后悔没有通知胡尔达必!毕纽尔的奇怪举动一定会使他想出一些有用和可推理的主意。至于我,我一点也不知如何推理,我只知道跟着毕纽尔,像一只狗跟着主人,警察跟着猎物般上路!此时绝对不能丢了这条线索,我快要有重大发现了!我让他的驿车超前一点——这是必须的,然后比毕纽尔晚了约十分钟抵达卡斯第庸。卡斯第庸位于曼屯到索斯贝路上的最高点。马车夫希望我让他的马休息一下,喝点水。我下了马车。这时,猜猜看我在通往另一处山坡的必经隧道入口看到了什么?
毕纽尔及拉桑!
我呆站着不动,好像突然入土生根了!我没有惊呼出声,也没有移动。我的天!这个发现如雷般将我击倒!过了一会儿,我才比较镇定。同时我对毕纽尔产生了恐怖的感觉,对自己则无限敬佩。啊!我就知道!只有我猜到这个恶魔会对达尔扎克不利!如果他们肯听我的话,这个索尔本的教授早就将他遣走了!毕纽尔是拉桑的杰作,拉桑的同谋!多么重大的发现!我早说过实验室的意外绝不是巧合!现在他们相信我了吧,我看到毕纽尔及拉桑就站在卡斯第庸隧道口交谈!我看到他们了,可是现在他们去哪儿了?我见不到了……他们当然是在隧道中。我加快脚步,把车夫留在那儿。自己走进隧道,手伸到口袋里拿着手枪,我好紧张!啊,我把这事说给胡尔达必听时,他会怎么说?是我,是我,我发现了毕纽尔及拉桑!
可是他们在哪儿?我穿越漆黑的隧道,没看到拉桑,也没有毕纽尔的踪影。我看着通往索斯贝的下坡路,一个人也没有。忽然,在我左方,往卡斯第庸旧城的方向,我好像见到两个黑影,动作好快,然后又消失了……我跑过去,我走到废墟停下来。也许这两个黑影正在我身后窥伺我?
卡斯第庸旧城已荒无人烟,这是有原因的。1887年的大地震摧毁整座城,城市差不多倒塌尽了,现在只剩下零星的几个石块。几座无顶破房被火烧黑,有两三根幸存的廊柱孤立着,忧伤地向地面斜倒。我的周围一片死寂!我如履薄冰般小心翼翼穿过废墟,它的裂缝深得吓人。1887年的地震使那儿的山岩裂缝处处可见。其中一道看起来好像无底井。我弯身向前仔细端详,手中扶着一株烧黑的橄榄树干。这时响起一阵拍击声,害我差点跌倒。我觉得有风拂过我的脸庞,我边后退边叫,一只老鹰如箭般从深渊飞出。它直向太阳飞升,然后我又看到它下降朝我飞来,在我头上不怀好意地打转,发出凶猛野蛮的叫声,好像斥责我打扰这个大地之火所赐予的孤寂死亡王国。
我是不是被幻影欺骗了?我再也看不到那两个黑影,是不是我的想像力又开了我玩笑?我在地上找到一张信笺,看起来像是达尔扎克在索尔本大学用的。
我从这张纸笺上读出两个音节,我猜是毕纽尔写的字,这两个音节应该是一个字尾,字的开头不见了,我只能从这张被撕过的纸头上读出“波内”。
两小时后,我回到海格立斯堡,把一切都告诉胡尔达必。他将这张纸放进皮夹,请我保守这次探险的秘密,不要让人知道。
我很惊讶这个重大的发现并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我看着胡尔达必,他掉过头,但他的动作不够快,我看到他双眼含泪。
“胡尔达必!”我叫他。
“桑克莱,闭嘴!”他再次叫我别开口。
我抓住他的手,他在发烧。我想一定不是对拉桑的顾虑使他如此激动。我责备他对我隐瞒了和黑衣女子间发生的事,但他不回答,就如以往一样,再次走远并发出长叹声。
众人都在等我们用晚餐,时间已晚。尽管老巴布的心情非常愉悦,但晚餐的气氛非常低沉。我们都试着掩饰冻住人心的可怕焦虑,好像顷刻间,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在威胁着我们,而悲剧随时可能发生。达尔扎克夫妇没有用餐,艾蒂则奇怪地看着我。十点,终于解脱了!是轮到我去园丁塔暗门站岗的时候。当我去会议室时,胡尔达必及黑衣女子从拱顶下经过,手中提着灯照路。玛蒂看起来异常激动,她恳求着胡尔达必,我没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我在这场争执中只听到一个字,胡尔达必说:“小偷!”接着,两人便走进鲁莽查理塔的庭院,黑衣女子向胡尔达必伸出双手,可是他没看到,因为他很快就走开,把自己关进房里去。她一人独自站了一会儿,靠在庭院里桉树的树干上,忧虑满怀,稍后才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回方塔。
那天是4月10号,方塔将在11号到12号的夜间受到攻击。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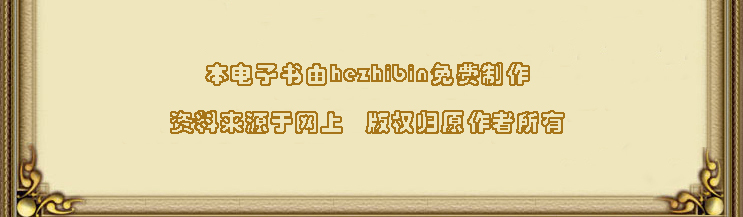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