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11章 方塔的攻击事件
|

|
|
|
我跑到他后面,抱紧他。我害怕他疯了,他的叫声中带有一种绝望的愤怒,一种呼唤,或可说是一种超越所有人类力量的求救声,我真害怕他忘了他只是个人,不能像鸟或箭一般,从这窗户飞出去,穿越这将他和罪恶隔开,而且满是他惊悸叫声的黑暗空间。突然,他转身把我推开,冲出房间,连滚带爬地跑过走廊、房间、楼梯、庭院,直冲到刚刚传出那和在走廊之谜一样之死亡叫声的悲惨城塔。
至于我,我还待在窗户前,那尖叫声使我无法动弹,我一直站在那儿。方塔门开了,在流泄出的光线里,我看到黑衣女子的身影!她站得直直的,虽然发出垂死般的叫声,但她仍活着!可是她苍白幽魂般的脸庞表露出难以形容的恐俱!她向暗夜伸出手,暗夜将她交给她的胡尔达必;黑衣女子的手臂搂住他,接下来我只听到叹息及低语声,还有两个音节一直在黑夜中重复着:“妈妈!妈妈!妈妈!”
我走到庭院,太阳穴发疼,心跳失序,肾脏无力。方塔门口刚刚发生的事一点也没使我安下心来。我试着以理性分析这一切,但没有办法。我跟我自己说:在我们以为失去一切的时候,一切不是全找回来了吗?儿子不是找到母亲,而母亲也找到儿子了吗?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她明明活得好好的,却发出死亡般的尖叫声?为什么她如此焦虑地出现在方塔门前呢?
奇怪的是,我穿越鲁莽查理庭院时,里面竟空无一人。难道没有人听到枪声吗?没有人听到尖叫声吗?达尔扎克在哪里?老巴布在哪里?他们还在圆塔的地下室工作吗?很有可能,因为我看到圆塔一楼有灯亮着。马东尼呢?他难道也什么都没听到吗?他不是守在园丁塔暗门吗?还有贝合尼耶夫妇呢?我看不到他们。方塔的大门仍开着,我听到温柔的低语声:“妈妈!妈妈!妈妈!”她则边哭边说:“我的宝贝!宝贝!宝贝!”他们完全失去了警戒心,连老巴布起居室的门都没关——她刚把她的孩子领进去。
他们两人独处在这个房间,紧紧抱着,重复说着“妈妈”、“孩子”,接下来,他们断断续续、有头无尾地说着一些再傻不过的话:“那么,你没有死!”当然!这很明显不是吗?可是这使他们俩又哭泣起来了!他们要拥抱多久才能弥补失去的时光呢?他要闻多少次黑衣女子的香气呢?我还听到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并没有偷钱……”他说这话的语气,仿佛他还只有九岁,可怜的胡尔达必。“不!我的宝贝!你不是小偷!宝贝!我的宝贝……”听到他们的谈话不是我的错,但我的心里万分激动,这是一个刚寻回孩子的妈妈啊!
可是,贝合尼耶老爹到底在哪儿?我向左转走进他的房间,我想知道是谁尖叫,是谁开枪。
贝合尼耶老妈在房里。里面光线昏暗,只点一根蜡烛。坐在扶手椅中的她像只黑袋子。枪声响时,她应该已上床了。她很快就披上了一件衣服。我靠前去看她,在烛光下,她的面孔明显地露出害怕的样子。
“贝合尼耶老爹在哪儿?”我问她。
“在那里!”她颤抖地回答。
“在哪里?哪里?”
可是她不回答。
我走开几步,突然一个踉跄不稳,我弯身看我踩到了什么:原来是马铃薯,滚得满地都是。刚才胡尔达必倒出来的,难道贝合尼耶老妈都没捡起来吗?
我站起来,走回贝合尼耶老妈身旁。我说:
“啊!对了,刚才有人开枪。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她答道。
不久我听到有人关上方塔的大门,贝合尼耶老爹出现在门口。
“啊!是您吗,桑克莱先生?”
“贝合尼耶老爹,发生什么事了?”
“哦,没什么,桑克莱先生,您放心,没什么……”他故意装得很大声、很勇敢的样子,好让我放心。“只是一个不要紧的小意外……达尔扎克先生把手枪放在床头时,不小心走火了。达尔扎克夫人很害怕,所以叫了出来。那时他们房间的窗户是开着的,她立刻想到您和胡尔达必先生一定会听到,所以马上走出方塔,要让你们安心。”
“达尔扎克先生也回房了吗?”
“你们刚离开方塔时,他就回来了,桑克莱先生。他进房没多久,手枪就走火了。我那时当然也很害怕,所以跑过去看,是达尔扎克先生亲自开的门,幸好没人受伤。”
“我们一离开,达尔扎克夫人就回房了吗?”
“几乎是马上。她听到达尔扎克先生开方塔门的声音时,就跟他回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是一起进去的。”
“达尔扎克先生呢?他还在房里吗?”
“哦,他来了!……”
我转身看,荷勃就在我前面。尽管房间的灯光很昏暗,仍看得出他的脸色惨白。他比个手势,我走向他,他说:
“听着,桑克莱,贝合尼耶老爹一定告诉你这个意外了吧!如果其他人没问你,你不用告诉别人,也许他们没有听到枪声,我们也不用吓他们,不是吗?对了,我要请你帮个忙。”
“说啊,我的朋友,”我说,“你知道,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我一定会做的,您希望我做什么?”
“谢谢!我只是想请您劝胡尔达必去睡觉,他离开的话,我太太就会静下心来休息。每人都需要静心休息的,桑克莱。我们每个人都得安静下来好好休息,不是吗?”
“好的,朋友,我会的。”
我发自真情握住他的手,这股力量代表我对友谊的真心。可是我确定这些人都隐瞒了一些事,一些严重的事情!
他回到他的房间,我也毫不迟疑,立刻去老巴布的起居室找胡尔达必。
我在老巴布房间门口遇到了正要离开的黑衣女子及她儿子。他俩都不说话,而且态度令人难解。刚才我听到他激动的情感,本以为儿子会投入母亲的怀中。可是不然,我站在他们前面,无法说话,也不知该做什么动作。这情形非常奇怪,黑衣女子竟急着离开胡尔达必!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发生了我不知道的事,还有胡尔达必居然就这样让她离开,我完全失去了头绪。玛蒂亲吻胡尔达必的额头,说:
“再见,我的孩子。”
她的声音疲惫忧伤,但很严肃,听起来像垂死的人在告别人世,胡尔达必没回答他母亲,把我带出城塔,全身抖得像片叶子。
黑衣女子亲自关上方塔大门。我确信在这方塔中,一定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他们对于这个“意外”的解释,并不能令我信服。如果胡尔达必没被他和黑衣女子的事冲昏了理智和心神的话,一定也和我一样!再说,谁知道胡尔达必想的真和我不一样?
一走出方塔,我就追问胡尔达必,我把他推到连接方塔和圆塔土墙的角落,就在方塔庭院突出来的转弯处。
这位记者像小孩般任我摆布,他低声说:
“桑克莱,我向我母亲发了誓,今晚方塔若发生什么事,我什么都不去看,也不去听。这是我第一次对她发誓。可是桑克莱,我宁可下地狱,也必须看到、听到……”
我们站的位置离一扇仍亮着的窗户不远,从这扇窗可看到老巴布的起居室及大海。这扇窗户是敞开着的,所以我们刚才很清楚地听到枪声及尖叫声,绝对错不了!虽然城墙厚实无比,而且由我们的位置不能看到窗后面有什么东西,可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就足够了,不是吗?
暴风雨已远,可是海浪仍未平静下来,还在不停地猛烈拍击海格立斯堡的基石,没有任何小船可能接近。我居然会在这时候想到小船,这是因为有一秒钟,我相信我看到了一个黑影,它出现没多久后就消失了,像是一条小船。我怎么了!这一定是我的幻觉,我把一切阴影都认定有敌意。我的心绝对比波浪还激动。
我们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差不多五分钟后,窗户传出悲叹声,掠过我们冒着冷汗的额头。哎!这声叹息既长又吓人!这深沉的低语,像是吐气,像是临终前的喘气;一种深刻的抱怨,遥远得像渐逝的生命,靠近得就像将临的死亡。然后,什么都听不到了……不,我们还能听到大海的咆哮声。窗户的灯光熄了,方塔一片漆黑,融入夜色中,我和我的朋友握手,借着这无声的沟通,我们控制自己不动,保持沉默。方塔里有人死了!一个被他们隐瞒的人!为什么?是谁?是谁?不是玛蒂,不是达尔扎克,不是贝合尼耶老爹,不是贝合尼耶老妈,更不可能是老巴布,而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在塔里的人。
我们伸长脖子,身子倾出护墙外,都快掉下去了。我们努力倾听那扇传出临终叹息声的窗户后面还有没有其他动静。一刻钟过去了,仿如一个世纪。胡尔达必向我指着他房间的窗户,里面的灯一直在亮着,我了解他的意思:必须去关灯,再下来。我小心翼翼地去他房里关灯。五分钟后,我回到胡尔达必身旁,鲁莽查理庭院的灯光也都熄了,只有一楼还有微弱的灯光亮着:老巴布还在圆塔的地下室工作。马东尼守卫的园丁塔暗门也有灯光。大致说来,我们确信老巴布及马东尼都没有听到方塔传出的声音,他们也没听到暴风雨即将结束时,胡尔达必在他们头上发出的怒吼:暗门的墙壁厚实无比;老巴布则在地下室。
我才跑回留在原处的胡尔达必身边,也就是城塔及护墙相接的墙角处,便很清楚听到方塔塔门的铰链在慢慢地转动。我正要从隐身的墙角将整个上身往庭院伸,胡尔达必把我推开,自己一人从方塔的墙后伸出头往庭院里望。由于他身体弯得很低,我便不顾他的命令,从他头上望去。以下就是我看到的景象:
首先我看到贝合尼耶老爹。虽然夜色黑重,我还是能辨认他的身形。他从方塔走出来,无声无息地朝园丁塔暗门走去。他在庭院中央停下来,望了一眼我们房间的窗户,又仰头看看新堡,然后转头向方塔打了个手势。那手势好像是表示安全的意思。他对什么人比这个手势?胡尔达必更往下弯,但他突然向后退,把我推开。
当我们再次窥看庭院动静时,那里已经没人了。后来我们看到贝合尼耶老爹走回来——其实应说是听到他回来,因为他和马东尼短短说了几句话后,回声传了过来。接着,在园丁塔暗门的拱顶下,我们听到了拖东西的声音。贝合尼耶老爹出来了,他旁边有一团慢慢前进的黑影。我立刻就认出是一台英式的小拖车,这是平时瑞思的小马托比拖的车子。庭院的土很松,这一小队人马没发出任何声响,就像在地毯上滑过去一样。托比又乖又安静,非常服从老门房的命令。贝合尼耶老爹走到井边时,又抬头看一下我们的窗户。然后继续牵着托比的僵绳,很顺利地回到方塔,他将马及拖车留在门口后,走了进去。几分钟过去了,我们觉得时间长得像几世纪——尤其是我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四肢又开始发抖了。
贝合尼耶老爹再次出现。他穿过庭院,独自一人回到暗门。这时我们必须更向前弯,现在如果有人站在方塔门口,一定会看到我们。夜色渐渐清朗起来,一道月光洒在海面上,照街一道长线,银蓝色的光芒一直延伸到鲁莽查理庭院。有两个人正要离开方塔,朝马车的方向走去。他们看到月色如此明亮,好像有点吃惊,向后退了一步。我们很清楚地听到黑衣女子的声音,她低声说:
“勇敢一点,荷勃,你必须勇敢起来!”
我后来和胡尔达必讨论,我们听到的到底是必须“勇敢起来”还是“勇敢去做”,但没有结果。
达尔扎克奇怪地说道:
“我不缺勇气。”
他有点佝偻地拖着一包东西。当他把它举起来要放在拖车板架上时,好像非常费力困难的样子。胡尔达必拿下帽子,两排牙齿格格作响。我们看出来那是个袋子。达尔扎克费了很大的力气在移动这个袋子,我们还听到一声叹息。黑衣女子靠在城墙旁注视他,可是并没有帮他。当达尔扎克终于将袋子放上车时,玛蒂突然惊悸地说:
“他还在动!”
“就快结束了。”达尔扎克回答她。
他擦拭额头,然后穿上外套,牵过托比的缓绳。他渐渐走远,向黑衣女子比个手势。可是她一直挨着墙,好像有人罚她站在那儿赎罪的样子,没有回答。达尔扎克好像比较平静,他挺直身体,稳稳地向前走,像是一个完成义务的诚实男人。他一直都很小心翼翼。等他和马车消失在园丁塔暗门后,黑衣女子也回到方塔去。
我想离开这个角落,可是胡尔达必硬是把我留在那儿。他是对的,因为这时贝合尼耶老爹从暗门走出来,再次穿越庭院,走向方塔。当他离塔门只有两米时,胡尔达必慢慢走出墙角,轻巧地闪进大门,站在被吓坏的贝合尼耶老爹面前。他握住老门房的手。
“跟我来。”他说。
贝合尼耶老爹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我也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贝合尼耶老爹在银色月光下看着我们,眼神非常焦虑,喃喃自语:
“真是太不幸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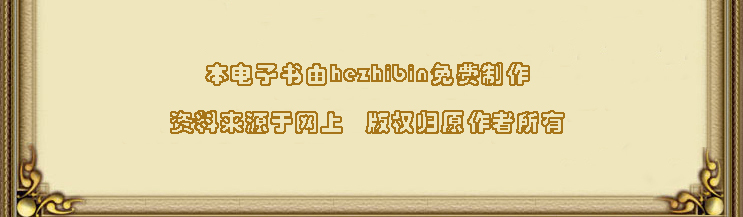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