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18章 死亡弥漫在日正当午
|

|
|
|
稍晚,我和艾蒂两人待在母狼塔的地下室。她既焦躁又担心,我试着安慰她,但没有用。她用双手盖住惊慌的双眼,双唇发抖,透露了她内心的真话:
“我好害怕!”
我问她怕什么,她说:
“您不怕吗?”
我沉默不语。真的,我也很害怕。她又说:
“您不觉得发生一些事了吗?”
“在哪儿?”
“在哪儿?在哪儿?就在我们身边呀!”她肩膀抖了一下,“啊!我好孤独!我好孤独,而且我好害怕!”她走向门口。
“您去哪儿?”我问她。
“我要去找人,我无法忍受一人独处。”
“您要找谁?”
“嘉利王子!”
“您要去找你的费欧多·费欧多维许?”我叫出来,“你为什么需要他,我不就在你身旁吗?”
不幸的是,当我试着减低她的忧虑时,她反而更加不安了。我很快了解到,她已经开始怀疑老巴布了。
“离开这儿吧!”她说,然后把我拉出母狼塔。
现在是中午时分,整个洪水区闷热得吓人。我们都没戴墨镜,只能用手遮着眼睛,才能避免被鲜艳的花朵刺痛眼睛,但我们脆弱的瞳孔还是无法躲避鲜血般的天竺葵。当我们较习惯这片缤纷的花圃后,我们走上焦炭般的地面,手牵着手走在灼热的沙地上。可是我们的手比沙还烫,我们好像被一团火焰包围着,我们必须看着自己的脚,才能不看到像无底镜一般的大海;也或许是为了不想看见阳光最亮处所发生的事。艾蒂重复对我说着:“我好怕!”我也是,我也很怕。昨晚的事情就已经让我很惊慌了,现在中午的死寂及艳阳更令我担忧!我们知道在阳光下发生的事比在黑暗中更令人担心!中午,所有事物都在休息,但也都活动着;所有的一切都不说话,但都发出声响。你的耳朵可清楚听到,就像大海螺发出的声音,比夜晚的一切发出的声音更神秘;合上眼皮,你会看到许多比深夜魅影更混乱的银色景象。
我看着艾蒂。她苍白的额头沁出汗水,马上变成冰冷的水滴。我和她一样打着冷战,因为我明白……唉,我无法为她停止我们周围正在进行的事;我们无法停止,也无法预测。她现在拖着我走向通往鲁莽查理庭院的暗门。它的拱门在耀眼的日光下看起来像把黑弓。我们看到胡尔达必就站在这阴凉走道的另一头,达尔扎克站在他旁边,好像两座白色雕像。他们转向我们。胡尔达必拿着瑞思的拐杖,不知为何,这根拐杖一直令我觉得很不安。他用拐杖指给达尔扎克看拱门上的某个东西,我们的位置太远,看不到是什么。接着他又用拐杖指向我们。我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话时,嘴皮几乎都不动,就如两个同谋在一起讨论他们的秘密。艾蒂停了下来。可是胡尔达必示意她继续前进。他又用拐杖比了一下。艾蒂说:
“哦!他又要做什么了?我的天,桑克莱,我怕死了!我要将一切告诉老巴布叔叔,然后看怎么办!”
我们穿过拱门,那两人动也不动地看我们前进,这种态度有点令人惊讶。我问他们: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我的声音在拱门下引起回声,令我耳朵很不舒服。
后来,我们走到鲁莽查理庭院的入口,站在他们身旁。他们要我转身背对着塔,看他们刚刚在看的东西。在拱门上端,有一盾形纹章,是摩特拉家族一支的纹章。这盾形纹章是用石头雕成的,这石块现在有点摇摇欲坠,随时会打在过路人的头上。胡尔达必也许是看到了悬在我们上方的这块石头,觉得危险,他征求艾蒂同意把它先弄下来,即使是以后再紧紧地黏回去也好。他说:
“我确定如果用拐杖碰这石头,它一定会掉下来的。”
然后他把拐杖交给艾蒂,他说:
“您比我高,您试试看。”
我们每人都试了,可是没有人能碰到这石头,它太高了。我正自问着这个奇怪的实验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时,突然在我背后,有人发出了垂死的尖叫声。
我们四人同时向后转,害怕地叫出来。啊!这尖叫声,这惊扰过我们多少个夜晚的叫声,竟在正午艳阳下响起!过去,我在葛龙迪椰城堡首次听到的叫声,何时才能停止向我们宣布又有一个新的受害者?如此迅速、阴险及神秘,有如瘟疫般!没错,连瘟疫的杀伤力都没有比这只杀人的手更明显!我们四人惊惶地打起冷战,目瞪口呆,站在跳动的光芒下问着:为何又有这种死亡的叫声?谁死了?或者说,是谁将死了?现在,是谁在喘息呻吟?这呻吟声好大。在这种光线下,谁能辨认出方向?那听起来像是白日的阳光在抱怨、呻吟呢!
最害怕的人是胡尔达必。以前我们经历过比现在更令人意外的时刻,可是那时他仍能够保持不可思议的冷静态度;我们也听过这种死前的哀嚎,他那时马上冲向阴暗的危险,像英勇的救生员奋不顾身跳入黑深的海中。现在日正当午,为什么他会抖得那么厉害?以前他都表现得像是能够主宰状况,但现在他站在我们面前,像个小孩般胆怯!他难道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分钟吗?马东尼这时正经过洪水区,也听到了,立刻向我们跑来,胡尔达必比了个手势要他停下来,在暗门下保持警戒。现在他朝呻吟声走去——应该说他走向呻吟声的中心,因为这呻吟声在我们前后左右四面围绕着。在这灼热的空间里,我们跟在他后面,屏住呼吸,双手僵直,好像在暗夜摸索前进,深怕会撞到看不见的东西。啊!我们快接近这个不停抽搐的男人了!我们走过桉树的阴影时,发现到这抽搐的男人就在树影的另一端。这个全身痉挛的人快死了!我们认出这人了——那是贝合尼耶老爹!是贝合尼耶老爹在呻吟着。他试着站起来,可是做不到!他快窒息了,血不断地从他胸膛涌出。我们弯腰看他。他在死前,用尽最后一股力气吐出几个字:“费得力克·拉桑!”
然后,他的头无力地垂下去。拉桑!拉桑!到处都有他,到处都看不到他!一直都是他,到处都找不到他!这是他的一贯手法:尸体躺在地上,而周围——非常合乎拉桑的风格——空无一人!这个行凶现场的惟一出口,就是我们四个人站着的暗门下。那时,我们四个人同时转身;当死者发出尖叫声后,我们立刻就转身了,照常理来说,应该可以看到凶手的举动,可是我们只看到日光!我们一言不发地走进方塔。我觉得我们有一样的想法。门是开的,我们毫不犹豫地走进老巴布的住所。起居室空无一人,我们打开他房间的门。老巴布很平静地躺在床上,还戴着他那顶高帽。一名老妇人在床边看护他,是贝合尼耶老妈!他们俩全都很平静!可是那可怜人的老伴,在看到我们的表情后,立刻有了不祥的预感,惊愕地尖叫起来。她什么都没听到!她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她要出去,她要去看,她要知道!我们试着拉住她,可是一点也没用。她跑出方塔,看到了尸体。现在,在中午难以忍受的暑气中,她对着流血的尸体痛苦地哀泣。我们扯开男人的衬衫,发现他心口上有道刀伤。胡尔达必站起来,他在葛龙迪椰城堡检验不可思议的尸体伤口时,也是这种表情。他说:
“看来好像是同一把凶刀!同样的大小!可是,刀子在哪儿?”
我们到处找凶刀,可是都没找到。凶手拿走了。他在哪儿?哪个男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可是贝合尼耶老爹在死前知道了,而且是为此而死!费得力克·拉桑!我颤抖着重复死者的最后遗言。
嘉利王子突然出现在暗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王子一边念报纸文章的内容,一边走过来,态度有点嘲弄。艾蒂抢下报纸,对他指着那具尸体,说道:
“这是刚才被杀的人,去找警察来。”
嘉利王子看看尸体,再看看我们,没说任何话,立刻就离开去找警察。贝合尼耶老妈低声哭泣着,胡尔达必坐在井上,好像已丧失了所有的力量。他以略高的音量对艾蒂说:
“那就让警察来好了!夫人,后果您自己负责!”
艾蒂的黑眼睛如闪电般盯着他。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恨死胡尔达必了!他居然使得她自己有一刻怀疑起老巴布来。可是,贝合尼耶老爹被杀时,老巴布就待在他房间里,而且是贝合尼耶老妈亲自看护的,不是吗?
胡尔必达很随便地检查了一下水井盖板,它没有被动过。他躺在盖板上,好像已经很久没躺在床上,好好睡一场觉了。他小声地说:
“您要跟警察说什么?”
“全部!”
艾蒂咬着牙关,非常愤怒地吐出这两个字。胡尔达必绝望地摇头,然后闭上双眼。我觉得他已彻底被击倒了。达尔扎克碰碰他的肩膀。达尔扎克想搜方塔、鲁莽查理塔、新堡及所有与这庭院相接的建筑物。没人逃得出去的,按逻辑来说,我在葛龙迪椰城堡的时候,当那男人不可思议地从走廊上消失后,我们会搜到什么东西吗?没有!没有!我们现在知道了,不能再用眼睛来找拉桑。刚才就在我们背后,有人被杀了。我们听到了他被杀时发出的惨叫声,但转过身时却只看到日光!若想看到什么的话,必须像胡尔达必一样,闭上眼睛。可是他现在不是睁开眼睛了吗?一股新的力量使他直起身子,他站起来了。他紧握拳头朝天空挥舞,他叫道:
“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我们推理有误!”
他突然伏下,四肢甸旬在地上,鼻子贴着泥巴,闻着每块石头。他在尸体及贝合尼耶老妈周围转来转去。我们试着将贝合尼耶老妈拖离她丈夫的尸体,但是徒然。胡尔达必又围着水井及我们每人身边打转。啊!真可以说他在这儿,就像是在泥浆中觅食的猪。我们在旁边,好奇、愚笨、阴沉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抓起一把泥土抛在空中,并发出胜利的叫声,好像就要用这把泥制造出拉桑的影像。这年轻人找到解开这谜团的新线索了吗?是什么让他眼神变得充满信心?是谁让他找回有力的嗓音?没错,他和达尔扎克说话时,音调又恢复正常了:
“请放心,先生,什么都没改变!”接着他转向艾蒂,“我们现在只等着警察来了,夫人,希望他们快点来!”
可怜的艾蒂又开始颤抖了。这男孩再次使她非常害怕。
“哦,没错,他们要来了,他们会接管一切,他们学查出来的!管它的,管它的,等他们来吧!”
说完,艾蒂挽了我的手臂。
突然,我们看到杰克老爹站在暗门下,后面跟着三个警察。他们是摩特拉地区的警卫队长及他的两个部下。嘉利王子通知他们后,他们就立刻赶来凶案现场了。
“是警察,是警察,他们说这里发生了命案!”杰克老爹叫着,他什么都还不知道。
“静下来,杰克老爹!”胡尔达必对他叫着。
看门人站在记者身旁气喘不停,胡尔达必低声对他说:
“杰克老爹,什么都没改变。”
可是杰克老爹已看到了贝合尼耶老爹的尸体。他叹气说道:
“只是多了一具尸体,是拉桑干的!”
“这是宿命!”胡尔达必反驳他。
不管是拉桑或是宿命,其实都一样。可是胡尔达必所说的“什么都没改变”是什么意思?自然是在说我们身旁,除了贝合尼耶老爹这具意外死亡的尸体外,所有令艾蒂及我怀疑害怕的未知物都还在。
警察们很忙碌,嘴里说着含糊不清的术语。警卫队队长告诉我们,他们已在这附近打电话到加里巴底客栈,凡提米尔的警察局局长正在那儿用午饭。他将马上展开调查,随后会有已得到通知的预审法官接手。
这位警察局长来了。虽然他没来得及用完午饭,心情还是蛮好的。一件杀人案,真的杀人案。他命令警卫队长派一名部下守着城堡门口,不能让任何人离开。一名警察领着哭得伤心万分的贝合尼耶老妈进入方塔。警察局局长检验完伤口后,以流畅的法文说:
“这真是高手干的!”
这男人很高兴,如果他逮到杀人犯的话,一定会恭维凶手的手法高明。他看着我们,仔细审视着,也许想从我们之中找出凶手,好表达他的仰慕之情。他站起来说: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碰到一起真正离奇的杀人案,高兴得不得了。他又说:“真是太令人难以相信了!难以相信!我当警察局长五年了,从没碰过杀人案!预审法官……”
他说到这儿时停住了,可是我们都知道他要说的是“预审法官一定会很高兴”。他拍拍黏在膝盖上的白沙,擦拭一下额头,重复说着:
“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他的南方口音更加强调他的惊讶。他看到有一个人走进庭院,是曼屯的医生,他来这里再次治疗老巴布。
“啊,医生,您来得正巧!快检查这道伤口,告诉我你对这刀口的看法!尤其是,如有可能的话,在预审法官来之前不要改变尸体的位置。”
医生在检视伤口后,告诉我们一切重要的专业细节,没有任何疑点。刀口很深,由下往上,刺破整个心脏,也伤到心室。当警察局长和医生讨论时,胡尔达必一直看着艾蒂。她是更握紧我的手,想逃进我的怀中。她眼睛躲着胡尔达必的眼睛,他在催眠她,命令她闭嘴。相反,我知道她一直想开口。
警察局长请我们进入方塔。我们全到了老巴布的起居室内。警察局长要在这房间询问众人。我们轮流告诉他我们所听到及看到的。贝合尼耶老妈第一个接受审问,但没什么结果。她说她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像疯子般进方塔来时,她正在老巴布的卧房,照顾伤者。她已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多钟头。她丈夫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忙着搓绳子!奇怪的是,此时我对眼前发生及听到的并不怎么注意,我只关心我看不到的,我等着……艾蒂会将一切说出来吗?她直盯着房间的窗户。有名警察待在尸体旁,尸体脸上盖着一条手帕。她和我一样,对在回答警察局长问话的人漠不关心,继续看着那具尸体。
警察局长一连串的惊叹声令我们的耳朵很难过。在听取描述命案的过程时,这位意大利警察局局长很明显地愈来愈惊讶了。他的直接自然反应就是:这桩命案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这整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时轮到艾蒂被询问了。
她正准备开口回答时,我们听到胡尔达必平静地说:
“大家看桉树树影的那头。”
“桉树树影那头有什么?”警察局长问他。
“凶器!”胡尔达必答道。
他从窗口跳出去,走进庭院。在那些沾血的石块中,捡出一块尖锐发亮的石头,拿到我们面前。
我们认出来了:那是“人类最古老的刮刀”!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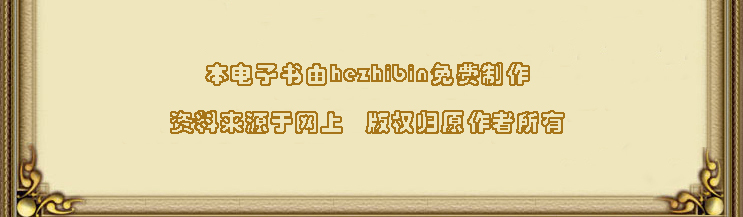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