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尾声
|

|
|
|
尼斯、坎城、圣拉斐尔、土伦……回程中的我一点也不眷恋这些从我眼前掠过的站名。噩梦结束后的翌晨,我迫不急待地想离开南部,回到巴黎好埋首于工作。此外,我很想和胡尔达必单独相处。现在他和黑衣女子就坐在我附近。直到火车抵达马赛,他们必须分开的最后一分钟,我都不愿打扰他们亲密感伤的细细私语、他们对未来的计划、他们最后的告别。胡尔达必不顾玛蒂的百般要求,坚持要离开,继续在巴黎的记者工作。他的英雄气概使他决定不去扰乱达尔扎克与玛蒂的生活。黑衣女子无法使他改变主意,只好全都听他的。他要达尔扎克夫妇继续他们的蜜月旅行,把红岩的意外当做没发生过。虽然旅行开始时,和她在一起的不是现在的达尔扎克,但现在将由这个达尔扎克继续幸福的旅程。对所有人而言,只有一个达尔扎克,没有变过!达尔扎克夫妇结婚了,在民事法律上他们已经结合。至于宗教法律,就像胡尔达必说的,他们可以和教堂达成妥协。他俩若觉得内心有些顾忌的话,可以去罗马,想办法使他们的婚姻正常化。达尔扎克夫妇现在很快乐,真的很快乐,这是他们努力赢来的!
这么多年后,刑事时效己过,我们不必再担忧法庭诉讼会引起的一切烦扰,若不是我因不得不公开在红岩发生的神秘事件—一一如我揭露葛龙迪椰城堡事件时的情形一样——而写下这篇文章的话,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多出人体袋子的悲剧。说起来,这事全要归咎于那可憎的毕纽尔。他知道许多事情,而且逃匿到美洲某处企图勒索我们,威胁要发表诽谤的文字。如今因为桑杰森教授已经辞世,我们不须再顾忌对他的打击,所以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公布真相。
毕纽尔在这第二桩恐怖事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悲剧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坐在回巴黎的火车上,在不远处的黑衣女子及胡尔达必两人泪眼盈眶地搂着对方时,我仍在问自己这问题!我将额头靠在卧铺车窗的玻璃上,心里想着许多问题,而胡尔达必只要说一个字,一句话,就能使我完全明白。可是从昨夜起,他根本没有心思想到我,从昨夜起,他就没和黑衣女子分开过……
我们在母狼塔时就和桑杰森教授道别了。达尔扎克立刻出发前往博地格拉,玛蒂将去那儿与他会合,瑞思及艾蒂则陪我们到火车站。艾蒂并没如我希望的,对我的离去感到难过。我将她对我的漠不关心归罪于嘉利王子的在场——他也到月台来送我们。艾蒂和我谈起老巴布的状况,说老巴布很好;之后,她便再也没来理睬我,我为此真的很难过。现在,我想我该向读者坦白了。几年过后,瑞思死了,加上随后发生的一连串悲剧,我娶了棕发忧郁的艾蒂,若不是如此,我是绝不会在此向各位泄漏我对她的感情的。
我们接近马赛了……
马赛!
他们的道别真令人心酸,他们什么都没说……
火车开动时,她仍站在月台上,保持不动,手臂微晃。穿着一身黑纱的她,像座哀悼悲伤的雕像。
在我面前,胡尔达必的肩膀抽搐个不停。
里昂到了!我们因为睡不着,便到月台上。记得几天前,我们曾经过这里,那时我们急着前去帮助那不幸的女人。我们又陷入悲惨的回忆中,现在胡尔达必开口了,他拚命说话,很明显,他要借此忘了那使他像孩童般痛哭好几个小时的痛苦。
“老兄,这毕纽尔是个下流胚子!”
他说这话时带着责备的语气,好像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人似的。
接下来,他便将一切都告诉我。如此重大的事,写起来只有短短几行。原来那时拉桑需要找一个达尔扎克的亲戚合作,想把达尔扎克关进疯人院。他找到了毕纽尔!这简直是最好的人选,这两个男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即使在今天,我们都知道要把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疯了——关进情神病院是多么简单的事。虽然这事看来不可思议,可是在法国,只要有一名亲戚的同意及医生证明,就可以完成这种勾当,既迅速又简单。对拉桑而言,签字是雕虫小计。他签了一个假名,付了毕纽尔一大笔钱后,交给他去办。毕纽尔到巴黎时,就已经是拉桑的同谋了。拉桑的阴谋是:在婚礼前便取代达尔扎克的位置。就像我猜想的,那场眼睛的意外不是真正的意外。毕纽尔负责尽快使他的眼睛受伤,这样拉桑在玩他的伪装游戏时,就有一张王牌——墨镜!不方便戴墨镜时,他也自然而然可以待在阴暗之处。
达尔扎克的南部之旅,更方便了两个恶贼的诡计。拉桑从头到尾都在监视他。等他要离开山雷摩时,才施展诡计,将他绑入疯人院。这勾当自然借用了某些专替不想张扬“家丑”的家庭办事的“私人机构”之助。这些人办起事来利落得很。
有一天,达尔扎克在山上散步,疯人院就坐落在这山中,离意大利边境不远,一切早已安排就绪,要迎接可怜的达尔扎克。毕纽尔在回巴黎前,就已和院长达成协议,并介绍给院长他的代理人,也就是拉桑。有些疯人院院长,只要一切合乎法律程序,还有付的钱够多,并不需要许多的解释,这笔交易于是很快就达成了;再说,这种事几乎天天发生,并不稀罕。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我问胡尔达必。
“朋友,你记得吗?有一天在海格立斯城堡,你交给我一张小纸条。那天你没惊动任何人,一人独自跟踪来到南部的毕纽尔。那张写着‘波内’两个音节并印有索尔本大学抬头的纸条,对我助益非浅。首先,由于那纸条是在拉桑及毕纽尔会合的地方被你发现的,它因此成了很珍贵的资料;而在我确定多出的人体是达尔扎克,而他已被装进袋子运走后,我因此决定去寻找他的下落,这时,你拾到纸条的地点,便成了很重要的线索。”
胡尔达必以最清楚的方式,让我了解他查清这谜团的过程;其他人却一直到了最后都还搞不清楚。首先,是干涸的红色颜料使他清醒的,接着是两个达尔扎克之一的谎言。胡尔达必在运走袋子的男人回来前,盘问过贝合尼耶老爹,那时他就知道那个大家以为是达尔扎克的男人的谎言!这人在贝合尼耶老爹面前虽然很惊讶,却没有告诉贝合尼耶老爹,下午五点时要他打开门的达尔扎克并不是他!那时他已试着隐瞒第二个达尔扎克出现的事。而他隐瞒事实的原因,惟一的可能是因为,那个达尔扎克才是真的,他不能让人发现真的达尔扎克!这个事实简直和白天的阳光一样清楚!胡尔达必被点醒了,这件事实使他恐惧极了,他原希望是贝合尼耶老爹弄错了,也许他听错了达尔扎克所说的话,误会了他所表现的惊讶。胡尔达必决定亲自询问达尔扎克,弄个水落石出!啊!只有达尔扎克才能合上论证圈圈的范围!他等得心急如焚。当达尔扎克回来时,胡尔达必还存着渺茫的希望问他:“您看到他的脸了吗?”这个达尔扎克回答:“不,我没有看到他的脸。”胡尔达必再也不怀疑了,满心喜悦,因为拉桑大可说:“我看到了,就是拉桑的脸。”这年轻人却不知这就是这恶贼最狡猾的地方。他这故意的疏忽正合乎他扮演的角色:真正的达尔扎克一定会这样做,他会想尽快摆脱尸体,一点想看的欲望都没有。可是拉桑再多的花招都敌不过胡尔达必的推理分析,胡尔达必一个猜测就够了。这个假达尔扎克在被胡尔达必询问细节时,就已将谜题解开了。他撒谎!现在胡尔达必看出来了,他理智的眼睛现在看到了!
但是他要怎么办?立刻揭穿拉桑的真面目吗?他有可能会立刻逃走;而且他那再次嫁给拉桑的母亲,会知道是她亲自帮助拉桑杀了达尔扎克。不!不!他必须深思、了解及策划!他要等确定了才行动,他需要二十四小时。为了保证黑衣女子的安全,他要她住在桑杰森教授的房间,而且私下要她发誓绝不离开城堡。他骗拉桑,让拉桑以为他确信老巴布有嫌疑。华特将袋子拿回城堡时,他心中又燃起希望了……也许达尔扎克没有死!反正不管达尔扎克是死是活,他都要去找。至于达尔扎克,他手头有一把手枪——在方塔找到的那一把全新的手枪。他曾在曼屯的一家枪械店注意到这款手枪。他带了手枪去问店主,店主告诉他,前天早上有个男人来买这把枪。他戴着软帽,穿灰色大衣,留着络腮胡,他这线索很快就断了。可是他没有气馁,马上去查另一条线索——或许该说是华特在卡斯第庸找到的线索。他在那儿继续华特没做完的事。华特找到袋子后,就什么也不管地跑回海格立斯堡,胡尔达必却继续追踪这条线索,也就是追寻英国拖车的双轮痕迹。他发现这轮痕到了卡斯第庸的地缝后,并没有继续走到曼屯,反而走另一道山坡去到索斯贝。索斯贝!毕纽尔就是在索斯贝下驿车的不是吗?毕纽尔……胡尔达必想起我的探险。毕纽尔来这附近做什么?他的出现一定和这悲剧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真的达尔扎克出现又再失踪,这证明他先前一定是被关起来了。可是关在哪儿?和拉桑有关联的毕纽尔绝不会无缘无故地从巴黎南下!他在这紧要关头下来,也许是为了监视被监禁的达尔扎克!想到这点,他继续推理。胡尔达必向卡斯第庸隧道口的客栈主人打听消息。他说前晚有个可疑的男人经过,他口中男人的模样和枪械店老板描述的人非常相似。这男人进来客栈喝东西,举止十分怪异,活像刚从疯人院逃出来似的。胡尔达必听到这里时,知道已是八九不离十。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道:“你们这里有疯人院吗?”客栈主人说:“有呀!巴波内山就有一间疯人院。”这时胡尔达必完全了解了“波内”这两个音节的意思了。从这时起,胡尔达必确定达尔扎克曾被当做疯子,关在巴波内的疯人院里。他跳上马车前往山脚下的索斯贝。如此一来他岂不是冒着在那儿碰到毕纽尔的危险吗?可是他一点也没想到这个,立刻前往巴波内的疯人院。他决定要知道一切,不计任何代价,为了这个索尔本大学教授,身为《时代报》记者的他,当然懂得如何让院长告诉他所有的事!也许,也许,他就要知道达尔扎克到底怎样了。既然我们发现袋子是空的,既然小拖车到了索斯贝就失去踪迹,既然拉桑没认为杀死达尔扎克是必要的(否则他大可将装在袋子里的达尔扎克丢入卡斯第庸的深渊中即可,他也许觉得将活着的达尔扎克关回疯人院对他是有利的)……胡尔达必想的很合理,活的达尔扎克比死的更有利用价值!玛蒂若发现他是假的达尔扎克时,真的达尔扎克便是最好的人质!这恶贼手上有这人质,就能随心所欲控制这可怜的女人。达尔扎克若死了,玛蒂也许会亲手杀了他,或把他交给司法单位。
胡尔达必想的一点也没错。在疯人院的门口,他碰到毕纽尔。他毫不迟疑,扑过去勒住他的脖子,用手枪威胁他。毕纽尔是个胆小鬼,他哀求胡尔达必饶了他,说达尔扎克还活着。一刻钟后,胡尔达必便知道了一切。让毕纽尔吐露一切的倒不只是手枪——因为怕死的毕纽尔除了爱惜生命外,更爱惜使生命变得可爱的东西,尤其是钱。胡尔达必不费什么力气就使他相信,如果他不背叛拉桑,他就完了;可是如果他帮助达尔扎克一家人不闹出丑闻就结束这场悲剧的话,他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他俩谈妥条件,一起进人疯人院。接见他们的院长听完他们的话后,刚开始很惊讶,然后是害怕,最后变得极为友善,立刻释放了达尔扎克。我曾说过,达尔扎克因奇迹般的好运,受了原可致命的伤却无大碍。高兴得不得了的胡尔达必马上把他带回曼屯。他们情感流露的谈话,我略过不提。为了摆脱毕纽尔,胡尔达必约他在巴黎见面付他钱。在路上,达尔扎克告诉胡尔达必,几天前,他在囚房看见一张当地报纸,报上说,刚在巴黎结婚的达尔扎克夫妇在海格立斯城堡做客!他无须知道其他细节,就猜得出造成他不幸命运的原因,他知道是谁那么大胆冒充他,欺骗心智仍然混乱、什么决定都可能做出来的玛蒂。这个发现给予他前所未有的力量。他偷了院长的大衣来遮掩他的病人制服,又偷走他钱袋中的一百多法郎,然后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攀爬过一道在其他情况下他绝对不可能跳过去的高墙。随后他下到曼屯,跑进海格立斯城堡。他亲眼见到了达尔扎克,他看到了他自己!他准备了好几个小时,使自己看起来更像自己,甚至连另一个达尔扎克都可能分不清楚!他的计划很简单,他将表现得像回到自己住所般,进入海格立斯城堡,然后走到玛蒂房间,在玛蒂面前和另一人对质!他向沿岸居民打听这对夫妻的住所,得知“两夫妇住在方塔里”。这句话比他所承受的一切折磨更令他痛苦。直到他在多出人体可能性的实体示范结束后,再次看到黑衣女子时,他的痛苦才平息。那时他了解了,假使她在另一个人的奸计迷惑下,身体或精神上有一秒钟做过那人的妻子的话,那她绝不敢如此看他,不会发出如此喜悦的呼唤,像打了胜仗般地和他相认!他俩曾被拆散,可是从未失去过彼此。
他在执行计划前,去曼屯买了把手枪,也扔掉大衣,因为那会使找他的人容易发现他。他买了和另一个达尔扎克一模一样的外套,等到五点后才开始行动。他先躲在卡拉凡大道上方的流溪别庄后面,从一座山丘高处观察城堡的一切动静。五点时,他知道假达尔扎克待在鲁莽查理塔,他将不会在方塔碰到冒牌的达尔扎党,便决定冒险进到方塔。他经过我们身旁时,马上就认出我们了。那时他很想大声对我们说他是谁,可是他立刻忍住冲动,因为他只求黑衣女子认出他!是这个希望使他继续前进,只有这个希望使他愿意活下去。过了一小时后,拉桑进入同一个房间,拉桑背对着他写信,生命就在他的掌握中,然而,经历了那么多苦难的他,仍然没有报复的念头,他的心中没有空闲容纳对拉桑的恨;他心里只有对黑衣女子的爱!亲爱的、可怜的、令人同情的达尔扎克!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我不明白的是,达尔扎克如何能再次进入城堡,如何回到衣橱。胡尔达必告诉我,当他带达尔扎克回曼屯的当晚,他用一艘船将达尔扎克送回城堡。老巴布的逃亡使他知道可以从水井通道进入城堡,他也如法炮制!胡尔达必计划选择出最合适的时间和拉桑对质,然后将他抓住。当天晚上已太晚了,他不能采取行动,但他已决定要在第二天晚上和拉桑了结。那时最重要的是要将达尔扎克藏在岛上一天;贝合尼耶老爹帮助他在新堡找了一处荒废的安静角落。
我听到这儿忍不住大叫一声,胡尔达必听了忍不住大笑。我叫道:
“原来如此!”
“是的……就是如此。”
“所以那晚我才看到了‘澳大利亚’!那晚我碰到的原来是真的达尔扎克!我一直想不清楚,因为他不只有‘澳大利亚’!他还有胡子,拉不下来的胡子!现在我都懂了!”
胡尔达必平静地说:
“你可花了不少时间才懂,那天晚上,朋友,你差点破坏了我的计划。你到鲁莽查理塔时,刚好达尔扎克正带我回到井边。我那时只来得及躲进井中,拉上木板;达尔扎克则立刻跑进新堡……后来你去检查胎记及胡子后,达尔扎克跑来找我,我们都很烦恼。如果第二天早上,你不小心和假达尔扎克提到你曾在新堡见到他这件事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灾难。达尔扎克本打算告诉你一切事实,可是我拒绝了。因为我害怕你知道后,第二天早上就无法装做没事的样子。桑克莱,你的个性有点冲动,平常你只要一见坏人便会怒火高涨,在这种时候,更会使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此外,另一个达尔扎克太狡猾了……于是我决定冒险什么都不跟你说。我必须让大家看到我在第二天早晨才回到城堡,所以得想个办法让你在我回来前不会看到拉桑,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一大早就叫你去钓锦蛤了吧!”
“啊,我懂了!”
“桑克莱,最后你总是会懂的。我希望你不会讨厌去钓锦蛤;那让你和艾蒂度过美妙的一小时,不是吗?”
“讲到艾蒂,为什么你要作弄我,让我愚蠢地发火?”
“这样我才有理由假装对你生气,禁止你跟我及达尔扎克说话啊!我说过,我不希望你向达尔扎克提到前一晚的事!桑克莱,你应该明白才是呀!”
“我明白的,朋友。”我说。
“我衷心谢谢你,桑克莱!”
“可是还有一件事我不懂!贝合尼耶老爹为什么会死?谁杀了他?”
胡尔达必低声地说:
“是那根手杖!那根受诅咒的拐杖……”
“我以为是人类最古老的刮刀。”
“凶器有两个:手杖及刮刀。那把手杖宣判了他的死刑,刮刀只是刽子手而已!”
我看着胡尔达必,自问这次我到底有没有搞清楚聪明的他在说什么。
“桑克莱,有几件事你还是没弄懂。其中之一是,在我知道真相的第二天,为什么我在达尔扎克夫妇面前,将瑞思的尖嘴手杖丢在地上?那时我希望达尔扎克会捡起来。你记不记得,桑克莱,拉桑的尖嘴手杖,拉桑在葛龙迪椰城堡时拿手杖的样子!他拿手杖的方式独一无二!我当时就希望看这个达尔扎克用拉桑的方法拿手杖!我的推理很正确,可是我更想看到达尔扎克露出拉桑的动作。我脑子里一直在打这个主意,甚至第二天我去了疯人院后,还这样想,甚至在我已经拥抱过真正的达尔扎克后,我仍希望看到假达尔扎克做出拉桑的动作!啊!我多希望看到这恶贼有一秒钟忘了他的伪装、他的身材,以他本人惯有的方式挥动手杖,伸直了故做驼背的身体去打摩特拉家族的纹章……亲爱的达尔扎克,努力挥你的手杖吧,啊!他果然打了!我看到他身体整个拉长,整个身体!而另外一个看到的人却因此死了,那就是可怜的贝合尼耶老爹。他在看到那一幕时,整个人都吓呆了,一个不稳,很不幸地跌在刮刀上,就这样死了!他死了,因为他捡到可能是从老巴布礼服中掉出来的人类最古老的刮刀,正要把它带到老教授在圆塔的工作室去。他是因为再度看到拉桑的手杖而死的,他是看到拉桑真正的身材而死的!桑克莱,在所有战役中,都有一些无辜的牺牲者……”
我们沉默了一下。我忍不住对他说,我很难过他对我这么没信心。我不原谅他让我及所有的人都认为老巴布是凶手。
他笑着说:
“我从未担心过他!当然我也确定在袋子里的不是他。在发现他的前一晚,我将真的达尔扎克交给贝合尼耶老爹藏在新堡中后,便从水井通道离开,将我的小船留在那儿,以便执行第二天的计划时用。那小船是‘海上屠夫’的朋友保罗借我的,他也是个渔夫。我游泳回到岸边,衣服叠在头顶上。我上岸时,刚好碰到保罗。他很惊讶看到我在那么晚时夜泳。接着他邀我一起去钓章鱼。这刚好使我能整夜监视海格立斯城堡,我于是便同意了。也就是那时,我才知道我那艘小船原是杜里欧的。‘海上屠夫’突然发了财,告诉所有人他要回故乡去,他说他以很高的价钱卖了一些珍贵的贝壳给老巴布。确实,事发前,几乎每天都可看到他和老巴布在一起。保罗知道杜里欧在回威尼斯前,会先在山雷摩停留。我渐渐明白老巴布的冒险经过。他需要一艘船离开城堡,就是‘海上屠夫’的船。我向保罗问了杜里欧在山雷摩的地址,然后写一封匿名信,寄给瑞思。瑞思因为相信杜里欧可以告诉我们老巴布的下落而前往山雷摩。事实上,老巴布付了钱给杜里欧,要渔夫载他到岩洞,然后别再出现了。我是因为同情这个老教授,所以才通知瑞思的,因为他的确很有可能发生意外。至于我,我只希望这个老先生能在我和拉桑结束一切后才回来,因为我希望让拉桑以为我怀疑的是老巴布。所以当我知道找到他时,我并不是很高兴。我得承认,得知他胸口受伤的消息,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多出人体的胸口也有道伤,如此一来,我便能多演几个钟头的戏。”
“为什么你没有立刻停止?”
“你不了解吗?我不可能让拉桑这具多出的人体在白天消失不见。我必须有一整天的时间准备,让他在夜晚消失!可是,贝合尼耶老爹死的那天,真是一波三折,警察来后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得等他们走后才能采取行动!你们在方塔听到的第一声枪响是一个信号,它通知我,最后一名警察刚离开加里巴底海角的艾宝客栈;第二声枪响则是表示海关人员刚回他们的营房用晚餐,所以海口已无危险……”
我看着胡尔达必明亮的眼睛说:
“胡尔达必,当你为了你的计划,把杜里欧的小船停在水井通道口时,你已经知道第二天它会载什么东西出去了吗?”
胡尔达必低下头,沉重缓慢地说:
“不,桑克莱,别这么想,我没想到它会用来载运尸体。不管如何,他总是我父亲!我本想用小船载这多出的人体去疯人院的!桑克莱,我本来只是想终身监禁他……可是他自杀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希望上帝饶恕他!”
接下来,我们整晚未再交谈。
到了拉荷胥时,我想帮他点些热食。可是他坚持不要用餐。他买了所有的早报后,低头忙着读当时要闻。报纸上登的都是有关俄罗斯的新闻。圣彼得堡刚查获反沙皇的大型间谍组织。报上所刊登的消息是那么惊人,实在很难教人相信。
我打开《时代报》,头版的粗大标题是:
乔瑟夫·胡尔达必启程前往俄罗斯
下面一行则是:
沙皇亲召
我将报纸递给胡尔达必,他耸耸肩,说道:
“啊!连我的意见都不问!主编要我去那儿做什么?我对沙皇跟那些革命分子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是沙皇的事,与我何干!他自己处理就好了。俄罗斯!我要请假,对,我真的需要休息!桑克莱,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某个地方休息?”
我连忙大声说:
“不,不,谢谢你,我已经受够了和你一起休息,我现在只想工作!”
“随便你,朋友,我不强迫人的。”
因为我们即将抵达巴黎,他便去梳洗整理一番。在清口袋时,他很惊异地在口袋里发现一封不知何时放进去的红色信封。
“啊,奇怪咧!”胡尔达必说,然后把信封拆开。
他看完后,笑得好大声,我再度看到我熟悉的胡尔达必。我想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得那么快活。他说:
“因为我要出发了!朋友,我要出发了!啊!既然是如此,我就去!今晚我就上火车!”
“去哪儿?”
“去圣彼得堡!”
他将信交给我,信上写着:
先生,在发生连沙皇皇宫都震撼的大事后,我们知道您的报社决定要派您去俄罗斯。我们必须警告您,您不会活着抵达圣彼得堡的。
署名为“中央革命委员会”。
我望着乐不可支的胡尔达必,简单地说了一句话:
“嘉利王子那时也在车站。”
他懂了我的意思,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说:
“那么,朋友,我将会玩得很高兴!”
不管我怎么抗议阻止,他只应我这句话。我们晚上抵达北站后,我拥抱他,绝望地流泪,求他不要离开我们这些朋友,但他仍是笑着重复说道:
“啊!太好了,我会玩得很高兴的!”
这是他最后的告别。
第二天我回到法院重新工作。我首先碰到的同事是合勃及海斯两位律师。他们问我:
“你的假期还愉快吗?”
“再愉快不过了!”
可是我的气色实在太糟,他们俩于是拖了我去喝酒。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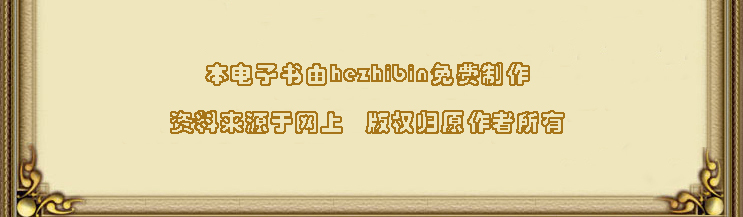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