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20章 “多出人体”可能性的实体示范
|

|
|
|
胡尔达必及黑衣女子走进方塔。他的态度一本正经,庄严得不得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处在一个忧虑惊慌的悲惨时期,我很有可能会觉得好笑。即使是准备审问被告的检察官,或法官穿着镶白助皮的红袍走进法庭,都没有他威严迫人。
至于黑衣女子,她焦躁地紧紧勾住她年轻同伴的手臂,努力掩藏她的恐俱。可是她惊慌的眼神,还是透露了她的情绪。达尔扎克面色阴沉果决,准备随时伸张正义的样子。除了这些以外,更令我们不安的是杰克老爹、马东尼及华特,他们都出现在鲁莽查理庭院里,三个人全背着猎枪,沉默不语地站在方塔门口,像士兵般接受了胡尔达必的命令,准备禁止任何人离开古堡。艾蒂被他们的举动吓到了,她问特别忠诚的华特及马东尼,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威胁的对象又是谁。但是令我惊讶的是,这三个人并不回答。于是,艾蒂毅然决然走到老巴布起居室的门前,双手张开,准备阻挡任何人进入这房间。她低沉地说:
“你们要做什么?难不成要杀了他?”
“不,太太。”胡尔达必严肃地对她说。“我们要审问他。但是为了确定法官们不会变成刽子手,我们将对着贝合尼耶老爹的尸体发誓,所有人都放下武器,不能留在身上。”
然后他领我们进人灵堂,贝合尼耶老妈仍在哭泣哀悼被最古老刮刀杀死的老伴。我们依照胡尔达必的话,解下身上的手枪,一一发誓。惟一不肯照做的是艾蒂。胡尔达必知道她把手枪藏在裙下,他让她了解,卸下武器是为了让她更安心。
她终于同意照做。
胡尔达必再次扶着黑衣女子走到走廊上,我们都跟着他。可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他并没有进人老巴布的房间,反而直直走向那多出一具人体的房间,他拿出我描述过的小钥匙,打开那扇门。
我们进人达尔扎克先前的房间时,看到达尔扎克的工作桌上,摆着他的绘图及颜料。这令我们有点惊讶,那是他在鲁莽查理塔的工作室里用过的东西。还有插着小画笔、装满红色颜料的瓶子。在工作桌中央摆着被染成血红色的人类最老的头颅,很搭配房间里的气氛。
胡尔达必关上门,拉上门闩。他情绪有点激动,我们都诧异地看着他。他说:
“请坐下,女士先生们。”
桌子旁边有些椅子,我们坐了下来。气氛愈来愈紧张,甚至可以说,我们全都极度怀疑与不安。在这些平凡无奇的绘画用具后面,可能藏着悲惨意外的可怕原因。还看,那颗头颅笑得真像老巴布。胡尔达必说:
“你们一定发觉到,这桌子旁有一张空椅,也就是说少了一个人。那是留给瑞思的,他就快来了。”
“也许他找到了老巴布无辜的证据。”艾蒂对胡尔达必这一连串的预备措施,比任何人都不安。“我请达尔扎克夫人一起和我请求所有在座的先生,在我丈夫回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黑衣女子没有回应,因为艾蒂还没说完,我们就听到走廊门后有很大的嗓音及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瑞思。他要我们立刻开门,并喊着:
“我带回来了红宝石别针!”
胡尔达必打开门,说道:
“瑞思,你终于回来了!”
艾蒂的先生看起来很绝望的样子。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又发生什么不幸了?我看到铁门紧闭时,真害怕是不是回来得太晚;我还听说城堡里有人在替死人祈祷。我以为你们处决了老巴布!”
这时,站在瑞思后面的胡尔达必关门上门,他很有礼貌地说:
“老巴布还活着,贝合尼耶老爹死了!先生,现在请您坐下。”
现在轮到瑞思惊讶地看着绘图板、颜料瓶及沾血的头颅。他问道:
“谁杀了他?”
这时他才看到她太太也在房里。他握住她的手,可眼睛却看着黑衣女子。
“贝合尼耶老爹在死前指控拉桑!”达尔扎克回答。
“您的意思是说,他指控的人是老巴布吗?”瑞思很快地打断他。“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事。我也曾怀疑过我们亲爱的叔叔,可是现在,我再强调一次,我带回了红宝石别针!”
他为什么一再提到红宝石别针?我想起艾蒂说过,在发生多出人体意外的那晚,她曾好玩地用别针刺过他,而老巴布抢走了她手中的别针。可是这个别针和老巴布的意外有什么关联?瑞思没等我们说完,就主动告诉我们,这别针是和老巴布一起失综的,他刚在“海上屠夫”那里找到。它别住了一叠那晚老巴布付给“海上屠夫”的钞票。原来老巴布买通“海上屠夫”做同谋,嘱咐他不可泄漏风声。杜里欧的确用船载他到了殉情洞口,他还因为一直没看到老巴布出来,担心得很,到了清晨才离去。
瑞思得意扬扬地下结论:
“那个将红宝石别针送给小船船主的人,是不可能同时在方塔被人装进马铃薯袋的!”
艾蒂听完后说:
“你怎么会想到去山雷摩?你知道杜里欧会在那里吗?”
“我收到一封匿名信,里面附着他的地址……”
“是我寄给您这封信的。”胡尔达必平静地说。“先生们,我很高兴瑞思先生如此迅速就回来了。现在所有人都到齐了,所有海格立斯城堡的人都在这儿,所有和‘多出人体的可能性实体示范证明’有关联的人,请你们集中注意力。”他以冰冷的语气补充道。
可是瑞思打断他:
“您说海格立斯城堡所有和‘多出人体的可能性实体示范证明’有关联的人,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能从中找出拉桑。”胡尔达必说。
还没开过口的黑衣女子站起来,抖得像片叶子,她屏住气小声地说:
“什么!拉桑就在我们之中?”
“我百分之百确定!”胡尔达必说。
房间里是一阵可怕的沉默,没有人敢看别人。
记者继续用冰冷的口气说;
“我确定,而且,夫人,您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因为您始终有这个念头!先生们,你们也一样,不是吗?我们在鲁莽查理塔平台戴着墨镜用午餐那次,你们也这样猜想,不是吗?在那一分钟,除了艾蒂,有谁没有感觉到拉桑的存在?”
“这问题也可去问桑杰森教授,”瑞思立刻反驳,“因为我们若要加以推理的话,我不明白,那天桑杰森教授也和我们一起用午餐,为什么他现在没加入我们……”
“瑞思先生!”黑衣女子叫着。
“对不起,请原谅我。”瑞思有点不好意思,“可是胡尔达必不应该说所有海格立斯城堡的人……”
“桑杰森教授的心神离我们极远。”胡尔达必以稚嫩的庄严态度宣布,“我根本不需要他的身体。尽管他住在海格立斯城堡,在我们左右,可是他从来没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户。至于拉桑,他却从来没离开过我们!”
这次,我们相互窥视,而拉桑本人就在附近这想法,在我看来是那么疯狂,使得我忘了不能和胡尔达必说话的约束,我大胆地说:
“可是,那次戴墨镜用午餐的人此刻还少一个……”
胡尔达必瞪我一眼,埋怨地说:
“又是嘉利王子!桑克莱,我已告诉过你王子在边境的活动究竟是什么。我向你保证,那和桑杰森教授女儿的不幸丝毫无关,别去打扰他的人道工作。”
“这一切,这一切都不合逻辑。”我恶意的说。
“桑克莱,就是你的废话使我无法思考推理。”
我那时因为已经愚蠢地开了头,居然忘了我向艾蒂发过誓要保护老巴布,而一心要找胡尔达必的漏洞,遂开始攻击老巴布。后来艾蒂为此还记恨了许久。我很大声并信心十足地说:
“老巴布也参加了那次戴墨镜的午餐,而你因为找到那个红宝石别针就排除他的嫌疑。可是这别针只能证明老巴布找过杜里欧,证明杜里欧和他的小船在水井出口的海边等过他而已,并不能解释老巴布如何由水井出去,因为我们发现水井的盖板从外面卡住了!”
“你……那是你自己的发现。”胡尔达必极端严厉地看着我,使我很不自在,“可是我却发现井盖是打开的!我在把你遣开,叫你去问马东尼及杰克老爹有没有任何动静时,我跑到水井边,看到它是打开的。等你回来时,我已经回到鲁莽查理塔原来的位置。”
“你把盖板放回去了!”我叫出来,“可是你为什么关上水井呢?你要骗谁?”
“骗你,先生!”
他说这两句话时,态度非常不屑,使得我脸都红了。我站了起来。现在,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同时,我想起胡尔达必刚才在达尔扎克面前对我的粗鲁态度!我有一个恐怖的预感,觉得每只看着我的眼睛都在怀疑我,都在指控我!哦,没错,我可感受到所有人都猜测着我可能就是拉桑!
我,拉桑!
我一个一个看着他们,我以眼神斥责胡尔达必,整个人狂烈的怒火都愤怒地向他抗议。可是胡尔达必并没低头,我血管里的怒火烧得更旺!我叫着:
“啊!你必须说个明白。如果老巴布没嫌疑,如果嘉利王子没嫌疑,如果桑杰森教授没嫌疑,就只剩下房间里的人了。如果拉桑是我们之中的一个!胡尔达必,你就指出来吧!”
这个瞪着我的年轻人,使我完全忘记了我受过的良好教育,我愤怒地又说:
“指出来!把他指出来!你和在重罪法庭时一样,那么慢条斯理……”
“我在重罪法庭时的缓慢,错了吗?我难道没有理由吗?”他冷静地回答。
“那么你要让他逃走吗?”
“不,这次我向你发誓,他绝逃不掉!”
为什么他跟我说话时,语气还是那么凶恶?难道……难道他真的相信我是拉桑伪装的吗?接着我的视线和黑衣女子的眼睛相遇。她看我的样子竟充满了恐惧!
“胡尔达必,你不会是要说……你不会这样猜测吧!”我说话时,好像有人扼住我的脖子。
这时,外面有枪声响起,就在方塔附近,我们全都跳了起来。我们都记得胡尔达必对那三人下的命令:若是有人尝试离开方塔,他们就开枪射他。艾蒂叫了出来,急着冲出去。可是胡尔达必只说了一句话,她就平静下来了。他说:
“如果有人对他开枪的话,那三人早就开枪了!这枪声只是一个讯号,代表我可以开始了!”
然后他转向我:
“桑克莱,你应该知道,如果没有正确的推理,我不会随便猜测任何事、任何人!这是我一贯的行事方针,而且从来没有失败过。现在也请你和我一样,采用这方法……拉桑就在我们之中,正确的推理将会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请你们都坐下来,眼睛不要离开我,因为我现在要在这张纸上做多出人体可能性实体示范!”
他在开始之前,又看看他后面的门闩是否是拉上的,然后回到桌旁,拿起圆规。他说:
“我决定在多出人体出现的地点做此示范,如此一来,结果将更不容置疑。”
他用圆规在达尔扎克所绘出的图上,取出代表鲁莽查理塔的圆形。这样他很容易就能在另一张白纸上画出同祥大小的圆形。他用图钉把这张白纸固定在绘图板上。
胡尔达必画完这圆形后,放下圆规,拿起红色颜料瓶,问达尔扎克那是不是他用的颜料。很明显,达尔扎克跟我们一样,不知道这年轻人意图何在。他回答道,那颜料的确是他为那张平面图特别调配的。
瓶里的颜料干了大半。可是根据达尔扎克的说法,剩下的颜料应可画出和他的平面图浓度相近的色彩。胡尔达必神色郑重地说:
“没有人碰过它,这颜料只被一滴眼泪冲淡过。还有,你们会看到,多一滴或少一滴眼泪都不会影响到我的示范。”
说着说着,他把画笔上了颜料,开始涂满他先前画好的圆形。他非常小心地画着。我们在鲁莽查理塔时,我很惊讶地看到,在有人被谋杀的时候,他居然只想着画图!
他画完后,看了一下怀表的时间,说:
“先生女士们,请看,我把这圆形的颜色和达尔扎克先生的颜色涂得一样厚,两个颜色几乎一模一样!”
“也许。可是这又代表什么?”达尔扎克问他。
“等一下,您承认是您画这张图的吧?”记者问他。
“当然!我和你们一起离开方塔,走进老巴布的工作室,看到老巴布将他那头颅扔在地面上,而将这张图弄得一团糟时,可不是很高兴的!”
“现在就要谈到这事了!”胡尔达必一字一字地说。
接着,他拿起摆在桌上的人类最古老的头颅,将它反过来,让达尔扎克看它血红的下巴,继续问道:
“您说,是它沾到您图上的颜料的,对吧?”
“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进入鲁莽查理塔时,这颗头颅还反过来在桌上放着。”
“我们的意见到目前为止都一样!”记者强调着。
接着,他站起来,将头颅放在怀中,走进厚墙的凹口。阳光从以前是大炮口而现在被达尔扎克当做梳洗处的窗户栏杆照进来。胡尔达必在那儿点亮一根火柴,点燃桌上的酒精灯,将一个盛满水的小锅放在灯上!这当中他都没放下那颗头颅。
我一直看着他做这些奇怪的事。胡尔达必的态度真是令我们费解。他从没表现得如此坚决,如此令人不安。他愈跟我们解释,我们愈不懂。而且我们很害怕,因为我们觉得在我们之中,有一人很害怕,比我们还害怕!那是谁?也许是神情最平静的那人!
最平静的人,是拿着头颅及锅子的胡尔达必。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突然同时往后退?为什么达尔扎克害怕地睁大了眼睛?为什么黑衣女子、瑞思及我自己都叫出声,我们异口同声喊出一个名字:拉桑?
我们在哪儿看到他?我们看到的是胡尔达必,怎么会想到他呢?啊!沐浴在傍晚血红余晖中的那个侧影,那个案发当日在晨曦一般血红的暮色中,站在窗凹里的胡尔达必的额头!哦!他坚决有力的下巴,方才变得较浑圆温柔,带着苦涩,在白日的光线下显得相当迷人,此刻在黄昏的暮色里却邪恶而骇人!胡尔达必和拉桑多么相像!这时,他真的很像他父亲!他简直就是拉桑!
他妈妈难过地叹了口气。胡尔达必走出了这阴森森的布景,走向我们。他又是我们认识的胡尔达必了。可是我们仍在打冷战。从没见过拉桑的艾蒂不明白这一切,她问我:
“发生什么事了?”
胡尔达必就在那儿,站在我们面前,手里拿着一锅热水、手巾,还有头颅。接着,他开始清洗那头颅。
他很快就洗好了。他要我们检察头颅上的颜料是否完全消失了。然后他坐在桌前,沉默不语地看着他自己涂好的颜料。他看了差不多十分钟之久。在这段时间中,他以手势命令我们安静。这十分钟真是非常难熬……他到底在等什么?突然,他用右手抓起头颅,好像玩滚球一样,在上了颜色的图上滚了几次。之后,他拿起头颅给我们看,要我们观察头颅上有投有任何红色颜料。胡尔达必再次拿出怀表。他说:
“过了十五分钟后,图上的颜料就干了。十一号那天,五点钟的时候,我们看到达尔扎克先生从外面走回方塔,然后关门上门。他告诉我们,直到六点之后,我们去找他前,他都没离开过。至于老巴布,我们看到他在六点整进入圆塔时,手上拿着干净的头颅!”
“这只须十五分钟就会干了的颜料,为什么那天在达尔扎克离开一个多小时后仍然没干?使得在六点整进入圆塔的老巴布气愤时摔在图上的头颅因此沾着红色的痕迹?这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我敢说没有人能找到第二个可能性:在五点进入方塔后就没离开过的达尔扎克,不是那个六点钟老巴布到之前在工作室里画图的达尔扎克;这个在五点回到方塔的达尔扎克,也不是我们在方塔房间找到,没见到他进去,却和我们一起离开的达尔扎克……简单地说,他不是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达尔扎克!正确的推理指出,有两个达尔扎克!”
胡尔达必说完看着达尔扎克。
达尔扎克和我们一样,还没反应过来他这示范的意思。我们都觉得这结论太可怕了,可是又对他佩服不已。胡尔达必将一切说得多么清楚!清楚而吓人!胡尔达必再次显现他逻辑推理的出众天分。
达尔扎克叫出来:
“原来他是伪装成我的模样,进入了方塔,躲进衣橱里。也因此,我在画完图离开鲁莽查理塔回到这里写信时,都没有看到他。可是贝合尼耶老爹怎么会替他开门?”
“那当然是因为他以为看到的是您!”胡尔达必答道,他握住黑衣女子的手,仿佛要使她增加一些勇气。
“所以我回来时,门一推就开了,因为贝合尼耶老爹以为我在里面。”
“没错,这是很正确且有力的分析。”胡尔达必同意他的话。“贝合尼耶老爹替第一个达尔扎克打开门后,没有去理第二个,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没看到他。您回方塔的时候,我们和贝合尼耶老爹还待在土台上观察老巴布的奇怪举动,他正在巴玛大洞洞口,对艾蒂及嘉利王子演说……”
“可是,贝合尼耶老妈已经回房了,不可能没看到我。当她看到一直没离开房间的我再度回房时,难道一点都不惊讶吗?”达尔扎克又说。
记者露出忧郁的微笑。他说:
“想一想,达尔扎克先生,假设当你回去时,也就是说,第二个达尔扎克经过时,她正在捡我倒在地上的马铃薯。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那么,我真庆幸还活在这世上!”
“你的确该庆幸,达尔扎克先生,的确该感到庆幸!”
“多可怕!想想看,当时我一回房,就关门上闩,而这个恶贼在我写信时,竟就躲在我后面,他原可毫不费力杀了我!”
胡尔达必走向达尔扎克,眼睛直视他眼睛,问他:
“为什么他没这样做?”
“您明知道他在等一个人!”
然后达尔扎克将悲伤的面孔转向在旁的黑衣女子。
胡尔达必现在和达尔扎克面对面,将双手放在他肩上,他的声音清亮有力:
“达尔扎克先生,我必须向您坦白一件事。当我明白了多出人体是如何潜进您的房间,而我又发现当您知道所有人——除了我之外——都相信您是在五点进去了方塔,却不说实话时,我当然很有理由相信在五点钟进房的那个达尔扎克不是拉桑。我大有理由相信那个达尔扎克才是真的;而您,您是假的。啊!亲爱的达尔扎克先生,我居然大大地怀疑过您!”
“这真是疯了!”达尔扎克叫着,“我之所以没说我进方塔的确切时间,是因为我根本不太记得确切时间,而且我不觉得那很重要!”
胡尔达必不理会他,也不管黑衣女子的激动和我们的惊异,继续说下去:
“所以,要回来取回被您抢走位置的正牌达尔扎克——这只是我的想像,达尔扎克先生,这是我的想像,您放心——在您的阴谋策划下,加上忠诚的黑衣女子的协助,终于无法揭穿您大胆的诡计。因此,达尔扎克先生,我因此还想像您就是拉桑,而被装在马铃薯袋子里的才是达尔扎克。啊!我真的太会想像了,我的疑心,多么不可思议!”
玛蒂的丈夫低声说:
“哎!我们这些在场的人也都彼此猜疑过对方!”
胡尔达必转身背对着达尔扎克,双手放进口袋,对着听完他说的话后,都快被吓昏了的玛蒂说:
“勇敢一点,夫人!”
然后,他以一个在讲台上解答几何习题的数学教授的口吻说道:
“达尔扎克先生,现在您知道当时有两个达尔扎克了,为了要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达尔扎克先生,我合理的推理告诉我,我必须勇敢公正地调查这两个人……我必须正直无私!所以,我当时便先由您开始……”
达尔扎克回答胡尔达必:
“够了,既然您已经不怀疑我了,请您立刻告诉我谁是拉桑!我坚决要求您现在说出来!”
我们围着他们两人一起大喊:
“我们也是……立刻!”
玛蒂冲向她的孩子,把他抱住,好像要保护他不受我们的威胁。可是这出戏已演得够久了,我们已经开始恼火。
瑞思喊道:
“既然知道就该说出来!让我们解脱吧!”
正当我想起上回在重罪法庭时,我也听过这样急切不耐的叫声时,突然,方塔门外又传来另一声枪响。我们很快地冷静下来,有礼貌地请求他尽快结束这无法再忍受的情况。事实上,我们的乞求仿佛是要说服别人——也许是要说服自己——我们并不是拉桑!
胡尔达必听到第二声枪响后,脸色很快就变了。他变得与先前完全不同,整个人好像充满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一改刚刚和达尔扎克说话时使我们每个人都极为不悦的讽刺语气,轻轻地推开一直想保护他的黑衣女子,背靠着门,双臂交叉,换了个语气说:
“各位要知道,面对这种大事时,什么都不可忽略。两个达尔扎克进来,两个达尔扎克出去,其中一个被装在袋子里,实在是很难弄清楚!即使是此刻,我都希望我不要弄错!……希望此刻在这里的达尔扎克先生容许我说一句话:我当时实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
那时,我心里觉得万分可惜。如果他早和我商量,我就会告诉他“澳大利亚”的事,那他也就省了这番工夫了。
达尔扎克站在记者前,愤怒地重复他的问题:
“什么理由!什么理由!”
记者异常地冷静。他说:
“您马上就会知道,朋友,我要告诉您的第一件事是,当我在调查您时,我告诉自己:‘不对,如果他是拉桑的话,教授的女儿一定会发觉!’那是一定的,不是吗?可是,在我观察达尔扎克夫人这段时间以来的态度之后,我很确定,先生,她始终都怀疑您是拉桑。”
本来已经坐下的玛蒂现在又努力站起来,以惶恐的手势表示她的抗议。
达尔扎克整个人好像被痛楚彻底击倒了。他坐下来,以正常的音量问道:
“玛蒂,你真是这样想吗?”
玛蒂低头没有回答。
胡尔达必以一种我无法原谅的残酷态度继续说:
“我回想起您从山雷摩回来后她的言行举动,处处都流露着她的焦虑和恐惧。请让我说完,达尔扎克先生,我必须解释,所有在场的人才能了解,我正在厘清状况!从那时起,桑杰森教授女儿的态度没有一刻是自然的,她顺从您的意愿尽快举行婚礼的原因,正是证明,她想永久摆脱心中的忧烦苦恼。我记得那时她的眼睛明明白白地在说:‘我怎么会到处都看到拉桑?甚至连在我身旁,即将是我丈夫的人身上,都有拉桑的影子!’先生,据我所知,她在火车站时的道别使人心都碎了!那时的她已在叫着:‘救命啊!’她希望从自己的想法、从自己的想像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您本身呢?可是她不敢告诉别人她的想法,因为她担心别人会说她……”
胡尔达必从容地靠近达尔扎克的耳朵,小声说了一句话——小声到玛蒂听不见,但却足以传到我的耳中。那句话是:“你是不是又疯了?”
接着他退后一步,说道:
“所以,亲爱的达尔扎克先生,您现在应该都了解了吧!为什么她后来对您的态度异常冷淡,可是有时她又很愧疚,因为她也不很确定,所以她时而又对您体贴万分。最后我必须说,您有时是那般地阴沉,我不免想,您是不是已猜到了,达尔扎克夫人在看您时,在和您说话时,常会沉思不语、心里常猜着您是拉桑吗……不过我可以告诉您,并不是‘如果他是拉桑,桑杰森小姐一定会发觉’这个念头使我清除了对您的疑虑,因为她无时无刻不是这么想!不!是另外一件事使我不再怀疑您!”
达尔扎克喊道:
“可是如果我是拉桑,我拥有了桑杰森小姐以后,我应该继续让别人相信拉桑死了,这对我才有利不是吗?这个推理再简单不过了,是不是?我不应该再出现啊!难道,我不是从拉桑开始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失去玛蒂的吗?”他的语气既讽刺又绝望。
胡尔达必的脸色变得苍白无比,他说:
“对不起,先生,对不起。请允许我冒昧说一句话,您再次忘了什么是正确的推理……因为正确的理由所指出的,和您所看到的完全相反!我观察到的是:当您的太太相信,或是快要相信您是拉桑时,您惟一的办法是,让她看见拉桑存在您出现以外的地方!”
听完这话后,黑衣女子慢慢退到墙边,挨近胡尔达必,呼吸急促,眼睛直盯着脸色变得严峻吓人的达尔扎克。至于我们其他人,都对胡尔达必这番不容置疑而且新鲜的推理所吸引,急着听他的下文,所以没有人打断他,我们全都等着知道这记者出人意料的推测结果。
年轻人稳如泰山,继续说下去:
“虽然,为了您的利益,您得让她看到拉桑存在您出现以外的地方,可是这事并不急,直到发生了一件事。请您想像一下,我是说想像,亲爱的达尔扎克先生。曾经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您在无意之间让玛蒂看到拉桑的真面目,所以您必须要立刻让他再复活一次,而这次,当然得是在您存在之外的地方,您得让您太太相信,复活的拉桑不是您!啊!冷静下来,我亲爱的达尔扎克先生,我请求您……我不是已经说过,我对您的疑虑已经完全消失了吗?如今,焦虑使我们忘了如何推理,我们不妨试着推理以为消遣。现在,假设您就是拉桑,下一步我该如何思考便很清楚。这些是数学的步骤,你是学者,应该比我更了解。在假定您就是拉桑之后,我自问道,在布格车站时,您为什么会以拉桑的模样出现在玛蒂小姐面前?拉桑的确在她眼前复活,这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却不可能是故意的!”
达尔扎克不再打断他的话。胡尔达必继续说:
“就像您所说的,达尔扎克先生,拉桑的出现使您的幸福消散了,所以这次的出现若不是有意的,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是一场意外!如此一来,整件事一下子变得很清楚了。哦,我研究了许久布格车站的意外。我继续分析,您不要害怕,在布格的餐室时,您以为您太太会在车站外等您,因为她是这样告诉您的。所以您在写完信后,想回到您的包厢梳洗一番,因为易容大师需要检视一下自己的伪装。您心想,再演几小时的戏,过了边境,到了她完全属于你的地方后,我就要卸下面具。因为不管怎样,您的面具戴得太久了,也很辛苦。没错!这面具使您非常辛苦。所以一进到包厢,您就把它拿下来,想休息几分钟。您才拿下伪装的胡子和眼镜,便听到车厢门打开的声音。您太太一看到没有胡子和眼镜的拉桑后,立刻吓坏了,尖叫着冲出去……啊!您知道情形很危险了!您太太如果没在其他地方看到她的先生达尔扎克的话,您就完了!所以,您马上戴上面具,从火车包厢的窗户跳到另一个月合,在她抵达前赶回餐室!她看到您时,您还来不及坐下,而是站在她面前。您成功了吗?很可惜,没有!您的不幸从此开始了,因为她再也无法摆脱您可能就是拉桑的恐怖想法。在月台的煤气灯下,她看着您,突然像疯子般放下您的手,逃进站长室。啊!您更加明白了,您必须驱散她可怕的想法。您一出了站长室后,马上就折回来,关上门,假装您也看到了拉桑!这是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此外也是为了骗过我们——万一她告诉了我们她的想法的话。于是您先发电报给我,通知我!当我想到这点后,您一切的行为都很清楚了!您不能拒绝她去找她父亲,因为她会抛下您,自己前去!但是,您还没有完全失败,您还有希望可以挽回。在旅行途中,您太太仍然迟疑不决。她交给您她的手枪。她的想像力使她产生妄想,她的脑中想着:‘如果他是达尔扎克,就让他保护我;如果是拉桑,那就让他杀了我!我不愿再去想了!’在红岩时,您再度感到她的疏远,所以拉桑就又出现了。你看,亲爱的达尔扎克,我所思考的是不是很完整?甚至于您以拉桑的面孔再次出现在曼屯,也就是您乔装成达尔扎克去坎城等我们的那次,我也知道您是怎么行动的。您在您朋友面前,搭上了在卡拉凡车站的火车。然而您只坐了一站就下车,也就是在曼屯车站。您在化妆室待了一会儿,然后以拉桑的模样,出现在去曼屯散步的朋友面前。接着您又搭了下班车,到坎城与我们会合。可是那天您听到也来坎城车站接我们的瑞思先生说,玛蒂并没看见拉桑时,您气恼白费了一番工夫,遂决定当天晚上让她从方塔的窗口,看到站在杜里欧小船上的拉桑,您看,亲爱的达尔扎克,假使我的猜疑属实,连那些外表再复杂难解不过的事,也就变得简单合理了!”
我自己明明亲眼看过并触摸过“澳大利亚”,可是听到这些话时,也忍不住发起抖来,怜悯地看着达尔扎克。在场所有的人也都为他颤抖着,好像面对着一个即将承担司法冤案的受害者一般。因为胡尔达必说的太有可能了,每人都在想,胡尔达必在如此周全地推理出达尔扎克就是拉桑的可能性后,究竟还能用什么论据证明他是无辜的。达尔扎克本来情绪很激动,现在稍微平静下来听这年轻人说话。我觉得他就像一些坐在被告席上的被告,在检察官滔滔不绝地指控他们的罪行时,眼睛睁得大大的,既震惊又害怕,可是全神贯注地听着,有时连他们都以为自己犯了其实没犯的罪。他后来说话时,没有那么生气,可是有点好奇的害怕。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天哪!我不知道我怎么躲过这危险的!”
他语气变得异常平静地说:
“既然您说您不再怀疑我了,先生,听完您说的这些话后,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使您消除怀疑的?”
“先生,为了赶走我的疑虑,我必须有证据!一个简单但绝对的证据。它要能直接清楚地告诉我,两个达尔扎克之中,哪一个是拉桑!先生,是您给了我证据的。就在您将多出人体的论证范围合上的时候,那天您承认——事实上也是如此——您说您回到房间后就关门上了门闩是骗了我们;您没告诉我们您是在六点回房的,而不是五点。可是就贝合尼耶老爹所说,而我们自己也观察到,您是在五点回去的!只有您和我知道,五点钟进门的达尔扎克不是您。可是您并没有说出来!别说您觉得五点没什么重要性,这很重要,因为这让您知道,另一个达尔扎克就是在这时进入方塔的——真的达尔扎克!所以,您在假装惊讶之后,便不再提这件事!您的沉默骗过了我们。如果您是真的达尔扎克,为什么要隐瞒拉桑伪装的达尔扎克已在您之前进了方塔?除非您是拉桑,您要骗过我们,不让我们知道另一个达尔扎克!两个达尔扎克中,说谎的那个一定是假的!所以我不再怀疑了,我确信,您就是拉桑!而当时躲在衣橱的是达尔扎克!”
“你说谎!”
我仍以为是正牌的达尔扎克,扑向了胡尔达必。
我们把他们拉开,一点都没丧失冷静的胡尔达必指着衣橱说:
“而且还在里面……”
接下来的一幕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令人永生难忘。顺着胡尔达必的手势,一双看不见的手将衣橱推开,和多出人体的那个可怕夜晚一模一样。
然后,多出的人体出现了!方塔里充满了惊讶、感动还有害怕的声音。黑衣女子发出了凄楚动人的叫喊:
“荷勃!荷勃!荷勃……”
这是喜悦的叫声。两个达尔扎克站在我们面前,两人是如此相似,以至于黑衣女子本可错认……可是她的心是不会被骗的,就算她的理智在听完胡尔达必无懈可击的推理后,还有任何犹豫。她伸出手迎向从可怕衣橱走出来的达尔扎克,玛蒂脸庞洋溢着再生的喜悦光辉。先前我常看到她忧郁的双眼逃避着她身旁男人的视线,现在她欢欣偷悦地定定看着这个人,平静而且确定。是他!是她以为已经失去的他!她曾试着在另一人脸上寻找他,可是徒然,所以她日夜指责自己的荒谬疯狂!
至于另一个男人,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无法相信他有罪的那个愤怒男人,他看到证明他罪行的活生生证据站在他面前,使他真正的身分再也无法掩饰后,再次试着那每次都救了他的举动。那么多人围着他,他居然还敢逃!我们这时才明白他到底有多大胆!他在我们面前演了好几分钟的戏,他早就知道他和胡尔达必的谈话结果会是如何,可是仍然以一种超乎凡人所有的力量控制住,不表现出来,同时狡猾地拖长谈论的时间,让胡尔达必尽情陈述他的推理过程,他知道胡尔达必一定会找出他的破绽,可是在这当中,他也许可以找出逃亡的方法。他算得那么准确,在我们走向另一个达尔扎克的当儿,他冲进了玛蒂先前住的房间,我们都来不及阻止他。他用力关上门,动作快如闪电!我们发现他消失时,已太晚了;他的诡计再次成功。之前,胡尔达必只注意通往走廊的门,并没注意到假的达尔扎克慢慢接近玛蒂的房间。但他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知道他无法从这房间逃出去的。可是,当拉桑这恶贼逃到门后,关上他最后避难所的门时,我们愈来愈焦虑,好像突然全都疯了一样,我们用力拍门,大声叫喊,害怕这个逃亡的天才又要成功!
“他要逃走了,他又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溜走了!”
瑞思是最生气的。这场景令艾蒂异常激动,她紧张地直掐我的手臂。没有人注意达尔扎克及黑衣女子,身处暴风圈中的他们,好像已忘了一切,连我们的叫喊声都置若罔闻。他们没说任何话,他们互看着对方,好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胡尔达必帮助他们找到的爱的世界。
胡尔达必打开通向走廊的门,向三位仆人求援,他们带了猎枪赶过来。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斧头!那扇门相当厚实,闩着的门门也异常粗重。杰克老爹拿了根木头柱子做撞锤用。我们每个人都加入了撞门的行动。门开始动摇了,我们的心绷得好紧,我们对自己说,门打开时,也许只会看到墙及栏杆……我们等着可怕的事发生,或者正好相反,期待什么事也不要发生,因为我们猜想,拉桑有可能消失无踪或者在空气中融化了。这些念头使得我们更加疯狂。
在门开动摇动时,胡尔达必命令仆人重新拿好猎枪,听从他的命令。不过他要他们在无法活擒他时才可开枪。然后他用肩膀再次撞门,门终于倒下了。他领先冲进房间。
我们走在他后面。在门口时,所有的人都凝住不动,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第一,拉桑竟在房里!哦!看得很清楚,整个房间里,我们只看到他。他很平静地坐在一把扶手椅中,就在房间中央。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祥和而且专注。他的手臂平放在扶手上,头靠着椅背,好像要对我们演讲,等我们提出意见的样子。我似乎看见他嘴上讽刺的笑容。
胡尔达必向前走了几步,他说:
“拉桑,拉桑,你投降了吗?”
可是拉桑不回答。
于是胡尔达必碰碰他的手及脸——拉桑已经死了。
胡尔达必指给我们看他的戒指。戒指的镶盖是开着的,里面原先已装有夺命的毒药。
瑞思倾听他心跳,然后宣布一切都结束了。
他说完后,胡尔达必请所有的人都离开方塔,忘记这个死人。他神色严肃,对我们说:
“我会处理一切。这是一具多出的人体,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消失。”
他由瑞思做翻译,指示华特去做一件事:
“华特,将装多出人体的袋子拿来!”
然后,他要我们离开,我们都服从他的命令,留他一人面对他父亲的尸体。
我们离开后,就扶着达尔扎克到老巴布的起居室休息。他不太舒服,可是这只是暂时性的疲惫。他一睁开眼,就对着他美丽的玛蒂微笑。她的脸色好像在说,她刚在近似奇迹的情形下,找到失去的亲爱丈夫,她怕再次失去。他要她别担心,说他一切都好,然后要她及艾蒂离开。这两位女士离开后,瑞思及我连忙检视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实在不明白,奄奄一息被装进袋子里的他,怎么能存活到现在,出现在这衣橱中?我们脱下他的衣服,拆开又重新包好他胸口的绷带后,知道这伤口并不如我们想像的严重。这伤口虽使他立即昏迷过去,但并不致命。达尔扎克是在与拉桑打斗时挨了这一弹的,子弹卡在胸骨上,造成外出血,所有器官都被震到,但生命机能毫未受损。
我们看过受这种伤的人,他们在别人都以为他们已死了的几小时后,竟能起死回生。我想起我一位好朋友的故事,因此而安下心来。我那记者朋友跟某音乐家决斗,在对方还来不及开枪前,他就射中对方胸口,一枪毙命。这使得他伤心不已。突然,那死者站起来,朝我朋友大腿射了一枪,害他那条腿差点得锯断,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在床上。那个音乐家后来陷人昏迷状态,可是第二天就能起床到大街上散步。他和达尔扎克一样,都是子弹打在胸骨上。
我们包好达尔扎克的伤口后,杰克老爹走来,掩上起居室的门。我自问为什么这老好人那么谨慎。这时我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及拖尸体的声音……我想起拉桑、装多出人体的袋子,还有胡尔达必。
我请瑞思继续照顾达尔扎克,跑到窗户旁——我没有弄错,庭院上果然是那列阴森的队伍。
这时天快黑了,事物都变得灰暗。但我认得出华特守在园丁塔门口,盯着洪水区,很明显地,他准备阻挡所有要进入鲁莽查理庭院的人。
我的目光转向水井,胡尔达必及杰克老爹的两个黑影弯向另一个黑影。我很清楚这团黑影是什么。在一个恐怖的夜晚,它装过一具人体,袋子好像很重。他们将它抬到井口上。我可以看到井口没盖子,那个平时盖在井上的木板已被拉开了。胡尔达必跳到井栏上,好像认得路的样子。杰克老爹将袋子推进井中,扑在井口,仍拉着那个我看不见的袋子。然后,他直起身子,将木板盖上,小心地将盖子及铁棍放回原来的位置。那声音让我想起,我在发现“澳大利亚”之前也听过这声音。那一夜,我跟着一个突然消失的黑影,鼻子撞上了新堡关闭的大门……
我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分钟,我要看,我要知道……我仍担心许多尚未清楚的事情!我只知道最重要的事实,可是我不知道所有的事实——或许该说是,缺少能解释真相的细节。
我离开方塔,回到新堡的房间。站在窗前,我远眺海面上的影子。夜色阴暗黝黑,什么都看不到,于是我努力倾听,但连海上的摇桨声都听不到。
在远处,很远的地方,反正是在我觉得很遥远的海面上,在地平线上——其实应说是正对地平线的地方,有一条落日余晖形成的红色地带。突然,一团黑影进入了这片红色条状区域。这团黑影又小又暗,可是因为我全副精神都集中在这黑影身上,所以感觉它很巨大壮观。这是一艘在海波上浮动的船影。然后它停下来,我看到胡尔达必的影子站了起来。我认得出是他,清楚得就像他站在十米外一般。他身后的红色背景将他的动作映得一清二楚,哦,他并没站多久……他弯下腰,很快抬起一个重物,这重物和他的影子混在二起。接着,重物被夜色吞没。这孤身一人的小影再次出现,他又弯下腰一会儿,然后坐进船中,小船开始前进。直到完全离开这片红色,接着这片红色也被夜色淹没了。
胡尔达必刚刚将拉桑的尸体投入海格立斯的海浪。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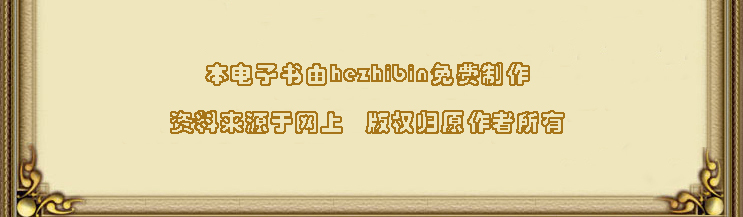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