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八回 白面郎拟开女校 神算子筹办银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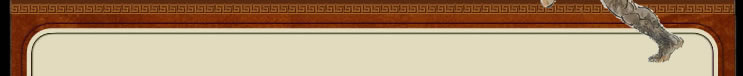 |
|
话说梁山泊众英雄下了山,闯入新世界,依从军师吴学究的将令,经营各种新事业,如今第一个先要提着那地煞星的地会星神算子蒋敬。看官,你道士谔为什么把天罡三十六个上上人才都丢下不讲,反把这素无名望的蒋敬提到舞台上来?原来“新水浒”本是个地覆天翻的世界,其位子自应天居下而地居上,所以开首第一个须写地煞星。然而还有一说,地煞星中之健出者,如神机军师朱武、镇三山黄信、神火将军魏定国、圣水将军单廷珪、百胜将韩滔、病尉迟孙立、母大虫顾大嫂、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等,或则肝胆照人,或则英雄出众,或则颇具机谋,或则全凭血性,为什么都不写,而独写此素来不甚著名的蒋敬呢?要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自古时间已竟如此,何况此天翻地覆的新世界,自然更胜一层了。
闲言少叙,且讲正文。神算子蒋敬下得山来,一路走着,一路想:“此去到什么地方呢?常听得学究先生说什么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我之目的在于求利,当向市场最大处所去是了。现下市场最大处所,要推着东京,其次莫如雄州,乃女真、契丹两国人所开之商埠,百货云集,兴旺的了不得。我此刻谋利,总向这两处中拣一处是了。但是我孤孤零零,个人又没带有伴当,即到那里作什么事业方好?”这日行到东平府,见天色已晚,遂在客店中借了一宿。次日起身,客店小二进来问道:“客人可要到雄州去么?今日本处有裕东公司轮船开往雄州,船身宽大房舱很是洁净,可要定下一间?在本店里买票,比了船中可便宜一个九五折呢,并且本店在雄州地方,也有分店开着,船中本店用有招待员照料,一切客人到了那里,雇车寻宿等一应琐事,自己可以不必费心。”蒋敬道:“过了今日,几时还有船开?”小二道:“说不定,至早恐怕也要十多天呢。”蒋敬道:“既是这样,就与我打一张房舱船票来。几时开船,与我雇人把行李发下船去。此间住了一宿,房饭钱共该多少,教帐房开一张发票来。”小二道:“船开要晚上十点多钟呢,客人舒徐着是了。”小二去后,蒋敬自语道:“我正东京、雄州去处未定,那知恰有开往雄州的轮船,我就不妨到雄州去一趟,试试我的命运。”一时小二送进发票,算给了房饭钱,一到晚上把行李搬向船中。蒋敬也就下了船。汽笛一声,轮机鼓动,那船便如弩箭离弦般,冲波突浪向北而去。那东平府到雄州有一千多里海程,舟行三日夜方到。
蒋敬坐在房舱,很是气闷,便踱到甲板上望望河境。原来这时候的航路,全踪黄河通行。因黄河河道,古今迁徙无常,所以目下一些儿踪迹都寻不见,若不表明,又要遭看官的指驳。闲言少叙。蒋敬走到甲板上,四下一瞧,见白浪滔天,水天一色。天上的明月,映在水中,跟着波浪涌动,宛如万道银蛇,闪闪不已。霎时浮云一片,把天空的明月遮掩住了,顷刻全河如墨,惨暗怕人。蒋敬正欲回房,忽的浮云过去,依然是一片通明,不觉失口道:“妙哉河景。”那知就引动了一个一般玩赏河景的客人,那人道:“怪道声口很熟,原来就是蒋哥哥。在那里下船,怎地我下船时不见你呢?此刻可是到雄州去么?”蒋敬见是那人,心中也甚欢喜,口说:“奇遇,奇遇!再不料你我即在此间相遇。”
看官你道此人是谁?原来即是白面郎君郑天寿。二人就在甲板上谈起天来。蒋敬道:“郑哥,你到雄州去不是?”郑天寿道:“正是。我们同路,船中可以不寂寞了。”蒋敬道:“你此去想做些什么事业?”郑天寿道:“我么,我想仗着自己这副面目,在学界中还可以混得过,就从学界入手,开一个女学校了。那些借名念书的女学生,怕不入我彀中么?蒋哥想做什么事业?”蒋敬道:“你在学界,我自然也到学界来混混。你我在一起,遇事也可以商议商议。”郑天寿道:“你于国文、地理、历史都不擅长,如何可闯入学界,充当教员?”蒋敬道:“我于算数一道,略有片长,可以充当算学教员;枪棒虽不精,也略会使几棒,也可当一个体操教员。横竖此刻的教员,也都不过如此,谁有什么真本领!”郑天寿笑道:“那么学校中岂不都成了强盗教员么?我看你既有着神算的绝技,埋没在学校中,也很可惜的。”
蒋敬道:“然则我当做什么呢?”郑天寿道:“我替你算起来,还是投身商界为妙。现在商战世界,以我梁山上的本领,出来与他们竞争,男儿好身手,杀人不翻眼,未必输给他们。”蒋敬道:“目下商界盛行的是杀人不见血的鬼蜮伎俩,恐咱们的杀人不翻眼的强硬手段,未必定占优胜呢。”郑天寿道:“呆子,谁叫你执一不化?军师曾分付着把真面目藏起,装一个假面具出来,与新世界应酬,谁叫你不去改良呢?”
蒋敬道:“说着军师,你可晓得学究先生可曾下山?”郑天寿道:“怎么不晓得?吴学究上东京去了,也于今日动身。他因听得朝廷复行开科,考取优拔,所以去投考呢。”蒋敬道:“奇了,自去年十月朝廷颁布绍述熙丰政事书后,科举停罢,已成铁案<通鉴辑览>宣和元年冬十月,颁绍述熙丰政事书于天下。按熙丰政事,即神宗熙宁元丰时所行之新法也。新法系王安石所创,绍述者,继续之谓,曾几何时,复行反汗?堂堂政府,作出来的事,竟同儿戏一般,怪不得西夏、契丹、女真在吾国的势力,日涨月盛呢!”郑天寿道:“这总算是嘉惠寒儒的政策,只可惜那些已经脱罪的学校监督,并国民公举的咨议局新议员,又要负笈囊书的,吃那考试苦头了。”蒋敬道:“想得起来,必是吾国的读书士子罪孽深重,上干天怒,那考试的刑罚尚没有受足,所以再有这尾声的优拔科呢。不然,像军师这么样聪明一个人,如何再会瞧不破起来,此非天谴而何?”郑天寿道:“月渐西沉,夜已深了,咱们下去罢。有话明日再谈。”蒋敬道:“你在几号房舱里?明朝我来瞧你。”郑天寿道:“几号倒不曾留意,横竖好找的很,我的房就在梯子下左向第三间。”于是二人各自回房安歇。
那蒋敬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不曾合眼。心下盘算:“到雄州做什么生意?目下洋货盛行,民间穿的衣料,不是契丹布,定是女真绸,我还是做洋货罢。但洋货一道,素来不甚明白,如何可以下得手?”又想:“洋货是从洋行里卖出来的,那洋行生意没有什么在行不在行的。我此刻有的是钱,到雄州化上几个钱,弄一个康白度做做,尽日价坐马车吃花酒,玩他个不亦乐乎,岂不甚好?”既而又想:“人情叵测,世路崎岖。听得通商口岸,往往有蹩脚洋人,靠着康白度的钱作为资本,开设洋行,赚了钱,康白度不过分润几个余利,有限的很。一旦折阅,则雪花花白银,尽丢到东洋大海去了,影踪全无。恁你天大的本领,合他打官司,即使官司被你打赢,而律师费、公党费等已花掉不少。洋人则说是做生意蚀本,实在没法可想,只好出还张笔据,约日归还。你收着笔据,今日去讨,明日去收,恁你跑他百十来趟,依旧是一文没有,倒白花了许多工夫。后来自己跑的厌烦,情愿不要了。我到雄州,又是第一次,地陌生疏,凭你是梁山泊英雄,恐也没处施力呢。”后来忽地想着道:“我真呆了,枉称做神算子,连这些都算不就,不惭愧死了么?商场竞争,全靠着交通机关的灵便,交通机关,不就是银行么?目下本国人开的银行,好在尚不甚多,我到那里,何妨就组织一爿银行做做。好便好,不好时,哼,哼!不怕不倒他个二三十万银子,那不是安安稳稳的事业么?”主意想定,也就睡着了。
次日醒来,只听得机器声轧轧不已,夹着船外的风涛声,颇为壮丽。那一丝丝的阳光,从窗隙中直射进来。蒋敬忙着起身洗毕脸,即到白面郎君郑天寿房中。见天寿尚没有起身,遂唤道:“郑哥,郑哥!睡的这么晏,一下山就失掉英雄本色么?”天寿打着呵欠道:“倦的紧。船尚没有到码头,起来做什么?”蒋敬道:“特来与你谈谈。”天寿道:“很好喂,蒋哥,你可晓得本山尚有弟兄在这船上么?”蒋敬道:“是那个倒没有知道呢。”郑天寿道:“起初我也没有知道。昨晚与你分手后,回到房中,只听得隔壁大呼捉贼,咱开出门去看,只见一个黑影闪将入来,咱就一把擒住。那人开口道:‘郑哥,放松些,小弟是鼓上蚤时迁。’问他到船上来做什么?他说也想上雄州寻些生意做,因见你隔壁房中的人行色甚壮,一时手痒起来,想弄一个盘费。那知是个鸦片烟鬼,通宵不睡的,险些儿着了道儿。咱问他:‘你是个贼子,到雄州去做甚生意?’他道:‘我此刻是个梁山实缺道了,做起生意来,也可称为大人了,怎么不好在商界里头混混呢?’”
蒋敬道:“照时迁的敏活手段,偷天换日,在商界算起来,果然是个出色人员。我今天告诉你一桩事。我到雄州,想组织一爿银行,商业、储蓄兼做。做了商业,可以发行钞票,做了储蓄,可以吸收零星散银。那发行钞票的利益,很是洪大。譬如我有银子十万两,再发行十万两钞票,不就变成了二十万么?并且十万两钞票,不见得一天中人家都拿来兑换的;算他有十分之一前来兑换,只消预贮着一万金就够了。再者十万两钞票,一年中不见得完完全全一张没有失掉的,水里火里要毁坏多少,经过的手多了,融掉的也必不少。即此一端,那个利益已经不少。且现银可以借给人家,又可以取利息,那银行借出去的钱,并且都有押抵,或是房屋。或是货物,千稳万稳,再没有风险的。自己名声大了,受了社会之信用,人家存款,整干整万,像堆山般堆压进来,我就把存款银子,再去发行钞票,再去借给人家,这个利益,可以算得清楚么?郑哥,这还是规矩办法呢。倘用奸滑手段做得起来,哼,哼!还不止此数呢,还不止此数呢。”郑天寿道:“到底有几许利益?何妨说出来,让我听了,也学个乖。”蒋敬道:“那是难说难言。”
两个人正说着,不提防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大声道:“唷,唷!好个难说难言。你的心比墨还要黑了,真不愧为神算子,可怕,可怕!”二人唬了一跳,回头急看。蒋敬道:“我道是那个,原来即是你。你这个人总是价贼头贼脑贼腔不脱,窃听人家私语。须知文明公例是不兴的,现下闯到新世界上来,也须改去些才是。”郑天寿道:“也亏他的贼智,竟使我们一些儿都不觉着,咱家问你多早晚到此间的?”那人道:“唷,唷!文明面目,强盗心肠,竟把假面目在我跟前施起来了。告诉你还早着咧。我们是一伙儿人,你们的性情行为,我肚里头早烂熟了呢。”正是:密室谈心,隔墙有耳;晓窗共话,意外人来。欲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再讲。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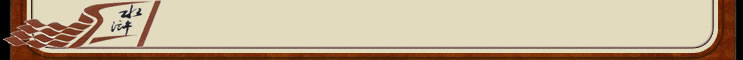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