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十回 郑天寿恃强占妻妹 章淑人被刺控公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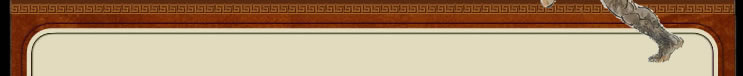 |
|
话说蒋敬、时迁正在谈论,忽报客到。蒋敬道:“必是来提取存款的,快教他五日后再来。”时迁道:“未必么。我们门口的长红告白,来客必定瞧见的了,倘是提取存款的,也不进来请见了。且请会了再说。”于是蒋敬、时迁齐至会客室,见来客前发覆额,其齐如剪;面白唇红,香气扑人。身上穿着西湖色春纱夹衫,实地纱马夹,胸前挂着花球,足上洋式皮靴,靴上的鞋油揩抹得光亮照人,走起路来,橐然有声。突然一见,竟认不出是谁人。
时迁眼光尖利,早已瞧清,开口道:“不是郑天寿哥哥么?打扮得这个样子。乍见了几乎认不清楚呢。”郑天寿道:“君真少见多怪,我如今是新学界人员了,新学界人员那一个不这么打扮?”蒋敬道:“长长的前留海,光光的油松辫,仿佛是个女学生。须知你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呢!”郑天寿道:“蒋君,亏你也是新世界人物,见识如此的顽固,连修饰学改良都不知道么?”时迁道:“郑哥一闯入新学界,竟像换了一个人是的,叫起我们来,某君某君,连自己弟兄都不认得了。”郑天寿道:“君真顽固极矣!这乃是学界上通行的新称呼,怎么说我弟兄不认?”蒋敬道:“这都是无谓之谈,不必说了,我们讲正事罢。你这许多时候,办了些什么事呢?”郑天寿道:“我办的事,一时那里说得尽,若编起小说来,一大部书好做。”时迁道:“这样必定新奇的了。我连着到过你学堂三次,多不曾碰见你,你们女学堂,又不能随随便便进来的。请问你到底在不在?为甚总不肯接见?”郑天寿道:“对不起的很,我实在没有知道。不然,总到你行里来回拜了。”
原来郑天寿到了雄州,就开一所女学堂,取名“尚德。”这时候风气初开,女学很少,一班开明绅士还在提倡女学,说什么女学系母教之根本,女学盛则家庭教育自会发达,这种很好听的议论。见了郑天寿开办“尚德女学堂”,那有不赞成之理?经众绅士竭力鼓吹,“尚德女学堂”声名顿时大振起来:学科如何完备,规则如何严肃,卫生如何讲究,附近各处的巨家闺秀、富室名姝闻了名,来的如云蒸雨聚一般,把个“尚德女学堂”塞了个足,郑天寿好不欢喜。那郑天寿的欢喜,果为学堂发达不是?明眼人自会晓得,无庸在下饶舌了。不过有一桩异处,这郑天寿平日间没一天不出来闲逛的,即在梁山上,每天少说些总于三五会出哨。说也奇怪,自从开办尚德女学堂后,马路上竟有终月不见他的踪迹。
一日新进一个学生,这学生乃是白面郎君郑天寿的妻妹,已经出嫁,颇有几分姿色,在娘家时,与姊夫郑天寿,本有些不明不白,郑天寿的妻子,为此气恼成病而亡的。及郑天寿上山做了强盗,好些时不通音问及,此番到雄州开办女学堂,却又碰着了。原来雄州自辟为商埠后,五方四处的人都来相聚,郑天寿妻妹随母到此看洋人赛马,因见地方繁盛,即便住下。住不及半载,就有人来说合,郑天寿妻妹遂嫁给雄州近乡一家士族。丈夫章淑人,生得身材短矮,品貌猥琐,且索性良懦,以<水浒传>人物比拟起来,只有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差堪伯仲,并且武大有一个英雄的胞弟,章淑人则有一个豪侠的胞兄,其处境又很相似。那章淑人娶了这妇人后,夫妇间虽不十分恩爱,倒也还可以过得去。事有凑巧,一日适逢星期,学堂照例放假,郑天寿出来闲逛,却碰见了岳母,询问情形,方知妻妹已经出嫁,也随即丢开。
次日,天寿起身尚在梳洗,门上报有一女客求见。郑天寿握发出迎,见正是新嫁的妻妹,心下好生欢喜,忙问:“妹子何来?”那妇人现出怨恨的样子道:“特来瞧瞧贵学堂的学生呢。我听说女学生都是天仙般的人,又有学问,又会说话,又聪明,又能干,所以特来见识见识。只恐握我们这样粗蠢呆笨、不识趣的乡下人,人家见了惹厌,不肯给我介绍呢。”郑天寿道:“女学生也不过如此的,为什么不肯给你介绍?”妇人道:“我可不信?若不是天仙般的人,你为甚么开了学堂,从不到我那里来?不知道也不来怪你,昨天见了我母亲,知了我住处,也不来瞧我一瞧!只有我这不识趣的人,人家厌弃我还厚着脸老远的赶来呢。”郑天寿默然不语。妇人道:“你不理我,我知道了,岂不为我来了,你心下不舒服?我马上去是了,让你们快活些。”郑天寿道:“你屈杀我了。我听得你来欢喜的什么相似,你不见我握着头发出迎么?连梳头也来不及。”妇人道:“你这种假话,去讲给人家听,我是不信的。你既这样欢喜我,昨日知了住处,为什么不来瞧我?”郑天寿道:“你如今有了丈夫,我来很不便呢,况昨天碰着岳母,时光已经不早。”妇人道:“亏你是新学界中人,也说出这样话来!现在文明世界男女平权,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他不能管我。我也不能管他。况‘丈夫’两个字,并没有什么贵重,‘夫’字乃男子之通称,所以耕田的叫作农夫,捕鱼的叫作渔夫,樵柴的叫作樵夫,拖车的叫作车夫,拉马的叫作马夫,以至挑担的叫挑夫,扛棺的叫扛夫,抬轿的叫轿夫,与丈夫的‘夫’字有什么两样?昔人说‘人尽夫也’,就是这个意思。你想丈夫既不足贵重,我惧惮他什么?还有一说:称男子为丈夫,尚是尊敬之词,其实现在的世界,丈夫已是绝迹没有的了。”郑天寿惊道:“你的话愈说愈奇了!怎么世界上丈夫已是绝迹没有?”妇人道:“十尺之谓丈,丈夫者,身长一丈之夫也。请问现在世界上有身长一丈的人么?”照此说,必文王可称为“丈夫”,商汤九尺,曹交九尺四寸,项羽八尺余,孔明八尺,俱不足为丈夫;欲为此妇之丈夫者,不亦难乎?一笑郑天寿道:“你的议论,真是透辟不过。”妇人道:“承你谬奖。我问你:到底厌弃我不厌弃?”郑天寿道:“那个厌弃你?除是他人厌弃,我终没有厌弃你的日子。”妇人道:“你如真的没有厌弃我,可依我一事情,我就信了。”郑天寿道:“依你,依你。莫说一件,一百件也依。是什么事?请快说了。”妇人道:“这事恐怕你不依呢。你如果真爱我,可快给我把这女学堂关闭了,或是你自己辞了出来。”郑天寿听了,吓得目定口呆,半晌说不出话。妇人催道:“肯从与否?请速答一语。君虽白面,尚是郎君,何忽面腆如女子也?”郑天寿道:“这句话教我如何回答得出?可否恳你换一个题目罢。”妇人道:“你既不肯闭掉此校,又不肯自己辞出,则此校的滋味,不问可知了。你恋着这所女学堂,照理我本不能来干涉,但我总舍不得你兰花一般秀,大虫一般健的人,不成教他们淘坏了么?你不肯听我,我也没法。如今还有一事要求你,我也到你那学堂来读书如何?”郑天寿道:“很好,很好,请你马上进来是了。”妇人道:“那么,我回去部署部署,明日即来。”
过了一日,那妇人果然搬了进来,一般的随班听讲。诸同学有知道底细的,未免要半真半假的谑浪笑傲。这妇人也不是好惹的,如何肯让人家?便常常的斗嘴弄舌。
时光迅速,夏去秋来,转瞬又届年假之期。年终大考,恰恰这妇人分数最高,获了个头名,阖校哄然。有两个学生约会了到这妇人房里来庆贺,说几句冷嘲热骂的双关话儿。一个道:“似姊姊这般用功,在我校中本是独一无二的,自应考个头名,我们也都替你欢喜。但这功课分数,填写的不甚恰当。姊姊的体操功夫,是精妙绝伦的,校长郑先生赏识姊姊,也不过就为此体操功夫,怎么体操分数,倒并不填足,那不是笑话么?”一个道:“像姊姊的体操,柔软兵式,各都登峰造极,同学中那个不钦佩你?”妇人道:“此间的体操,只有柔软,没有兵式,我如何会登峰造极起来?”两人齐道:“姊姊休谦,只要问校长先生,就知道了。”妇人听毕,顿时两颊绯红,有些没好意思起来。两个再嘲笑一阵,也就退出。
一时郑天寿进来,妇人就哭诉其事。郑天寿道:“他们有口,尽他们去说是了。横竖年假了,你我聚的日子长呢。”妇人道:“章家这乌龟,来干涉起来如何?”郑天寿道:“你只管放心,章淑人这厮不来便罢,他如要干涉你我,哼,哼!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便是他的榜样。”妇人道:“你我还是住到母亲家去,还是仍住在这里?”郑天寿道:“此间是学堂,总部恐有人来说话,住在岳母家最好。”妇人称善。于是年假后,郑天寿共这妇人,就在雄州居住。
章淑人得了消息,三回五次派人来接,妇人推说假期补习,不能回家。淑人没奈何,只得听其所以。后来淑人的哥哥章谷盛,瞧不过起来,对兄弟道:“你这个人太忠厚了,妻子被连襟占着,竟没法子管理么?”淑人被乃兄说了两次,只得硬着头皮,自己去找。找到岳母家,这妇人却避而不见,郑天寿也不来招呼。淑人一个人在客堂中坐了许久,连鬼都不见一个,忽自笑道:“呆子,我又不是外人,他们不出来,难道我不可进去的么?况我来找他,他如肯见我时,也不用来找了。”想毕,举步向里,一径登楼。谁知郑天寿伏在暗里,淑人从亮处走来,如何会瞧见。看看相近,被天寿举起手来,陡地一拳,打个正着。淑人蓦然悟会,知道彼等不出相见,正欲己之入内也。忙着向外奔逃,郑天寿如何肯舍,拔刀相追,口里说:“今日杀掉你这乌龟。”一个前行,一个后逐。究竟郑天寿做过强盗的,跑的如追风逐电般异常迅速,一瞬间已经追到,把刀略按一按,向后心飕的就刺。淑人忙着回身,恰恰刺在臂上,顿时鲜血直流。郑天寿再要戮第二刀时,站岗警察已经闻声而来,郑天寿乖觉,看见警察走来,忙着避警察搀起淑人,唤乘街车送回家里。
淑人的哥哥谷盛,瞧见乃弟如此狼狈,询问情形,淑人从头到尾细诉了一遍。谷盛怒道:“此而不报,枉为丈夫!目下第一要着,先到雄州州官衙门去告发,抬着请验,怕不扳倒他么?”淑人道:“大难,大难!我听说学界人员都与官府联络一气的呢。”谷盛道:“恁他联络一气,总也讲个理儿!”淑人道:“我终不敢。”谷盛道:“助你一臂力是了。”于是兄弟二人做了个禀帖,直到州官衙门喊控。州官瞧过禀,验过伤,立刻批准。向二人道:“此事如果是真,还当了得,你二人且退去候着。”二人应着出去,各颂州官明察不提。州官马上签票,饬传尚德女学堂校长郑天寿到案听审。一时回报说:“郑天寿患病,不能到案。”次日学界进了张公呈,说:“郑天寿是日在南园与学界同人商议要事,自晨至暮,不曾离园一步,离园且不曾复,何能持刀逐人?章氏所控,必虚无疑。”州官接了学界公呈,遂把此事搁起不究。郑天寿依然逍遥法外,无患无悉。章淑人见势力不敌,只好饮恨吞声。怎当得乃兄谷盛一再掇撺,淑人于是再到州衙去进催办禀帖,州官终是给你个留中不发。
谷盛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判刻几张传单,把此事宣布开来。”于是一面印发传单,一面派人去知照郑天寿,说:“你如爱这妇人,只消偿还婚费银六百两,此妇即归郑姓,章姓当出立离婚契。”郑天寿接着此信,忙与妇人商议。在郑天寿的意思,原要妇人自己拿出钱来了结此事,那知妇人也拿不出这许多银子。妇人道:“你学堂开了近一年,银子赚下不少,难道区区六百两,尚拿不出么?你若拿不出银子,我的性命必给你送掉呢。”郑天寿道:“我有银子还等你开口么?所有收进来的钱,都汇到梁山泊去了。此刻莫说六百两银子,即六十两也难。你若有时最好,如果一时拿不出,且向岳母商借了,俟我有了钱,还他是了。”妇人无奈,只好去向母亲商量。他母亲道:“我的儿,做娘的又没赚钱之人,所有你父亲遗下的几千两银子,这几年的用度,连嫁你姊妹两人,差不多完快了。此刻只有二百两银子,是我老来的棺材本,即全数给你,也属不够。你还是同姊夫商量罢。”妇人道:“母亲,你既有二百两银子,何不拿出来给了我罢。你百年长寿后,横竖有我们来收拾你呢。”他母亲道:“唷,唷!我可不想,你们休来骗我!”妇人见不是头路,回到房中,哭了一夜。
次日章淑人又派人来催,说限三日缴银。妇人见郑天寿不肯拿出钱来,自己又没有这注银子,左思右想,没有解免的法子。忽地心一横道:“都是我自己造下的孽,:不如死了,省得拖累着人家。”想定主意,遂提笔写了一纸绝命书,写毕,把左手戴的金戒强脱下来,望嘴里只一推,狠命咽下。正是:埋地下之优,土花长碧;洒生前之泪,绢帕成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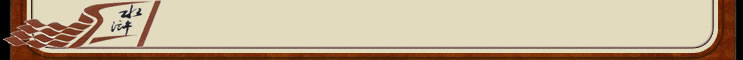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