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快意恩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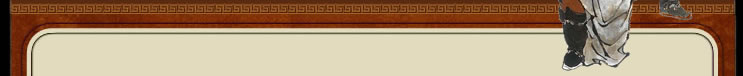 |
|
“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
这些都是在侠义小说中最容易见到的话,把它们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
早在《史记·刺客列传》里,就可看到对“快意恩仇”的演绎,传中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为报恩慷慨赴死,为报仇亦慷慨赴死。他们惨烈的行动,固然有如荆轲刺秦王那样兼及力抗暴秦的天下公义的,但更多的是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游侠列传》中的大侠郭解,则“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
到了唐传奇中,快意恩仇更是成了那些来去倏忽的侠士行侠的主要动力,或报主人之恩,或酬知己之情,或复家族之仇,演绎不尽的是个人恩仇,红线、昆仑奴、聂隐娘、古押衙、谢小娥、贾人妻……,莫不如此。
《水浒传》也不例外。晁盖等为报宋江通风报信活命之恩,一在梁山扎稳了脚跟,就派刘唐给送去百两黄金;宋江为报坑陷之仇,江州法场上刚捡回一条命,就带众好汉攻破无为军,活捉活割了黄文炳;梁山好汉为报朱仝几番相助的情分,不惜使出辣手,派李逵劈死小衙内,强拉朱仝上山;石秀为报被冤屈之仇,怂恿杨雄将老婆潘巧云开膛破肚……水浒世界里,最能体现这种快意恩仇精神的是行者武松。他的人生行旅,几乎就是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为报兄长无辜被害之仇,诛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报施恩几顿好酒好肉之恩,醉打了蒋门神;为雪张都监倾陷之恨,鸳鸯楼连杀十五人,直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刀光血影里,武松俨然如一座威风凛凛的金甲的复仇之神。(在“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里,对此将细为分说,请参看)整个梁山大寨更是要讲究快意恩仇。除了要对宋江、朱仝、柴进等人先后报恩外,更不忘的是血腥报仇:只要是梁山好汉的对头,无论是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还是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只要庄园或城镇被破之日,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一定是不分良贱、满门尽灭!
说到这里,也许列位看官中有的朋友已经从这“快意恩仇”中嗅出了阴冷的气息。对此加以深省,不能说没有必要。
在鲁迅先生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頵以病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说的是,三国时期吴国有个叫朱朗的家伙,他的父亲是个专搞一些乌烟瘴气的不法勾当的道士,流窜到会稽郡一带,被乌伤县的县令陈頵抓住杀掉了。这朱朗暗中图谋替他那被正法的老爸报仇,一直没得到机会。等到陈頵病死,朱朗便刺杀了陈頵的儿子,而后逃到魏国。魏国听说了他“孝勇”的名声,便提拔他做了将官。
对此,鲁迅先生写了一段按语,大加鞭挞,说按道理,一个人犯法该杀,那么其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报仇的义务,况且即使要报仇,也只应找正主,现在朱朗的父亲做了坏事被杀,死有余辜,而朱朗竟为了报仇杀了县令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博得了“孝勇”的好评,且受到提拔重用,充分暴露了国民性中丑陋的一面。
的确,这件史事的结尾,让今人读了觉得恶心。
但问题是,今人觉得恶心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却受到了赞美,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心中有一个近乎于天经地义的价值信条,那就是:快意恩仇。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有恩报恩,哪怕这恩人是个恶棍;有仇报仇,哪怕其曲在己,并且不惜滥杀无辜,而理性和良知,从来就是完全缺席的。
如水浒世界里的青面兽杨志,被发配到大名府后,得到梁中书的赏识,因此列位看官便看到,梁中书要将自己搜刮来的金珠财宝即生辰纲送往东京蔡京处、请杨志押解护送时,好汉杨志是何等的替他的赃官“恩相”竭诚尽力。怪只怪他的运气太坏,遇到老谋深算的吴用,使他这个老江湖竟而栽了,没法交差,最后只得窜入山林。杨志的落草,实在是因此后报恩无门,且不得已而避祸,绝不是因他的觉悟提高了,要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这里不妨做个杀风景的假设,假设梁中书能“明察秋毫”,派人找到流荡江湖的杨志,对其温言劝慰,道些“生辰纲一事原委已尽知,皆系老都管等掣肘误事,闻君匿迹江湖,风波寒苦,不胜悬念,冀速归”之类,那么以杨志的“觉悟水平”,会不会感激涕零呢?哪位看官还能保证此后水泊梁山中照样还会有青面兽杨志这号人物?
至于说到梁山好汉及整个梁山大寨的复仇,固然有诛锄邪恶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血腥屠戮带来的快意,便如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
毫无疑问,复仇的杀戮会带来莫大的快感,即所谓“快意”。所以即使在《水浒》之后的武侠小说中,也常可以读到类似的情节,如民国时期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秀莲杀死武功高强的恶霸苗振山,殊无快意,“因为苗振山不过是一个恶霸,并非我的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慕白终于杀死了仇人黄骥北后,“痛快得他要发出狂笑来”;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要求金世遗只能助她复仇而不准替她复仇,仇人孟神通必须得死在她之手。又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弟子农夫听说当年重伤他的欧阳克已死,竟会勃然大怒,怪别人多事,使他不能亲手杀仇人。但若他一直没能力或没机会亲手复仇,那恶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他人又当如何?这却没兴致去考虑。同样,《飞狐外传》中的侠女袁紫衣,为了能对她那恶贯满盈的父亲凤天南快意恩仇,决定救他三次不死,以报生身之恩,然后再亲手杀死他,以报逼害母亲之仇。为了实现这计划,袁紫衣不惜在凤家祠堂外引走了正要杀凤天南的胡斐,导致钟阿四一家惨遭凤的报复而被杀害,但是侠女袁紫衣对钟阿四一家的惨死并无半点内疚,侠肝义胆的胡斐对袁并无半点责怪,素有香港“良知的灯塔”之称的作者金庸在叙事里对此也并无半点批判,读者对此也很少提出异议,这后面的三个“并无”和一个“很少”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它们说明具有悠久传统的快意恩仇对国民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它竟而会造成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
也正因如此,水浒世界里,宋江攻破祝家庄后,一度要下令洗荡了祝家庄,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了。不过总算有曾得钟离老人之助的石秀求情,祝家庄数千人众,才终于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免遭尸横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梁山大军的刀斧下的厄运。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