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32章:神医叫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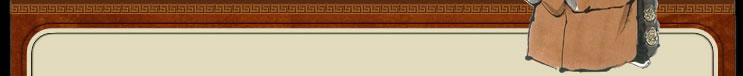 |
|
只见那叫化子出了街口,往右边胡同折去了。戴宗见了,便赶快了脚步,追上前去。一霎过了街口,进了胡同来。便见得一条胡同细巷,望里延去,长短莫约三十丈,两侧一色青砖瓦墙,中间漏了二三处朱扇门户。静悄悄的,看不着一个人,也不见了那叫化子影踪。戴宗心下疑惑,便四处张望。见得四处连个鸟影也没有。那戴宗生怕自个花眼,揉了揉双目来望。仍旧是一般的静杳杳,渺不见人,耳畔只听些远处的喧闹声响。戴宗看此光景,暗想老叫化好快的脚力,却去了甚么所在?便靠墙边站了,细目来望。方立住了脚,猛听得前面嘭的一声,甚么落在地上。戴宗连忙疾看过去,见得青石板路面陡然添了一口牲畜,白毛毛的,一动不动躺在地上。行近看时,却是一只兔子,雌雄难辨,气息已经全无。戴宗心下又一阵狐疑。闪神思索间,听得耳边又是一阵疾风响起,见得另一只兔子打苑囿内里飞了出来,嘭的一声,落在自己身旁。端的黑乎乎,也已气绝。戴宗心下一凛,连忙出了街口,看个角落匿了身,提了神来看。却再不见有甚么兔子飞来。等了良久,只是不见动静。戴宗便息了心,有些气蔫,拾脚要走。
殊料方提起脚尖,听得胡同里面一家门户打开了开来,咿呀一声,噌噌噌出了人来。戴宗便把身匿了,举目看去。见得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急急脚望近走来。到了路中央拾起两只兔子,望门口闪去。不是老叫化是谁?戴宗心下费解,暗道:“好你个叫化的!搞甚么名目来?”寻思之间,见那叫化闪进门去了。身影有些眼熟,勾得看者来了兴致。那戴宗便提步冲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一阵风似的到了门口。见得那叫化子已然进了门内,正掩着门扇,剩下一条指缝没有扣上。戴宗急了,赶忙拿了朴刀冲进门缝处。里面那人见一柄尖刀插了进来,手下一松,便看见戴宗挤了进来。
叫化子见来了人,来不及掩锁呐喊,噌噌噌的望望前跑去了,迳到门口,释了兔子,交给一个青衣手里。不一时,闪进里屋去了。那青衣接了兔子,放在门口瘫了。空了手,抬起身来堵了门口,生防戴宗入去来。嘴里不停吆喝,引得近处几个青衣纵身前来,一道拦截戴宗。那戴宗进不去,便顿一顿身,施了礼,唱了喏,道:“几位小哥,好歹行个方便则个。”那四个小厮相互对望了一眼。见是生脸,自然不肯放手。却不动怒,笑道:“敢问官人,前来邀约那个?”戴宗怔道:“便是方才入屋的那个哥哥。”小厮哦一声,笑道:“那是咱家的姑爷,不肯见人,官人请回罢了。”戴宗道:“姑爷也好表哥也好,但求行个方便,让一让步。小可有事请教那个哥哥。”小厮道:“不管谁人,但凡自身上门的,不经咱家妈妈点头,便休想进得去。小的怕坏了衣钵,不敢放大官人进去。”戴宗笑道:“这有何难。此间二十两白银,四位哥哥拿去平分了。好歹放我进去一遭。小可斯文人物,必不生事。”说罢,果然从怀里取出一锭银子。那小厮见了银两,彼此咬耳一阵,自消受了,道:“小的一时招呼不周,官人莫怪。进了门时,直到花厅找个位子看茶便了,小的却不指引。”戴宗微微一笑,道:“这个自然,不敢再劳两位。”便入了屋去。
进得来时,见得里面却是一个精致的花厅。那花厅正墙,开设了一道亮敞敞的红棂门,对开八尺见宽。门口一个徐娘,手里捻了画绢,招啊摇的,引得许多客人入来,进了花厅。戴宗心想,原来此间方是正门,适才来的却是后门。怪不得人影好生冷清。却看此处,方是一番热闹天地。看得一拨拨来客,悉数到了花厅,寻个位子坐了,由小厮招呼看茶来。戴宗也看了茶,张目四顾。见得掌灯结彩的,人来人往。那花厅落来两级,由一道木梯子引到上层。上层四处栏杆,成了一个厅井来。那厅井四周,倚了许多红颜粉脸。见戴宗抬头看去,一个个挤眉弄眼的。戴宗心想,直娘贼!万想不到,入了烟花之地来。暗骂着,又吃了两盅茶。便见一个老鸨模样的女人迎上前来招呼,一脸笑容,做作道:“呦,官人好生面生,怕是头一遭光临寒舍?”戴宗道:“妈妈说得是。”老鸨道:“官人一身精猛,老身便撮合一个浪姐与你。可好?”戴宗道:“且不劳妈妈费心。小可清扰,只想求见一人。”那戴宗一心要见那叫化,哪有心情作乐。老鸨道:“敢问官人要会那位?”戴宗道:“便是那个装扮叫化的哥哥。”老鸨听了,眼中闪过不欢神色,道:“官人见谅,老身不知你说那一位。”说完退了出去。
那戴宗心下不是滋味。在花厅等了一晌,不见那叫化子出来,便抬了脚,依原路出了门口来。见那几个小厮依旧张罗不停,只不理会他出来。便心下一动,暗想,一不做,二不休。今儿便匿在院落无人处,看他出不出来?主意定当,便望来到厢房外首树荫下,由树桠掩着坐了。
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那戴宗坐了一柱香工夫,见得后门探出一个东张西望的脑袋。看看没人了,走了出来。那人手里提了药囊,正是那一身破落的叫化子。戴宗看的细了,益发感觉那人眼熟。当下也不打话,只匿身看那叫化举动。当下见得那叫化子步如流星,直楞楞到了院子中央,看兔子跟前停了。俯了身,打开药囊来,拿出药刀针线,看准兔子施起法来。戴宗一心好奇,睁开大眼看了半晌。见那叫化动作忘情,便到他身边一起蹲了。那叫化也不察觉。戴宗便在侧旁打量他的颜脸来。见得一盏破旧方巾下面,掩住一张污垢的面皮。那污垢后面,却是一脸标致的五官,三停匀称。一头乱糟糟的蓬发散落下来,遮了半边脸,再看不清了。见得那叫化子手里拿了针灸,看准兔子经络穴位扎去。一连扎了上百针。毕了又用手指看四处推拿,似是帮兔子活血。不移时,见的那兔子四肢微微一抖,活过命来。叫化子便舒一口气,擦擦额头的沁汗,又来救治另一只兔子。只片刻工夫,见有了气息来。老叫化微微一笑,伸了伸脖子,舒口气出来。当下起了身,到井口勺了一瓢水来。回到原地,把兔子上肢提了,喂他喝水。见得那兔子顺喉吃了水,当即张开了懵眼来,不一阵便落地活蹦活跳开了。戴宗心想,真神医也。
脸上却不声张。见得叫化又是舒心笑了一笑,戴宗道:“兄弟,你怎地也来了东京?却不来找我。”那叫化听了说话,全身一震,方留意到戴宗来。当下别了脸出去,掩口道:“兄台恐怕错认他人了。”戴宗笑道:“决计错不了!你便是我安道全兄弟。来来来,再不要玩儿,招呼哥哥进屋吃茶。”叫化听了,又道:“兄台当真错认人了。小可姓王,单六字,却不是你甚么兄弟。”说着便站了起来,转身要走。戴宗心下益发疑惑,便连忙起了身,拦了他去路,道:“兄弟何苦改名换姓来。再别要捉弄哥哥。”叫化道:“老叫化与兄台素昧,哪敢捉弄兄台。兄台请回了。”戴宗道:“你乔了装,我虽认不清你的脸,却认得你手腕上的瘢痕。”叫化道:“老叫化手腕瘢痕怎地?”戴宗道:“往日兄弟帮公明哥哥医治背疮,因去深山采青,给那响尾蛇咬了一口,染了一手毒气来。”那叫化子嗤笑道:“胡说!”戴宗笑道:“兄弟,你虽不认,却否不得口。你中毒那遭,还仗了我去买药解毒。山上湿卤,罕有那满天星药青。为兄连夜到济州城内,买了二十斤回来,救了你一命。心下欣慰,是故记得。莫非你到忘了?”那叫化听得戴宗说话,半晌不吱声,只顾在地上冷冷笑着。戴宗道:“到我回山时,你的毒势已见发作,右手红肿溃烂。后来虽说用满天星止了毒来,却落得满手疤痕。”叫化又是一声冷笑,道:“恁你说得怎生动听,我只不是你兄弟。”戴宗道:“兄弟,怎生这遭你这般教人不解?为兄便算错认了你的手腕,终不成天下另有他人,有兄弟你这般神奇医术?兄弟只招了罢了。”
那叫化子道:“老叫化家传医术,不见得怎生高明。兄台错认了人,还是快快请回吧。”戴宗喝道:“兄弟!你恁地不认兄长!终不成忘了往日情义?忘了梁山所在?”叫化冷笑一声,点头道:“梁山?叫化子知道是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拨强盗,专门杀害忠良,残害无辜。”戴宗厉声道:“安道全,你胡说甚么!你便不认我戴宗,也断不得诋毁梁山好汉。”叫化冷笑道:“好汉?那一个是好汉来?”戴宗道:“那一个不是好汉?那一个不是响当当的好汉?鲁智深兄弟行侠仗义,武松兄弟舍己予人,林冲哥哥忍辱负重,李逵兄弟敢作敢当。你说,那一个不是好汉?”叫化冷笑一声,道:“鲁智深?老叫化只知道他一个玷污神灵的蠢人,终日在神殿幔帐后拉矢。武松?清河县杀害兄嫂,何仁何义?林冲,沧州杀害庄稼老翁,专勾无辜性命。李逵,只宋江身边一条狗!再看其他,那个称得上好汉?”戴宗骂道:“臭叫化子,没出息,是非不辨!依你说,梁山没有一个好人。那宋公明哥哥一世忠义,又怎地说?”叫化道:“宋江罪大,不折不扣一个魁首!一生专为些为非作歹的勾当。”戴宗道:“直娘贼!你说说来,哥哥做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勾当?鸟嘴乱叫,含血喷人!”叫化冷笑道:“宋江设计陷害卢俊义,累他家破人亡的,可算为非?打大名城之时,只为身上疽疮小疾,不顾卢员外石秀等人死活,执意退兵。可算作歹?此人好称忠义,我不见丝毫忠义所在!”戴宗道:“直娘贼的!不通便闭上你的鸟嘴,不要放出屁来!当日宋公明哥哥兵退大名城,原是为了晁天皇梦中托言,方无奈退去了。你懂小鸟鸡毛?”叫化冷笑道:“说是晁盖托梦!何曾见过给你我托过一个梦?捎过一句话来?那宋江本来心生退意,又别无他法。便撒了谎言,好施施然归山去。”戴宗道:“臭叫化!你再罗嗦,我便杀了你,省得两耳干净。”叫化道:“杀便杀,杀也要说话。戴院长,你心肠倒好,终是缺了心眼,跟了宋江此种屑小,自毁了一世英名。”戴宗道:“讲活讲全套,救人救到好。你要说不明白,叫你成为刀下亡魂!”叫化道:“那宋江素来装神弄鬼的。便不算这遭,说他忠义堂里石碣受天文那回,不一般做了手脚?便你等蠢人尽信了他。”戴宗道:“撮鸟,闭嘴!满口胡说八道,少不得我真一刀喀嚓了你。”叫化笑了笑,道:“我也是一心为你好来,不想你受人蒙蔽。若然说到你恼处,杀了我便是。”戴宗道:“臭叫化的,再罗嗦我可真不客气了!”说着,举手作势要砍过去。叫化笑了一笑,道:“来来来,望脖子结实处砍来。”说着,指了指自个后颈。戴宗听说,果真恼了,便抬脚噌一声踢了过去。叫化子来不及闪躲,打得跌在地上,哎哟哎哟喊叫起来,引得一拨青衣前来帮腔,要拾掇那戴宗来。戴宗原本一时气恼,方起了一脚。见真伤了那叫化子时,心下好生不忍。便蹲了落来看他伤势,帮他揉了揉痛。叫化子道:“滚!滚!少来装腔。叫化子自个料理得了。”戴宗笑了笑,道:“自个料理得了,那便最好。”说着,把叫化头巾扯了落来。
那叫化子少了头巾遮掩,露出了一张文儒面目来。戴宗收在眼内,道:“再抵赖不得,你便是我安道全兄弟。”叫化道:“便是,又怎地?再无兄弟情份。”戴宗嚷道:“哎吔吔,说上说下说人负义,你便是最负义之人。”安道全道:“我怎地便负义了?”戴宗道:“可记得在建康府别了张顺那时?我怎地对待你来?平时又怎生待你来?”安道全道:“自然记得。我说些你不中听说话,也只是为了你好。”戴宗道:“多谢。若果然为了我好,好歹叙个兄弟情份。”安道全一阵默然。那小厮见了,便要揪了戴宗来打。安道全喝道:“住手!不可对我哥哥无礼。我兄弟二人拌嘴不必你等干预。”戴宗听了哈哈一笑,道:“正是。”安道全道:“罢罢罢,好歹一场兄弟,且随我上楼歇歇脚儿来。”说完,举步便走。戴宗一笑,也跟来上去。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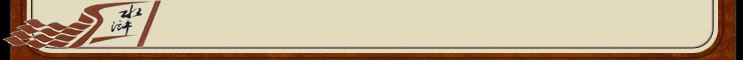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