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智取生辰纲与强盗逻辑 左子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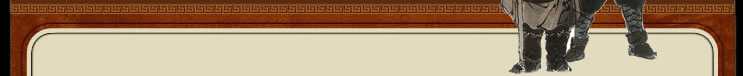 |
|
原载:《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一期
一部《水浒传》说的都是强盗逻辑。
要从理论上驳倒强盗逻辑并不难,但要使强盗逻辑不能成立,换言之,要使强盗觉得没有做强盗的必要就很难了。说到底,这是有关赵宋政权整个官僚体制和整个官僚阶层利益的问题。如果整个官僚阶层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并希望继续获取更多的利益,就必须维持这种体制。这样,强盗逻辑就成立,就有人或更多的人要做强盗。
不必为梁山的聚义者们讳,他们就是一个武装的盗匪集团。这样说,丝毫没有减轻统治者的罪责,也丝毫抹杀不了他们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逼良为娼的这一基本事实。清人徐珂在《两粤盗风之炽》中说得很清楚:
两粤盗风之炽,甲于通国……粤人贫富之不均,甚于其他省,富者极富,而贫者极贫。贫人既无生计,饥寒亦死,为盗而为官所捕亦死,等是一死,而饥寒重迫必死无疑。为盗虽犯法,然未必为盗者人人尽为官捕,即捕,亦不过一死。是不为盗则死在目前,且必无幸免之理,而为盗非特目前不死,且可以侥幸不死。既若此,是亦何乐不为盗也。
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无疑是引发各种刑事犯罪和社会动乱极为重要的因素。“贫困是最主要的潜在的不稳定源”(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语),是“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寻找不正当的职业过活”(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奈选择。不要骂宋江是投降派,正常的环境下有几个人甘愿做盗匪的呢﹖一旦有招安的机会(这也属于“给出路”的政策,尽管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是无论如何要为自己和弟兄们找个合法的归宿的。七十一回之后的失望,是因为过去我们过多地赋予了他们并不能够承担的革命义务和理想。
由于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政府又放弃了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的职责,他们实际上进行的就是一场求生存,并希望过上好日子的经济斗争(当然他们也有政治诉求,例如“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斗争(农民式的)又和近代工人与资本家的合法斗争截然不同,它以刑事犯罪的非法方式,用最原始、最落后的抢掠手段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吃大户、抢富户、劫府库。江湖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无序的社会,加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于一些小股的单打独斗的盗匪来说,他们更多的是伤及众多无辜的老百姓。说到底,它所遵循的仍是市场法则——利益的最大化。“替天行道”也好,“劫富济贫”也罢,只是文化人和一些有头脑的人加入以后所采取的一种争取民心的宣传,一个为自己争取最大生存空间的策略,究竟实践如何是要打问号的。
智取生辰纲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起刑事大案。小说文本提供的这起案例自有它的独特性,它所提供的政治学意义、社会学意义远远超出了刑事犯罪学意义。这从后世的读者们并不以为或者说并未意识到这是犯罪,无不为好汉们劫取不义之财拍手称快也可以看出。这当然是个误区。这固然与我们—直以革命的名义对待梁山聚义有关,更与社会缺失公平与公正,以及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现象有关。长期以来,武侠小说经久不衰,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表明:当公刑不能主持正义时人们便寄希望于私刑;又表明:当“窃国者侯”,“窃钩者”又算得了什么﹖北宋末年出现的盗贼遍地、血腥和暴力层出不穷的局面是令人担忧的;更令人担忧的是从宋徽宗到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国家的“积贫积弱”找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因战争的需要和统治者自身腐化使得许多问题达到了极致:政府冗员之多(英宗时,官吏“十倍于国初”)、升迁之滥为历朝历代之最;土地的兼并历汉、唐而至于宋更加畸形发展;公役之繁重因战争的剧烈,需要甚殷,被史学家称之“宋之公役,最为苦累”。更加的繁征厚敛:财政收入仅以皇祐至熙宁为例,只短短的二十年光景便由每年的三千九百万增至五千零六十万(按:当时的生产力绝对不可能如此发达,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只能是加重人民负担的结果),而支出每年由一千三百万增至五千零六十万(猛增了四倍)。军队的战斗力之弱使得对辽、西夏、契丹、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全国几千万人口供养的一百多万军队成了一种对内需要的力量。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有宋一代,所有的农民暴动全都镇压下去了。而统治中枢呢,依旧纸醉金迷、穷奢极侈、贪污腐败、失政失德……这样的君臣,你要他率先垂范,你要他关注百姓的疾苦也勉为其难了。老实说,他不做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事已算是积德了。 《宋史·食货志》引范镇说,“岁大熟”尚且“民不得终岁之饱”;若一遇灾荒呢,《宋史》引大官僚司马光之言曰:“水旱霜雹蝗蜮间为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上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 还是这部《宋史》,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
民……不得已为盗贼。
“此一事却好”
已是盗贼遍地了。
在智取生辰纲前,已有了占据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占据二龙山的邓龙和占据梁山泊的王伦、杜迁、宋万、朱贵。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本领十分了得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宋以前的匪盗以农村地区无以谋生的人群为主,宋以后城市无以谋生的人群开始加入其间。
此外,还有清风山、桃花山、对影山都是强人草寇出没之处。
关于生辰纲——
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
这情景颇似民初,在“盗风之盛,甲于各省”的河南,“地方扰害既穷,大家相率为匪”〔1〕的态势:其时政局日非,江河日下,各地匪情,愈演愈烈,竟至于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一省之中,无一县没有盗匪,而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
现在我们可以搞懂了,为什么从未与晁盖谋过面的刘唐,能够一见面就直言不讳“送一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与晁盖“只闻其名,不曾会面”的公孙胜同样开门见山:“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专送与保正作见面之礼,未知义士肯纳否﹖” 须知,晁保正不是名声在外的江洋大盗,他是“本县本乡的富户”,是管几百户村民的村官(按宋《保甲法》规定:十家为一保,有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正副都保正)。他在江湖上的名声不过就是“仗义疏财”、“好广结天下好汉”而已,不是谁都可以随随便便同他商量抢国库抢银行的。如果不是到了“大家相率为匪”的地步,刘唐、公孙胜敢这样做、敢这样说么﹖他们相信晁盖一定会干,尽管他是一个“富户”,是一个“保正”。
这从吴用同晁盖保持高度的默契也可见一斑:
吴用问道:“保正,此人是谁﹖”
晁盖道:“江湖上好汉,此人姓刘名唐……因有一套富贵,特来投奔我……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今早正要求请教授商议……此一件事若何﹖”
吴用笑道:“小生见刘兄赶得来蹊跷,也猜了七八分了。”
可以想象,晁盖和吴用平时一定对今上的昏庸、对奸臣的当道、对吏治的腐败、对民间的疾苦发表过不少议论,也一定说过许多“大逆不道”的话。他们都彼此了解对方。因此,说起如此“非同小可的勾当”(吴用语),居然就像请客吃饭,就像做文章那样从容,如同作案累累的惯匪剧盗。
而事实恰恰相反,上述四人包括后来参与作案的阮氏兄弟和白胜全都没有前科,称得上守法或半守法公民。即便是桀骜不驯的阮氏兄弟,除了“打鱼为生”,也不过“在泊子里”干些“私商勾当”而已。
何谓“私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证经营,不过是偷点税漏点税,且本小利微,属于轻微违法。
现在,守法对他们失去了意义。因为守法的成本高,违法的成本却低,甚至不需要成本。就拿梁中书来说,去年搜刮了十万贯,今年又是十万贯,这普天下人尽皆知的贪污受贿所得,朝廷管了吗﹖因此,劫取它并非是没饭吃活不下去了,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的严重不公和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所致。
没饭吃活不下去了是许多人犯法作乱的导火索却不是惟一的导火索,最起码对晁盖和吴用而言是如此。于是,关于劫取生辰纲,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吴用提纲挈领轻轻吐出一句话:
此一事却好!
未来的梁山泊军师一槌定了音。
“正是搔着了我痒处”
学究先生低估了阮氏兄弟的“觉悟”,但你非要把阮氏兄弟列为“有强烈犯罪倾向”的对象也未免对他们不公。
依晁盖的意思,“使人请他们来商议”一下就行了(“请”只是一种谦词,说白了就是“唤”。估计白日鼠白胜就是这样使人唤来就行了,虽然书中没有交代),而吴用却说不可,“着人去请,他如何肯来?”这说明至少在吴用的眼里阮氏兄弟不是轻易就肯干违法犯罪的事的。否则,吴用也不必煞费苦心地“必须自去那里,凭三寸不烂之舌,说他们入伙”了。
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虽然三阮“不通文墨”,毕竟也“两三年不曾相见”了。在这个“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只要敢违法就发财,老实守法就受穷的社会,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彻底改变了。严酷的社会现实改变了阮氏兄弟,因此,当说起梁山泊的王伦们——
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喝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
阮小七又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
纵观梁山泊一百单八排得上座次的头领,真正属于最不稳定因素即只要有诱因就有可能犯罪的算上阮氏兄弟也不过二十余人,仅占两成。问题是如果社会消灭诱因或者说把诱因减少到最少,可能他们就不会犯罪或犯些轻微的罪,这样,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轻一些。如果再积极一些,能够让包括阮氏兄弟在内的全体老百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恐怕就不是什么犯罪不犯罪的问题,而是如何为社会做贡献的问题。招安后他们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鲁迅语),小二、小五战死沙场。可见通过合理的制度性安排结果就完全不同。
问题是诱因太多。
阮小二道:“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因此一言难尽!”
土匪扰民,阮氏兄弟也深受其害。但作为匪患的受害者也盼着落草为寇、去当土匪为害社会,这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究竟在讽刺谁呢﹖请看书:
吴用道:“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
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那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来。”
这又应了一句老话: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在烧杀抢掠欺压百姓方面,兵一点也不亚于匪,有些时候,兵患甚至超过匪患。据《明季北略》载:明末大臣们向崇祯汇报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说“贼”知道百姓恨什么,“贼”对朝廷的“剿匪安民”针锋相对打出“剿兵安民”的旗号,结果百姓望风投降。在这里,老百姓也有个利害算计,如果两者必择其一的话,匪患甚于兵患,老百姓就选择兵;反之,兵患甚于匪患,老百姓就选择匪。所以,“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来”也好。小七说:
我虽打不着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
这岂不就是宋版的“苛政猛于虎”么﹖
诱因还不止这些。接小七“学他们过一日也好”的话茬,吴用故意道:
这等人学他做什么﹖他做的勾当,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白把一身虎威都撇下了。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白做的罪。
阮小二马上反唇相讥:
如今该管的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突,千万犯了弥天大罪的倒没事。我弟兄不能快活,若是有肯带挈我们的,也去了罢!
不消说,阮小二说的“该管的官司”和“犯了弥天大罪的”当然不是指王伦们,否则他又何必“学他们”和“也去了罢”。在持草根立场的阮小二看来,当官的贪污受贿成百万上千万的“没甚分晓”、“倒没事”,老百姓凭什么要傻乎乎地奉公守法受苦受穷﹖酒已经喝了不少,话说到这个程度,可谓水到渠成了。学究先生开始摊牌:
“……如今欲请你们去商议,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处,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不知你们心意如何﹖”
一如灌满了炸药的炸药包,就等着这个火星呢。
小五听了道:“罢、罢!”叫道:“七哥,我和你说甚么来﹖”
阮小七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正是搔着了我痒处。我们几时去﹖”
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阮氏兄弟是决计不按照宋徽宗规定的游戏规则玩了——国家的恩泽惠及不到他们,机会也不给他们,手上没有任何资源,不占有任何信息……总之,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博弈的结果是他们又苦又穷(顺便说一句,官场博弈的结果是清官被淘汰出局)。而按照江湖的游戏规则,凭着他们的“一身本事”,完全能够过上“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所谓风险成本非常高,无非是一条命亦或是自由。要知道,一贫如洗的穷苦老百姓的命和自由不值钱,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成本有多高。即便是当代社会,一些亡命之徒、一些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时,常常会从口中蹦出这样一句话:老子反正这辈子该享受的都享受过了,死了也够本了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宋徽宗游戏规则的最终博弈结果是,国家的顺民越来越少,山中的盗贼越来越多,社会的安全越来越得不到保证。
又要劳师糜饷剿匪了。显然,政府对于犯罪,只有惩罚机制而缺失防范机制。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宋的统治者们不会反躬自问:在动用法律之前,国家是否尽到了责任﹖是否穷尽了一切手段﹖“不义之财”
在智取生辰纲的整个密谋中,本案的当事者多次反复强调这是“不义之财”:
1.刘唐(对晁盖)道:“小弟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而何碍!”
2.晁盖(对吴用)道:“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3.公孙胜……对晁盖说:“这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4.吴用(对阮氏兄弟)道:“……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
不难看出,当事者都在为劫取生辰纲作出道德解释。因为这个解释,使他们处于道德审判者的地位和拥有了道德执行权,从而使他们的行为具备了合理性和正义性(按:貌似至高无上的法律实际上要受到人情、天理,乃至公序良俗的制约。违背天理、人情、公序良俗的法律很难为社会认同,往往也行不通)。也因此刘唐理直气壮地说:“小弟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
而三阮到了晁家庄后——
次日天晓,去后堂里面,列了金钱纸马,摆了夜来煮的猪羊,烧纸……排列香花灯烛面前,个个说誓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大师生辰,此一等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鉴察。”六人都说誓了,烧化钱纸。
上述的“说誓”,简直就是一篇“吊民伐罪”的檄文。民间的秘密结社、叛逆者的犯上作乱、图谋不轨的政治力量政治势力、包括宫廷政变军事政变无不通过上述程序,从理论到形式上确定自己的行为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从而达到否定现行秩序(法律)的目的。
法律,封建社会称王法。所谓王法,用一句市场经济的话来说,就是经营者强加于消费者的不平等霸王条款。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法制国家。虽然封建王朝的法律长达几十卷条款上千条,这种严密的法网并不成其为法治的象征,相反它们是人治的工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曾说过这样一句大话:
便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不过是借他一闹,大家没脸。若告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平息。
琏二奶奶说这些话,不是藐视国家官吏,更不是目无王法,恰恰相反,是她目有王法的表现,因为王法是保护她的。虽然她自己说时无心,其实讽刺了她所依赖的官僚机构,形象地反映了封建官吏的性质及其社会职能。至于封建王朝也会惩处几个贪官污吏,如果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就是你的火玩大了,损害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影响到政权安危。
既然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官吏是如此不可靠,既然法律是针对一般普通民众而不是针对权势者的,民众对是非对错,包括罪与非罪的判断,便取决于道德判断而非政治判断。一旦在道德上作出合理解释(这主要因为统治者不道德,制度和规定的不道德),民众违法(违法不等于犯罪)的事就会大量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逾越法律的界限要比逾越道德的界限容易得多。尽管前者是刚性的、强制性的;后者是软性的、自觉性的。因此,当阮小五听岔了,误解成抢在晁盖前面把他待取的一套富贵半路里拦劫了,便断然拒绝:
这个却使不得。他既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买卖、生意),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时笑话。
再看下面这段对话:
吴用又说道:“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么﹖”
阮小七道:“便捉的他们,那里去请赏,也吃江湖好汉们笑话。”
去劫生辰纲,这杀头掉脑袋的犯罪,小七跳起来说“正是搔着了我痒处”欣然入伙。而同样劫财,因“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却成了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可见道德的力量有多大——虽然只是江湖的“职业道德”。
晁盖们反复强调劫取的是“不义之财”,同后来上梁山树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如出一辙:因为政府角色的缺位,因为公刑不能主持正义,只能由他们来担当审判者和执行者。以“天”的名义就像政治家常常以“人民”的名义,用私刑剥夺其财产,剥夺其自由,乃至剥夺其生命。
“非同小可的勾当”
在商量劫取生辰纲时,吴用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说话是有区别的。
对晁盖和刘唐,他表现出的是一种“羽扇纶巾、谈笑间”胸有成竹的儒雅风度,就像在说一桩寻常事。对三阮,他却语气凝重,一如常人,又如老大哥,明白指出:
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当。
晁盖何许人也﹖人称晁天王。如果不是曾头市中箭身亡,当是梁山的天然领袖,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对于他,难道还要婆婆妈妈地提醒什么“这可是一桩弄不好要杀头的事呀,一定要慎重考虑”云云?真要这样说,倒显出吴用冬烘先生的小家子气,不是做大事的人物。
而三阮则不同。他们“不通文墨”,没有脑袋,全凭意气用事。但他们又是“真有义气”的“好男子”,更何况对学究先生是那样地敬仰和信赖。用小五的话说,就是“那王伦若得似教授这般情分时,我们也去了多时,不到今日。我弟兄三个,便替他死也甘心!”吴用怎么可以藏私、不把事情的性质和利害关系说清楚呢﹖也因此,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
这是真正的肺腑之言。唆使这三个愣头青干这样一件杀头的事,吴用的良心一定受到煎熬。设想如果眼前有一条光明大道可走,他一定会谆谆教导他们走正路。但令人灰心的是合法的途径都被堵死……当然,如果做得机密,计划周到,不出事情,岂不是“一世快活”的目的就达到了,“一世的指望”也就“还了愿心”了﹖吴用确实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
最最重要的是,学究先生虽是“诸葛、陈平”一流人物,但英雄也有常人的一面,也食人间烟火。上述对三阮说的话,又何尝不是对自己说的呢﹖正因为处在不是同一个对话层面上,吴用才无所顾忌地流露了内心真正的隐忧:此一去,恐怕就此走上了不归路。
作为一个文化人,吴用原本应该有很多路可走。可以走科举的路,博取功名;可以到衙门里做个书吏,帮办公文;如果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这些都是想当然。如果处在吴用的位置上,也许你不会说这样的话。
关于吴用是否参加过科举,书中没有提到,但科举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正途,吴用不会置身于外。这从他上了梁山以后不反对朝廷招安这一态度也可以说明。他一定在这方面严重受挫。君是昏君,臣是奸臣,最受信用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以及宦官李彦被时人称为“六贼”。他们相互勾结,排斥异己,广树党羽,贿赂公行,直至公开标价卖官。故民谣“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广为传播。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正直之士受到排挤,人才被埋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那么做个帮办小吏吧。恐怕吴用心有不甘,同时也受不了那个鸟气。明朝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说这位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施耐庵先生的心和吴学究先生的心是相通的,他弃官不做,他笔下的吴用难道会谋个每天见了上司点头哈腰满脸赔笑说些违心话的小吏干干?
至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固然是一种洒脱,但前提必须先要有饭吃。作为一名乡村的民办教师,吴用的日子过得比贫苦农民好不到哪里去。且看第十五回:
至二更时分,吴用起来洗漱罢,吃了些早饭,向晁盖讨了些银两,藏在身边,穿上草鞋……连夜投石碣村来。
“银两”是用来请阮氏兄弟喝酒的酒钱。依吴用的性格人品,如果不是囊中羞涩他不会伸手向晁盖讨。他日子过得很拮据。“穿上草鞋”,不管怎么说还是个教书先生,而且又是出客访友,连最起码的体面也无法维持。如果是一介腐儒倒也认命了,谁叫他是一个腹藏韬略、胸有甲兵、决不是终老“三家村”的人物呢!
经济得不到保障,事业得不到成功,空辜负了他满腹的经纶,一身的本领。怀才不遇是知识分子心中永远的痛。这几乎成为一种宿命。参与抢劫,而且又是主犯,吴用先生不得已采取下下策了。他是把皇帝看透了,把朝廷看透了,兴许,他把所谓的名节也看透了。
文人从贼历来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吴用将从此被钉在了“贼”的耻辱柱上。但对“成则为王”的贼又当别论,正史从来奉行的是两套标准。
纵观吴用先生一生,他的人格人品是没有问题的,能力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政治不是那么黑暗,朝廷不是那么腐败,他是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一点贡献的。耿介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耿介不是一种错,错不在他。落草为寇,是吴用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
“担着血海也似干系”
写到这里,智取生辰纲已接近尾声了。“黄泥岗事发”,逼得晁盖们一不做二不休,“一发”上梁山“入了伙”,索性把事情搞大了。
大家都知道了,通风报信的是宁愿充军流配也不肯上山为贼、及至后来被逼上梁山还念念不忘招安、报效朝廷的郓城县押司,人称孝义黑三郎的宋江。
押司,宋时地方官属吏,办理案牍、官司等事务,所以何涛才会把捕盗公文给他看。
正是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泄露案情,致使案犯全部逃脱。这个中原因岂是一句“江湖义气”和“兄弟交情”可解释。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最不可信的就是“义气”和“交情”。一部江湖志,真正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没见几个,出卖朋友和朝朋友身上捅刀子的倒不少。施耐庵这么写,他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因为在官场上,更无“交情”和“义气”而言。
宋江在郓城县衙供职。
县衙(县政府)是封建王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中央政府通过它来体现政府意志、管理百姓、完成各项任务,它集行政、司法、教育、民政救济、征收赋税、派发徭役等各种权力于一身。它就是缩小了的中央政府,一个封建王朝的缩影。要研究制度腐败,县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封建时代的县衙,除了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等少数在编的拿国家俸禄的官员,其余的属吏和衙役有些仅有一些口粮银(一年才几两银子),大多数连口粮银都没有。这些为数众多(小县几百、大县几千。明末的《虞谐志》中说常熟一县的衙役竟然有上万人之多)的人员,就是靠搜刮盘剥老百姓生活和发家致富。积弊重重,陈陈相因,其搜刮盘剥内幕之黑、机关之巧、方法之多、用心之狠、手段之辣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县府第一把手知县,虽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却有“灭门的知县”恶谥。那点知县俸禄虽不菲但不足以致富。清官海瑞平时自己种菜吃,老母亲做寿才买了几斤肉,在官场上曾引为笑谈。死后大殓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因此,刮起地皮来,第一把手也是一号种子选手,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也。
这样的政府,又遇到灾荒,你要老百姓不为寇为盗也难。
作为一个老练的属吏,宋江洞察其中—切。他肯定对“乱自上作”(金圣叹语)和“官逼民反”有更深切的感受:政府官员未必比盗贼更道德,贪官口袋里的银子未必比盗贼口袋里的银子更干净。而官员又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他们全都打得一手漂亮的擦边球,即便豁边打成界外球也不要紧,无非是重新分赃,把多捞的拿出来上下打点好就没事了。他实在不忍心看晁盖“性命”就此“休矣”。于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出于良知,通知他赶快逃走。就是为了这件事,又犯下了人命案,守法公民注定是做不成了,从此成了“贼配军”。
最后要提一提的是后周世宗后裔、大财主柴进。他的心更是向贼没商量。王伦、杜迁、林冲、武松等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和庇护。宋江亡命他庄上避难,这位过着“体面生活”的柴大官人说出的话更无法无天:
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官府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是出于政治目的﹖书中看不出,也看不出此人有什么大志。虽说赵家的江山是从他柴家手中夺过去的,他人还在但心未必不死。因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以后,宋朝对于降服的各国君臣都予以优待,使之不发生复仇的举动,而对后周及其子孙更加优厚。施耐庵写《水浒传》已是元末明初,既然“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李逵语)这样的碍语都可以写,如果柴进有政治目的,他没有必要掩掩盖盖。那么是出于经济目的﹖恰恰相反,凡是流配沧州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来,我自资助他”。他有的是钱。世受皇恩的柴进都这样同朝廷离心离德,饱尝朝廷寡恩薄义的人民就更没有这个义务同朝廷同心同德了,最终唾弃它就一点不意外了。
平心而论,赵宋政权还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政权,它施行的也不是暴政。如果是,轮不到金人灭亡它,人民就将它推翻了。但北宋末年出现的盗贼遍地和人心向贼决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它表明除了在根本制度上,赵宋政权在许多环节上都出了问题。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着各种危及政权根基的矛盾。在内患大于外患的基本判断下,决策层主动以降低效率和对外忍辱求和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若干年后,战斗力急剧衰退的赵宋在与辽、西夏、契丹和金的对抗中惨败。公元1127年,金兵渡过黄河,俘获了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文武大臣、嫔妃宫女三千多人和各种财物北上。北宋灭亡。时值靖康二年,史称“靖康之难”。北上途中,颠沛流离之际,赵佶这位误为人主的当年的风流天子、眼下的亡国之君仍不失词人本色,做了一首《燕山亭》:
北行道上见杏花 裁翦冰销,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它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哪里是在写杏花,分明就是北宋王朝的一阙挽歌。
南渡以后,时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盗匪问题便不突出。但每隔一段时期,这种周期性的盗匪问题就会重新突出。这往往都是纲纪与道义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是体制无法保证公正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实现的时候。当然,任何朝代、任何政治制度下,包括太平盛世也会有盗匪,也会发生刑事案件,但这并不是“问题”。一旦成为“问题”,为政临民者是难辞其咎的。
注释:
〔1〕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69页。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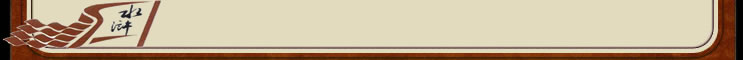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