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十三章 进京(二)
|
 |
|
片刻那丫头回来,将柳、燕二人带到一处高大的房门前,低声道:“姐姐,客人到了。”屋内一个慵懒的声音道:“请进来吧!”丫头推开门,让柳、燕二人进入,又将门轻轻带上。
柳絮儿四处看去,房间却比以前大上许多,白纱幔帐,淡黄窗帘,金睛兽烟气袅袅,整座屋内纤尘不染、华而不奢,恬淡幽雅。一个苗条女子背对门、侧卧在床上,手中一柄紫纱小扇,无力的上下晃动,淡淡道:“哪里来的举子,即过得了琴棋书画之关,非是常人,当应刻意功名,却来这等烟花场所,不怕辱没祖宗清誉。”燕青开口赞道:“竟是‘碧水’,果真清香怡人。”李师师翻身坐起道:“果然有些道行,连高丽国进贡的‘碧水’香也知晓,却是那里人氏?”话音未落,柳絮儿看清李师师相貌,双目泪花闪动,已扑上来。李师师大吃一惊,以为这书生骤然见到自己貌美,情难自禁,急靠向床里,怒斥道:“客人休的无礼,这里是京城重地,非是蛮夷之邦,只怕官府捉了你去。”
柳絮儿泪水已潺潺流下,将一张沾满脂粉的脸弄得一塌糊涂。李师师脸现厌恶之情,正欲喝斥,柳絮儿已瞧见屋角有一铜盆,盛满清水,顾不得解释,急忙走过去,掬水洗将起来。李师师更感惊诧,一时不知如何对付,柳絮儿已洗净,用一方洁白的手巾擦拭干,回头看向李师师。
李师师瞬时双目圆睁,嘴张开却无力发声,看着柳絮儿清秀娇美的容颜,颤声道:“竟然是絮儿妹妹么,可不是在梦中罢?”柳絮儿已扑倒在李师师怀中,二女哭将起来。
燕青识趣退到屋外,一个丫头端着茶水上来,燕青接过,随手放一锭大银在丫头手中,低声道:“央烦姐姐在楼梯口守候则个,若有人来可咳声为号,拜托、拜托。”丫鬟惊喜得银而去。
二女在房内喁喁叙旧,不时又哭上一番,李师师擦泪道:“闻听妹子被掠上梁山,姐姐十分担心,天天托佛主保佑妹子平安,那帮凶神恶煞,岂不狠过嫖客十倍,想不到妹子竟然还这般秀丽绝伦。”看向房门外,神神秘秘道:“这后生该不是妹夫吧,却来京师求取功名么?”柳絮儿脸色一红道:“姐姐不可胡说,此人不过是我家相公手下的一名头领罢了。”李师师叹口气道:“有仆如此,妹妹的相公当非凡人了。”柳絮儿怪异的笑笑道:“我来时听李妈妈说怎么这里还有柳絮儿和秦如烟?”李师师鄙夷道:“不过是两个卖身的罢了,李妈妈为了多赚钱,便不惜用你二人的名号,当真可恶的很。”柳絮儿道:“当初若非李妈妈日夜督促我练琴,柳絮儿或许真的卖身了。”李师师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此时燕青敲门后,端茶进来,李师师注目下,叹道:“草寇中也有如此人物,当真是奇了。”柳絮儿面有得色道:“我二人已结为姐弟,小乙过来见过师师。”燕青放下茶具,施礼道:“小乙见过李姑娘。”李师师闻听二人结为金兰,不由大眼圆睁,上下仔细打量,燕青羞赧起来,这李师师毕竟坊间出身,毫无顾忌。柳絮儿急道:“姐姐不可以这样欺负人家。”李师师笑道:“闻听梁山草寇将高俅的禁军杀的落花流水,却见不得一个女子,怪哉。你却如何知晓‘碧水’香的?”燕青道:“小乙也是冒昧揣测,以前在柴大官人家中闻过,端的有如麝香袭人,却又香而不腻,有飘飘醉倒之念,难得李姑娘房中雅致如此,更添世外桃源之意,不由得小乙夸赞起来,惊扰李姑娘尚请恕罪。”李师师吃吃笑道:“若非妹子介绍,此人同那些纨绔子弟倒也难分彼此?”柳絮儿正色道:“姐姐此言差已!小乙非但武艺高强,更兼琴棋书画皆有专长,方才你那棋局,就是小乙破的”
燕青急忙抱拳道:“适才多有得罪。”将经过说了一遍,李师师倒并不见怪,道:“以后要小心了,免得被浮华浪子钻了空子。”
燕青脸色一红。柳絮儿道:“姐姐不要讥讽,小乙的技法高超,妹妹有时也自叹弗如,岂是纨绔子弟能比?”
李师师一脸疑惑的看着燕青,柳絮儿怂恿道:“小乙便来弹上一曲,给师师姐品评品评。”燕青躬身推辞道:“小乙怎敢鲁班门前弄斧,久慕李姑娘的琴音妙律,今日若能有幸听上一曲,虽死无憾亦!”李师师高兴道:“好罢,就来弹一曲,总不能让小乙兄弟的银两白花。”柳絮儿摆好琴椅,李师师慢慢坐上去,十指如笋,在琴弦上飞跃起来,一曲仙音如幽谷鸣翠,空涧流水渲泄开来。
一曲弹罢,已是额头见汗,李师师虽然不认可柳絮儿所说,但亦分外卖力,加之姐妹重逢,喜悦难禁,自认为是弹奏最好一次。
柳絮儿递过手帕,李师师接过慢慢擦拭,看着燕青犹自沉湎于琴乐中,不由抿嘴笑道:“小乙兄弟可来品评一番。”燕青躬身道:“李姑娘果真是技艺非凡,能将指法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的人物,天下无二。”李师师微笑道:“你叫我师师就可,絮儿即呼你为弟,也便是我弟弟,大家却不必拘礼。”燕青道:“小乙怎敢!”李师师怒道:“师师最恨繁文缛节之人,叫你叫师师,你便叫!”柳絮儿‘扑哧’笑道:“怎的这般大声,当是你相公,只怕日后无人敢娶你。”此话说完,便知不妙,三人立现尴尬之中,柳絮儿急道:“小乙只云师师指法超群,岂是顾左右而言他,这‘空谷幽兰’弹的可比我强多了。”燕青迟疑了一下,偷看了一眼李师师,李师师眉目庄严,也正等着燕青说话。
燕青正色道:“李姑娘既然最恨虚伪小人,小乙就胡乱说些,望李姑娘莫怪。”这‘师师’二字中终是说不出口。李师师嘴角微微噙噙,想看这粉面小生有何说法。
燕青续道“李姑娘于琴技一道可谓熟亦!便如练武之人,习练射箭,已是百发百中,只是随便张弓搭箭,也是命中目标,如此一来,神情不免懒惰下来,再练射箭,虽然同样射中目标,但已无先前的激情和真诚,只是一种卖弄和应付。声乐一道亦如此,每次操演,需要全身心投入,心、神、情三者具备,如此一来,纵使指法稍有欠缺,但在用心人听来,也不免心神激荡,神思游移于物外,陶醉于真诚之中。李姑娘可能身处污龊之处,每日所见大多是无聊贪色之人,听琴不过是附庸风雅,其意不在此,绝无伯牙与子期之念,久而久之,李姑娘不免心疏意懒,纯是指上技巧,全无心灵之音。”
柳絮儿又羞又急,怒道:“小乙怎可如此胡说八道!还不快向师师姐姐赔罪……”
回头欲向李师师解释,早见李师师大颗泪珠滴下,柳絮儿更是慌神道:“小乙不懂事,姐姐不要往心里去!”李师师已是哽咽起来,抽泣道:“师师心中的愁苦,今日竟然被小乙兄弟一口道出,师师感激不尽。”起身拭净泪水,向燕青施礼道:“十年未逢君、逢君是知己,请受我一拜。”燕青脸色通红,局促不已,不知是扶还是不扶李师师,急忙道:“小乙亦受李姑娘真诚所动,才敢信口胡说,请李姑娘恕罪。”二人竟有惺惺相惜之意。柳絮儿在一旁大是惊讶。
李师师叹道:“很多人看着师师风光无限,谁知其中真滋味?便是周大人偶尔来听师师抚琴,琴罢摇头云‘失神久已,去真趣伪,岂是乐道?’原来同小乙竟是一般口吻,奇怪哉!朝中大臣同人称草寇的梁山豪杰竟有同样想法,可真是奇了!”
柳絮儿道:“琴乐一道,同参禅悟道相差不远,到了最高境界,不论是皇上还是乞丐,恐怕都有同一般想法。”
李师师赞道:“连妹妹都有如此进境,看来我也要同你们一同去梁山呢!”三人都笑起来。李师师凤眼瞄上燕青道:“小乙兄弟可否让姐姐也能聆听绝技?”燕青不好再推却,在盆中洗净了手,上前弹了首‘关山月’,此乃汉朝传下的曲谱,大开大合,气势逼人,原本是描述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之事,琴声中偶尔重音,似是金戈铁马、气势恢宏,听来使人神情震荡,志向高远。
曲罢,李师师悠然道:“果然技如其人,非豪放之人,原弹不出这等境界。不过在过宫二片处,这食中二指间弹过快,显得过于急促,而尾后又有些含糊不清。”俯身在燕青身旁,指点缺陷,几屡秀丝在燕青脖颈刮来刮去,阵阵脂粉的香气传入鼻孔,燕青一时大窘,手指也僵硬起来,李师师终知有异,叹口气道:“小乙方才语气何等凛直,并无男女之防,此时因何又心猿意马,现在只是技艺切磋,小乙兄弟以为如何?”燕青在一旁大是惭愧,收摄心神,二人仔细讨教起来,不时还争辩几句,连柳絮儿在旁亦觉成为多余之人。
燕青依照指点重又弹了一曲,曲中李师师吁口气道:“小乙方才身处局外,说来头头是道,如今轮到自己亦难把握,汝为人太过拘禁,似常以奴仆自居一般。”燕青心内黯然,脸色显得有些尴尬,李师师自顾自说道:“这豪气说来容易,要做起来,除非是看开大是大非之人,绝难做到。唐朝李太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何等万丈豪情!源于大唐武功威震四方,四夷宾服;本朝虽有坡公豪气,但终参杂一丝无奈,源于朝内不宁,外辱不断。”柳、燕二人听得目瞪口呆,眼中全是敬佩之色。
李师师不好意思的笑道:“这都是听周大人说来的,我哪有这等见识!小乙不妨放开胸怀,凝神静气再弹一曲‘关山月’来听听。”
燕青此番弹来,果真不同凡响,不但曲调连贯,豪气更胜一筹,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琴弦犹如战场,千军万马在燕青的手指间冲撞、厮杀;又如沧海怒潮,无数波涛,层层涌上,激起无数浪花后,又悄无声息的退下。燕青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渐渐做到人曲合一的境界,于外界万物充耳不闻,及嘎然而止,柳、李二人犹感意犹未尽,沉浸在其中。
房门突然被推开,一个儒雅的长者高声道:“好一曲‘关山月’,师师竟能达此境界,难得,难得!”及看清是个俊俏的后生坐在琴边,惊讶不已,等到看清柳絮儿相貌后,更是吃惊不小。柳絮儿跪拜下去,怯生生道:“周大人安好,絮儿拜见。”一个小丫环出现在门边,手中抚着喉部,一脸惶然的望着燕青,显是连番咳嗽下,竟然无人听见。方才莫说是咳嗽,就算是外面打的天翻地覆,屋内人也是充耳不闻。
周邦彦敏捷的掩上门,疑惑的上下打量燕青,燕青上前跪倒道:“小人燕青,参见周大人。”周邦彦道:“这位小哥不但人长得俊俏,难得有一手好琴艺,是絮儿的相公罢?”柳絮儿羞红脸正想解释,李师师开口道:“周大人同我一般猜错了,此人只不过是絮儿相公手下的一名头领而已。”
周邦彦诧异道:“絮儿不是被掠上梁山吗,缘何出现在这里?”柳絮儿再拜道:“絮儿就是奉相公之命,前来求见周大人,可巧在这里碰到。”周邦彦疑惑道:“你家相公究竟是何人?”燕青上前参拜接道:“敝头领梁山之主宋公明遣小人和夫人前来求见周大人,听说大人清正廉明,非是奸佞之辈,这里有封宋头领亲笔信,盼大人能够转交皇上,还望大人在皇上面前分辨我主替天行道、忠君爱国之意,勿受奸人拨弄,早下旨诏安,实为万民之福。”
周邦彦尚在犹豫,柳絮儿哭道:“望周大人成全,我家相公绝非大奸大恶之徒。”周邦彦点头道:“且将书信拿来我看。”燕青撕开贴身小衣,取出一封信递与周邦彦。
周邦彦展开读道:“罪臣宋江拜上,吾皇万岁,罪臣等诸兄弟虽草莽出身,现落草为寇,实非本心。皇上神明,下臣无道,欺罔圣上,以塞视听,罪民大都忠良之后,迫于无奈,占山据寨;纵如此,罪臣等无不以忠君爱国为己念,替天行道为己任,更不敢滋扰州府、欺压良善,皇上圣明之君,必能体察罪臣一片忠心,切盼及早下旨招安,实为苍生之幸,宋江再叩首,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邦彦感慨道:“语虽粗鄙,难掩一片赤胆忠心,周某一定启奏陛下,不负絮儿所托。”
门忽地被推开,守候的丫环满面惊恐之色道:“赵、赵大官人到了!”李师师脸色霎时剧变,颤声道:“是、是皇上来啦!”燕青喜道:“何妨就此向皇上辩白。”周邦彦一边寻找出路,一边喝斥道:“胡闹!皇上来此,怎能让外人知晓,况且也须找寻一个好机会向皇帝奏明此事。大家快躲起来,迟了恐有杀头之祸!”柳、李二人闻听更是惊恐万状,燕青推开窗子,朝下望一眼,到声‘得罪’,抱起柳絮儿一跃而下,悄然落地。
柳絮儿脸色羞红挣脱燕青怀抱退在一旁,楼上周邦彦急得轻声喊道:“喂!我却如何是好?”燕青道:“大人不妨也跳下来,我在这里接着。”周邦彦见燕青身材矮小,自己壮硕肥大的身子他如何抱的住!摔坏可不是耍的,犹豫片刻,楼梯脚步声响起,一个和颜悦色的声音道:“师师姑娘睡下了么?赵大来此。”周邦彦脑中‘嗡’的一响,可不正是皇帝的声音,立时双腿酸软,想要跨上窗棂,却哪里动得了。李师师强自镇静道:“师师换过衣服,马上就来。”伸手一指床下,周邦彦无奈只得钻入。
李师师见周邦彦藏好,又简单收拾一下,忙去开门。赵喆笑眯眯跨进屋来,二个侍从在门外守候。赵喆看了一下四周道:“这房里不会藏别的人罢?”床下周邦彦大惊失色,李师师心也狂跳起来,却故作嗔怒道:“官人把俺师师当什么人了,不信可以派人来搜搜。”李师师知道赵喆顾忌身份怎会亲搜,故而涉险激他一下。赵喆笑笑道:“李总管先要派人来查检一番,我怕坏了师师情趣,‘美人一怒、千金难顾’,就叫他们在楼下守候。”原本赵喆每次来此,必先派人前来知会,又有宫中好手前来搜寻一番。
师师听如此说,一颗心才放下,心里奇怪:“皇上一向是月初来此,如今却大违常理月中即来,是何道理?”
赵喆虽有后宫佳丽三千,比李师师貌美之人也不在少数,徽宗并非好色之人,来此不过是寻求才子佳人的感觉而已,后宫六院哪一个见了他或循规蹈矩、或战战兢兢、或有所求,皇后又过于正派,每每以国家大事相劝,偏偏徽宗对国家大事不屑一顾,对棋琴书画之道甚是偏好。
这李师师活泼可爱,全无机心。徽宗偶尔在坊间行走,听的师师才高貌美,赵喆以客商身份,三次才见的师师。李师师见赵大官人出手阔绰,又才气横溢,书法飘逸,画风峥嵘,李师师大是佩服。不料后来鸨儿从李总管口中得知赵大官人是当今皇上,吓得半死,为防止李师师过于娇纵,惹来祸事,就透露给李师师。
徽宗再来访,见李师师花容失色,低眉顺目,心知有异,询问之下,知道缘由,大为愤怒。在李师师求情下,才放过鸨儿和李总管。
事罢赵喆叹道:“朕本想过几日寻常人的日子,却也不成。”言下甚是萧索,李师师大胆道:“我便当陛下还是行商的赵大官人,若有冒犯之处,还请陛下不要责怪!”赵喆大喜道:“如此甚好,朕饶你一切罪过,你尽可放心就是。”李师师乘机道:“空口无凭,官人需要留下凭证。”赵喆正在兴奋头上,立时挥毫写下一纸手谕,李师师笑容满面的藏了。
今日赵喆匆匆来到,叫众人措手不及。李师师见皇上面上甚喜,动问道:“官人这般高兴,可有什么喜事?”赵喆笑笑坐下来,将个精致的果匣放在桌上,有人敲门将一壶上好的茶送进来,李师师接过给赵喆倒上,坐下静静地听。
赵喆轻啜口茶,淡淡笑道:“却也不是什么喜事,福建知州进贡许多龙岩脐橙,我想起你曾说过爱吃此物,便挑了几个大的给你送来。”李师师感动道:“陛……官人大恩,师师铭记在心,永世不忘。”赵喆掀开盖子,一种清香扑到,李师师取出一个放在鼻下,贪婪的嗅着“好清新的橙子,这般圆润晶莹,好似圣物一般,却怎舍得吃哩!”
赵喆喜滋滋的看着李师师惊奇的表情:“师师但吃无妨,宫中还有,明日派人再送些来。”李师师伸手欲撕开橙皮,赵喆急摆手道:“切莫如此,此橙乃新摘下,快马送到,皮虽薄,却极难撕扯,弄得到处汁水淋漓,好不狼狈,须以刀剖开,分瓣而食。”李师师如何不知,不过怎敢在皇上面前弄刀具,要知刀具在皇上面前皆为凶器,愁道:“却那里寻刀来?”
赵喆伸手入怀,取出一紫色小盒,翻开盒盖,一柄二寸长小刀卧在其中,白洁光亮,煞是可爱,李师师惊呼一声,拿起此物,赵喆急缩手道“莫急!此物锋利异常,要小心些!”李师师小心翻看着,赞道:“好精巧的玩意,却是那里寻来?”赵喆道:“此乃福建知府一并送来,却是并州铁匠选精铁打造而成,专为破橙而用,名曰‘刈橙指’。瞧来和人手指长短相仿,并州原产好铁,此物锋利更甚,师师可破橙一试?”
李师师将‘刈橙指’放在橙上,竟悄没声息没入,似被橙吸入一般。师师轻轻旋动,两个半橙立时分开,在桌上轻轻晃动,举刃一看,难得锋面上无一滴橙汁。李师师赞叹声中,将圆橙分做八瓣,动作轻柔,橙瓣在桌上轻轻摆动,很凛冽的清香传来。
李师师甜美的深吸一口,面呈陶醉之色,末了取过一瓣正要放入口中。
赵喆忙道:“且慢。”又从盒内拿出一折叠的纸袋,慢慢掀开,一小撮晶莹透亮的物什呈现在李师师眼前,李师师喜道:“是白糖么?我原喜欢橙酸味。”赵喆不语,捏起一点放入茶杯中,用清水冲开摇均,将两瓣鲜橙放入其中,才满意的笑道:“那里是白糖,这是吴地的海盐,那里的匠工有很高明的处置方法,研磨出来的盐细如珠粉,洁白如雪,故又称为雪盐。这新橙味过酸,一般人绝难承受,盐水渍后味道更佳。”说罢,伸出白净的手指取出一瓣浸过的橙递给李师师,李师师将信将疑的放入口中,初时酸中带微苦,咬动下,渐渐的舌根生出甘甜的味道,很快传遍满口,李师师喜道:“果真奇怪。”又取过一瓣贪婪的吃将起来。
赵喆在旁专注的看着,欣赏道:“果真是一幅‘美女破橙图’。”赵喆的艺术灵感极佳,立时命人拿来笔墨、宣纸,挥毫画将起来。师师也甚是乖巧,静静的坐在桌边吃着橙。
不过片刻,一个鲜灵活现的少女跃然纸上,那种神情专注的吃着蜜橙,又有些慵懒、放任的表情无不栩栩如生地体现在赵喆的画中。画毕,赵喆满意的放下笔,微笑着看着自己的作品——一种非常成功自负的表情。
李师师亦站起,来到画前,忽然怔住了,有些激动,眼中闪着泪花。赵喆的画中少女,有种不可名状的情愫表现得惟妙惟肖,喜悦、羞涩、惊异、紧张,还有种担惊害怕的神情。唯有面貌却不是很相像,赵喆只是要表现出一个真实的少女,一个鲜活的少女陶醉于爱物中的真实表情。赵喆画技高超,人物表情拿捏得很准:画中人手指微张,既想抓紧橙子,又怕刀锋伤手的紧张动作亦能通过指间墨迹的薄重细致入微的体现出来。这种技巧绝非一朝一夕练就,乃是天生而成。
赵喆亦有些兴奋得看着一旁的李师师道:“宫中怎能有如此率真之人?”李师师奇怪道:“官人此话我可真是不懂了?”复又叹道:“我不知官人是做皇上好,还是做画师更好一些?”赵喆闻言一怔,思索半响,摇摇头不得其解,慢慢踱步到窗前,此时是子夜时分,但见长空万里,银汉迢迢,无数繁星布满夜空,赵喆低头看向京城,已是夜深人静,偶尔传来更漏声,街边的雾气渐渐升起,附近的楼台亭肆渐渐淹没其中,忽隐忽现。
赵喆望着夜空悠悠,身旁美人在侧,忽然想起苏东坡的‘洞仙歌’,不禁开口吟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汗。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到流年,暗中偷换’。”李师师听的如醉如痴,呆呆的看着赵喆,心道:这样的人就是皇上,怎么同那些书香门第的举子相差不大。
赵喆吟罢,望着呆呆看着自己的李师师,似乎有相同的感受,幽幽道:“我有时真想做个凡人,也比这皇上好上几倍。”李师师吓了一跳,从痴呆中醒来,看皇上有一丝颤抖,急忙拿件披风给赵喆披上,关切的问道:“这家国大事总让官人心烦罢!”忽然想起柳、燕二人,心中思忖道:“要不要先给皇上解释一番。”赵喆回头看着李师师笑道:“来这里我便是赵大官人,那管什么家国大事?”深情地看着李师师道:“夜已深,我就宿在这里了。”李师师脸一红,忽然想起床下的周邦彦,更是忸怩,却又怎能拒绝!赵喆看到李师师娇羞不胜的容颜,一颗心也温暖起来。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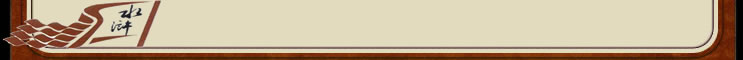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