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十四章 饕餮(二)
|
 |
|
阿绣喊了良久,未见回音,轻轻推开门,见疯老者和衣倒在床上,阿绣挥着鼻息上前,叹道:“我还当药效不错,谁知还是如此!”勉力替疯老者脱下外衣,已是气喘吁吁,加之气味难闻,及换到小衣时,有些犹豫,终究是未出嫁的姑娘,又非亲人,前几日是央求乔三找人替换衣物。阿绣人温柔和气,又会医些小病小恙,很有人缘,不少喽罗乐此不疲,不料今日来的早些,还无人前来奉承。
阿绣走到屋外,大口吸着微带潮露的新鲜空气,暗道:“这般难闻,需要尽快换下,免得老爷爷生病。”阿绣却不知疯老者本是仵作出身,专替官府验尸查迹,这种尸味对他实属平常。
一阵狗吠声传来,阿绣循声望去,雾气中,一人持枪在练功。阿绣惊喜得跑过去,见是一个同她年纪相仿的少年在练枪,这枪又粗又长,正是林冲的‘飞虎枪’,几个套路下来,少年不免额头见汗,身旁一条黑毛犬冲阿绣低吠两声。少年收住枪,用腰间手巾擦汗,望着阿绣。
阿绣好奇的看着少年手中的枪,惊奇的吐舌道:“好厉害,这枪快有你三个长了,竟使得这般好。”其实阿绣根本不知道枪法好坏,不过为想拉着少年替疯老者换衣才是紧要问题,又找不出太合适的话语搭讪,只好先奉承一番。少年闻听嘴一撇道:“小毛丫头懂得什么枪法?”显然是对枪比身长三倍耿耿,故而还击。
阿绣歉然道:“我不会说话,小头领莫见怪。”少年听的‘小头领’三字‘噗嗤’笑了起来,“不要乱说,我哪是什么小头领,我姓杨,名再兴,你叫什么名字?”阿绣恍然大悟般,“那日听姜姐姐说打败两个头领的小孩,就是你么,我那日上山采药去了,没有看到,想来……。”一时不知如何夸赞。忽然吐舌道:“对不起,这小孩是姜姐姐说的,可不是我,我叫阿绣。” 杨再兴笑笑,不再理论,持枪转身要走。
阿绣急道:“先别忙走,可否帮个忙?”杨再兴无奈回身,抱着长枪道:“鲁伯伯说了,女人最是难缠,遇上总有闲事。”阿绣只是微笑道:“对不住,一桩小事,一会就好。”杨再兴见对方笑意盈盈,毫不着恼,随口答道:“好吧,我先将师父的枪送回去。” 毕竟是少年心性,也不问是什么问题。
二人来到疯老者的居处,黑犬已开始不安,冲屋内哀哀的吠叫起来,杨再兴疑惑的看着阿绣道:“你屋内不是藏着个大虫吧?”阿绣不好意思道:“屋内是个疯老人,今早不知跑去那里才回来,身上味道很难闻,外衣我已换掉了,央烦你把内衣换了,实在是对不起之至。”见杨再兴满脸不信的样子,只好将收留疯老者经过叙述一遍。
杨再兴见阿绣如此良善,一时大为感动,阿绣告诉杨再兴新衣位置,杨再兴正要进去,黑犬一头扑上,咬住主人裤脚,阿绣见状蹲下赞道:“好个忠义犬。”轻轻抚摸着黑狗顶门,柔声劝道:“不要紧的,只是换件衣服。”那黑犬只是不松口,口中吐出含混的低呜,两只耳朵也立起来,显然对阿绣不很友好,若不是就一张嘴咬着主人,只怕要对阿绣下口了。
杨再兴道:“黑子别闹,一会就出来,我们上北林抓山鸡。”黑犬勉强松口,伏在地上,双目紧紧盯在屋内。
杨再兴进屋内大声喊道:“哇,臭死了!”不一会急速冲了出来,大口喘气道:“什么味道,比茅厕还要臭。”换下的内衣扔向一旁,阿绣急道:“别扔,好好浆洗一番,在日头下多晒晒就没事了。”急忙过去拾起,黑影一闪,那狗儿蹿了出去,一口咬住,阿绣急拉,同时央求道:“好黑子,放口吧,回头我找骆姐姐给你多打几只山鸡。”黑子死死咬着,双目挑衅似的看着阿绣,杨再兴高兴的看着,口中道:“怨不得爹爹给我取名再兴,确实大有道理。”阿绣见杨再兴不但不帮忙,反而幸灾乐祸,急道:“你不是高兴的兴,是幸灾乐祸的幸。”杨再兴还是笑道:“也是伶牙利齿的吗,干么总做出一幅柔弱的样子。”阿绣眼中泪水都快流出,大力撕扯,‘哧’的衣服撕裂,一物掉落,滴溜溜滚向一旁,阿绣摔倒又羞又怒,不由低低的哭出,黑子也松开衣物,跑到掉落物近前,嗅嗅又用前爪拨了拨,想用口刁起,闻闻又躲开,又复冲了上来,杨再兴正在有些后悔,发现黑子的举动,上前拾起一看,是一颗亮亮的珠子,正想还给阿绣,黑子朝西侧吠叫,杨再兴回头望去,扈三娘快步走来,见到阿绣蹲在一旁似乎在哭泣,生气道:“真是有什么样的师父,就教出什么样的徒弟。”杨再兴见挖苦到林冲,不乐道:“此事因我而起,我自会处理,却扯不上师父。”走到阿绣身前,高声道:“对不起阿绣姑娘,这是疯老人掉落的珠子,你去还给她吧。”
阿绣木然接过珠子,脸色红赧道:“扈姐姐,你错怪他了,他是来帮我忙的,我只是不小心摔了跤。”杨再兴见阿绣如此善解人意,高兴道:“下次有事还来找我。”阿绣也破涕为笑道:“可不许带黑子。”黑子似乎听懂,朝阿绣怒目相视,杨再兴对扈三娘施礼道:“别过扈头领。” 转身道:“黑子,我们去捉山鸡喽。”一人一犬快步跑开。
扈三娘问明了经过,来到屋内,见疯老者犹自昏昏沉睡,道:“这味道同腐尸气味很像,难道此人有梦游症不成?”阿绣在旁点点头道:“爷爷曾说患失心疯后行为匪夷所思,有夜游症也不足为奇。”举起珠子翻看着,喃喃道:“这件衣服是我找姜姐姐缝制的,会不会是姜姐姐遗落在里的。”
扈三娘沉思片刻道:“或许是疯老人自己藏进去的。”阿绣道:“不会吧,这样的人会藏东西。”又在撕扯开的小衣中检查着,终于发现有半截玉簪。阿绣点头道:“这是连在一起的,刚才撕扯断了。”说罢开始穿线将珍珠串上。
扈三娘点头道:“用酒泡一泡,把怪味去掉,再去问问是不是你姜姐姐掉的。”
不料姜若群接过半截玉簪一看,几乎昏倒,连声追问阿绣那里寻来的,阿绣说了经过,二人又急急来到疯老者的屋内,虽然疯老者已醒,不过对姜若群的苦苦哀求毫不理会,一会嘻嘻傻笑,一会怒喝连连,根本不明所以,姜若群无奈含泪回到女寨。
扈三娘看见姜若群伤心的回到寨中,急忙上前询问。姜若群断续道:“家中祖传一珍珠翡翠碧玉簪,母亲临终时交给哥哥保管。”脸上忽然飞起一抹红霞,有些扭捏道:“作我出嫁时用。”又伤悲道:“哥哥出征时,将此物交于我,言道此战吉凶未定,我含泪央求哥哥收回此物,因祖传宝物珍贵,必能佑人逢凶化吉。不料哥哥一去三年,至今毫无音信,这珠子就是碧玉簪上所属,竟神奇般出现在此,岂不太过奇怪。林头领不是说派人前去寻找我兄长的下落吗,今日天意竟让我看到珠儿,或许我兄妹真有合物为一、劫后团圆的那天。”不由喜极而泣。扈三娘想起那日林冲面见姜若群焦虑的神情,或许其中另有隐情,急忙告辞来到林冲大寨。
林冲听罢事情经过,吃惊不小,感激道:“多谢扈头领真言相告,林某感激不尽。”扈三娘见身旁更无旁人,乔三在院外练拳,看似神情专注,其实左顾右盼,探看是否有外人来此。
扈三娘一颗心酸酸的道:“林、林头领。”险些喊出林大哥,不过话到嘴边,生生咽下。续道:“我看林头领有重大内情瞒着,莫不是以为女流之辈但不起重任么?”林冲闻言一愣,感慨道:“扈头领女中豪杰,行事光明磊落,林某自愧也常常不如。”扈三娘脸现红晕,见意中人如此夸赞,又想起雁台私寄书信一事,以为林冲讥讽自己不敢当面言明情意,心头更是鹿撞,林冲怎会想到扈三娘心中所想,自顾自说道:“此事确有别情,暂时林某摸不清深浅,怎敢拖扈头领下水。” 此时扈三娘脑中全是旖旎之念,听到拖…下水之句,更是羞不可言,林冲注意到扈三娘神情有变,不觉讶异的望着扈三娘,不知哪里说错了话。扈三娘骤然发现林冲不再言语,抬头望去,见林冲也怔怔的望着自己,一时情难自禁,闭上凤目,身躯缓缓向林冲倒去。林冲吃了一惊,急忙双手扶住扈三娘双肩,低声道:“扈头领、扈头领,你不碍事吧?”传来乔三的声音道:“王头领好清闲,且请屋内坐坐。”王英爽朗的笑声响起:“我方才听人说三娘向这边过来,我顺道来瞧瞧。”扈三娘浑身剧震,脸色煞白,双目睁开,身体站直,僵硬的走向屋外。王英见扈三娘果然从林冲房内走出,心内泛起一阵醋意,仔细打量扈三娘衣装、发饰。林冲也尴尬的走出道:“王头领到了,且请屋内用茶。”王英肚内将林冲祖宗十八代全骂遍,可武功不及林冲,威望资历更是远远不足,大部分还是靠老婆是宋太公的干女儿得来的面子,才得到众人尊重。扈三娘对他一直很冷,特别是经历一事后,扈三娘看王英形同陌路,几乎不许王英碰一下,这王英本是好色之徒,守着美人却形同虚设,怎不心急如火。
王英强咽下心中的不满,满脸堆笑的看着扈三娘道:“宋夫人下山省亲去了,太公十分想念,大哥命我寻你安慰干爹,我到过女寨,听小鱼说你向这边来了。”
林冲吃惊道:“宋夫人下山了,怎么我竟不知。”王英讥讽道:“宋夫人下山,关你何事,宋寨主好像不用亲自来告诉无干之人吧!”说罢冷笑不止:这个林冲,却也是个好色之徒,对着宋夫人也这般不敬,怎生像个法子在大哥面前告他一状?也除除我胸中恶气。
原来林冲是怀疑宋夫人就是契丹公主,见杀了燕飞龙,借机出山逃走,忽而脱口而出。扈三娘也不理解林冲为何忽然对柳絮儿也关心起来,林冲自知失态,急忙掩饰道:“王头领说的是。”
扈三娘不再言语,向忠义堂方向走去,王英一脸和气抱拳道:“林头领告辞。”紧紧跟在扈三娘身后。
见二人走远,一直隐忍不发的乔三重重的啐道:“林爷与你称兄道弟,没地辱没了英雄名头。”
林冲叹口气道:“去把再兴找来,我有事问他。”
杨再兴所说同扈三娘并无大的出入,林冲疑惑道:“你换衣时,那老者是否有异常举动?”杨再兴大眼圆睁,思索一下道:“那疯老者似乎睡着了,但是手却抓住小衣,嘻嘻,这般老了,也知道害羞。”林冲双眉皱起,默默沉思,杨再兴见师父不言语、一负忧心忡忡的样子,叹气道:“长成大人也没什么好,连天烦恼忧愁的,我还是不要长大。”林冲在沉思中醒来,笑笑道:“你先回去吧,一会你爹该着急了。”杨再兴见未帮上师父忙,意兴索然的走了。
林冲回屋写了张纸条,交给乔三速送给阮小七。
傍晚时分,阮小七匆匆赶到,乔三自觉走到院外望风。阮小七压低声音道:“燕飞龙尸首已给人翻过,又重新埋好,手法利落,好像不是一人所为。”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林冲道:“大哥竟然知晓是何人所为不成?”林冲自嘲笑道:“此事太过匪夷所思,新近从山上搜寻一个疯老者。”阮小七点头道:“听说安神医的徒儿,当爷爷般领回医治。”失声道:“难道竟是此人,安神医也有看走眼之时?”
林冲又问道:“小七是否知晓宋夫人下山一事?”阮小七摇头道:“大哥难道怀疑宋夫人是契丹公主。”林冲苦笑摇头“我真不知如何下手了。”阮小七道:“看来疯老者同燕飞龙关系大非寻常,何妨利用此人寻到真凶。”林冲恍然大悟,阮小七道:“不管真疯假疯,加派好手黑日监视,白日派人前去探查,早晚会查出破绽。”林冲赞道:“小七此计大妙,若这老者果真装疯,必是从水路潜来,小七这几日要加强湖面和晚间的巡视,防止大批敌人潜入。现在梁山是多事之秋,小七兄弟多多费心了。”阮小七抱拳道:“大哥那里话,小七遵命,这就告辞。”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第二日,阿绣正在煎药时,乔三来到,说林冲指派几人帮阿绣照顾疯老者,阿绣喜极而泣,连声赞着林冲。乔三望着疯老者,小心道:“这病不好医吧?”阿绣倒出熬好的药,用口吹着,慢慢服侍疯老者喝下,疯老者口中‘吧吧’声响,似乎饮下玉液琼浆一般。阿绣慢慢道:“或许是我的药灵验,这疯爷爷今早竟跑了出去,你们晚上派人可要看好疯爷爷,万一再跑上山去,就不好找了。”乔三看疯老者服完药安静的躺下,口中含混的答应着,阿绣见乔三根本没放在心上,大为焦急道:“乔大哥,乔大哥。”乔三摆手道:“是乔三哥,非是乔大哥。”阿绣哭笑不得。
疯老者忽地‘嗬嗬’出声,双手在空中一阵挥舞,复而又紧紧抓住中衣,不住扭动,上下摸索。阿绣急忙上前喊道:“疯爷爷、疯爷爷!那里不舒服么?”疯老者双目茫然,胡须不住抖动,阿绣忽然想起,大声道:“你是不是在找珠子?”用食中二指曲成捏珠状,在疯老者眼前比划,疯老者停止动作,皱眉费力的在思索。阿绣喜道:“那珠子果真是你寻到的么?”回头对乔三道:“快去女寨把姜姐姐找来。”乔三静静的看着疯老者,饶有兴趣道:“疯病也能医好,当真天下少见。”阿绣不满道:“是我家祖传药灵验,还不快去找姜姐姐。”乔三无奈派了一名守候在院外的喽罗去女寨寻姜若群。
片刻姜若群一阵风般跑进来,扑到疯老者床边,大声道:“这碧玉簪那里寻来的?”从怀内掏出一方锦帕,小心翼翼掀开,拿出半截玉簪,带着个浑圆润绿的珍珠,递到疯老者眼前。疯老者睁大双目,盯在玉簪上一会,又合上双目,鼾声已开始响起。
姜若群焦虑的瞧着,阿绣在一旁劝道:“姜姐姐不必心急,或许再用过几服药后有转机。”姜若群低低抽泣起来道:“我也来照顾疯爷爷吧。”乔三想起林冲挨棍、受伤全是因姜若群而起,摇头道:“这却不成。”阿绣也劝道:“姜姐姐还是先回寨里吧,这里有什么事,乔三哥一定会及时告知的。”乔三对阿绣的态度非常不满,冷冷道:“那却未必,姜姑娘未必瞧得起我们下人。”姜若群脸色苍白,心中恼怒,可以为了兄长不得不厚着脸皮道:“这疯爷爷若有什么话语,尚请乔大哥见告,姜若群感激不尽。”朝乔三深施一礼,转身走了出去,留下目瞪口呆的乔三等人。
乔三回到大寨,恰好见林冲也匆匆赶回。林冲急道:“那疯老者可有异常。”乔三摇头道:“姜姑娘来询问珠儿之事,疯老者看不出知道此事,我已安排四人黑白照看。”林冲点头道:“我需得下山一趟。”乔三睁大眼道:“是官军又攻来了莫?”林冲摇头道:“听说李逵私自下山向京城去了,神行太保已赶去,但是宋头领怕戴宗无法劝阻李逵,在京师惹出事来,命我率几名头领即刻下山,这里的事你要小心应付,有事多找武头领和阮头领。”林冲无法对乔三说得更详细,带一队亲兵匆匆而去。
疯老者不知是阿绣的药做崇,还是尸气所至,一连两天夜里没有清醒。守看的喽罗也怠慢下来,姜若群每日前来探看一番,又失望而去。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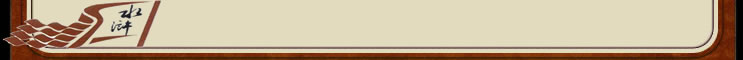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