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九纹龙的第九位师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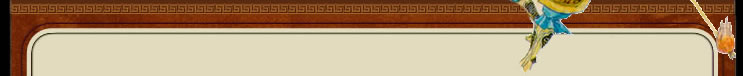 |
|
一
史家庄三四百户人家大多姓史,由于这个姓和某个脏字同音的缘故,为了避讳,我们平日说话比别处要文明些。比如肚子不好上茅房,我们会说去出恭,包括脏话,我们也只会骂“打得你拉不出秽物来”,或者“你去吃狗的粪便”,等等诸如此类。总之,屎字是说不得的,否则就违反了村规,会受到在肥料场毒晒一天的惩罚,说实话,那儿的气味超乎一般的痛苦,事后,至少有个一年半载的,就算吃肥肉也觉不出香味来了。
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特别讲义气,经常偷自己家里的鸡拿到地里和小伙伴一起烧着吃,后来被父亲发现了,他也不懊恼,只是告诉我下次再偷的话尽量偷公鸡,比母鸡味道香,更重要的是,母鸡要留着下蛋,蛋能孵出小鸡来,小鸡长大了还可以再偷其中的公鸡吃。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父亲也是讲义气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辈分有差距,我简直想和他拜把子。据说父亲讲义气也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我们祖上就很讲义气,不但给我们传下了丰厚的家产,也把讲义气的规则和习惯像珍宝那样传下来了。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仗义疏财,从不吝啬。别说是来来往往江湖好汉,就算是路过投宿的陌生人,也好酒好肉的招待。有时候,我也纳闷为什么有我们这样的爷俩,家产非但没败坏干净,反显得更兴旺了?想想小时候父亲讲那个“偷鸡”道理,便豁然开朗起来。
父亲说他最大的遗憾是不会武功,因此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要按照别人的脸色行事,有时候甚至还要多浪费一些银子,才能达到目的。因此,他希望我能学好武功,倒并非为了考个武状元什么的光宗耀祖,而是为了不吃哑巴亏,守得住祖上的这方荫凉。
我能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八岁那年,我和邻居家一个孩子因为争吃一个鸡腿打架,鸡是我从家偷的,说好了每人吃一个鸡腿,结果他吃完了自己的,把我的也抢了过去。我肯定不服,就和他撕扯起来,被揍个乌眼青不说,我过年的新衣服也被他扯烂了。当时父亲还没有当里正,小孩子打架的事他毕竟也不太好管,何况打我的还是个女娃,家境贫寒,衣服也陪不起,只好不了了之,事后,父亲腰痛了好几天。
那件事过后我开始习练武术,最初是为了报这一个鸡腿之仇,后来慢慢竟喜欢上了,这和我的几位师父有关。
二
听说我要习武,父亲很开心。二话没说,就让管家去镇上打了全套的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戟、叉、锤……这些铁家伙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一样我能拿动的,只都能搁在院子里当做排场的摆设。
八岁的孩子力气是小了点,拿不动倒是件幸运的事,否则,我早就当废铁去换了面人。馊主意也是邻居家的孩子出的,那天,我们俩使了吃奶的力气把一只流星锤从架子上挪下来,结果没走三步就砸了脚,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痛苦的大哭,货郎挑起插着面人的担子落荒而逃。
半年后,脚终于不肿了,习武的心又回来了。我决定自己钻研轻功,长工王二告诉我,先种一棵树苗,每天从树苗上跳五十次,树苗逐渐长高,我的轻功就越来越好,等树苗长成院外那些大柳树那么高的时候,人就会身轻如燕,还说南侠展昭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于是,我从父亲床下的箱子里偷了一锭银子给他,让他去市集上买棵树苗给我,种在了屋后的空地里。每天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此处略取三十二个“跳啊”)半年过去了,树苗没有长高,反倒死了。我拿着死去的树苗质问王二,把他吓出一头冷汗:小少爷,这事千万别告诉老爷,我再白送一棵好的树苗给你。
我当然不会告诉父亲,相反,王二给我种下新的树苗后,我又赏了一锭银子给他。人总要讲义气嘛。有了上次教训,这次王二的树苗一定不会死了。结果,我还没跳一个月,树苗就显示出欲死的样子来。我把王二叫过来:这叫怎么当子事?
第二天,王二把新的树苗种上了。这棵树苗的生命力果然极其旺盛,不出半年,我怎么跳也跳不过去了。
父亲发觉此事后,王二遭到了解雇。他收拾行李从我们家离开那天,阳光照在枝繁叶茂的树杈上,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伤心,便偷了一锭银子塞给他,这次他死活都没有接。
后来,我才知道,王二用我的那两锭银子,请大夫治好了他儿子王四的急症。王二种的那棵树一直茁壮的生长着,他儿子王四后来死在我的刀下,因为贪酒,有“赛伯当”之称的王四坏了我的大事,那天我一把火烧了史家庄,逃离的刹那,我回头看到这棵树在火中倔强的挺立着,突然想起了王二。
我始终认为王二是我的第一个师父,尽管我这辈子也没学会什么轻功。
三
教我开手的师父是李忠,在史二和李忠之间,我还有过两个师父,似乎也不应该不提。
十三岁那年,庄上来了个画画的艺人。他说自己是进京赶考没了盘缠,只好在路上为人做画挣点碎银子。我问他是否会纹身,邻居家有个孩子跟着做买卖的父亲去了趟东京,回来在胳膊上纹了条龙,甭管是出汗、洗澡都不会掉色,威风极了,我让这名艺人也给我纹条龙。
你想纹几条?
废话,能纹几条纹几条。
你可怕疼?
我心里想问:有锤子砸脚疼吗?自己的确是有些怕疼的,但话既然说了,再反悔的话就不算好汉,索性拍着胸脯说:我怎么会怕疼呢,应该是疼怕我才对。
纹身的疼痛完全超乎想象,尽管我事先喝了五六碗酒,那持续不断的疼还是钻心而来,像一群蚂蚁不停噬咬涂满蜂蜜的伤口。艺人说这九条龙要分九次纹,每次相隔九天,否则根本无法承受。于是,那八十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包括多年后在东平府所吃的那一百大棍,在死囚牢里所受的非人折磨,也断不能和这次纹身相比。
美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次纹身给我在江湖上带来了一个美丽的绰号——九纹龙。可是谁知道,虫在变成龙之前要付出多少无法忍受的疼痛?
父亲对我的纹身十分满意,赏给艺人许多银子,教他欢喜而去。据说,后来这名艺人到了东京,成为了宫廷画师,还把东京清明集市的盛大场面画了下来,因此名声大噪。那时候我已经沦落成彻底的土匪了,只想把那幅画搞到手,当做明晰的地图,美美去东京抢上一票。
尽管张先生没有教过我武功,但他手上的刺针让我感受到许多道理,他应该算我的第二位师父。
第三位师父是一个来自西域的家伙,说是要去东海求什么佛,路过史家庄。父亲几乎把他当成了圣人,但其实他在武功上根本没有什么造诣,还号称有什么气功护身,纯粹是个骗子。我对他的唯一印象就是他从西域带来了一种有奇特香味的粉末,这种粉末洒在烤羊肉上奇香无比,为此我从家里偷了不少羊,尽管都是公羊,可羊倌还是发现并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就用十两银子把西域骗子赶跑了。
为更彻底的亡羊补牢,父亲开始为我物色一个真正高手拜师。我有过去少林寺学习的想法,但被父亲否决。父亲说去少林寺的路太远,怕出什么事端,还会吃很多苦,恐怕养尊处优的我根本吃不消。其实他内心的想法是不想让我离开他,这一点我能理解。也许去少林寺我也只是想想而已,我对史家庄的依赖和眷恋始终如一,如果不是后来因为朱武他们,恐怕这辈子我都不会离开祖先留下的这片宅院。
李忠出现了。他做为治疗跌打损伤的江湖医师,被管家在镇上的集市看到,请到家里来为父亲看腰。从我小时候的“鸡腿”风波开始,父亲的腰一直不太好,请过很多医生,连吃带敷都没什么明显效果。李忠也一样,他本应该只是为了显示管家的殷勤所走的又一个过场,但他进院子的时候却在那些兵器面前停住了,还提起一把长枪来,问:这家伙好使不?
我讨厌装腔做势的人,冷冷回应道: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李忠拖着枪走出院子,轻轻退了两步,又猛地蹿了一步,一抬胳膊,便抖出两朵枪花,接着用枪尖点地,凌空跃起,在空中,忽然将枪掷了出去,正钉在王二栽的那棵树上。
这几下子完全把我震住了,从此,李忠就在我家住下来,每日教我枪棒。奇怪的是,父亲用李忠的药,腰竟也觉不出痛了,我们全家人都陷入这种莫名的喜悦中。
李忠在我家呆了两年,这两年间他教了我一些功夫,但进度极其缓慢。明明一个动作我已经学的娴熟,他依然让我再练:
苦练基本功,打虎才轻松。
这句话被他重复过一万遍,他的绰号叫打虎将,但从来没给我讲过自己打虎的事,我愈发好奇的问他,他愈卖关子:
打虎很神秘,不能告诉你。
有时候,他也会和我对练几个回合,基本上我都不是他的对手。我按照他教的打虎棍法第一式——“一捅到底”向他捅去,谁知道他一转身,在背后也用这招“一捅到底”,一下就捅到我屁股上。
有一次我被捅急了,拿起棍来,连扫带敲的胡乱打过去,他竟然不知道怎么招架了,门牙被打落了两个,尽管他满嘴鲜血、说话漏风,却依然用口诀来教育我:
对打没套路,早晚要吃苦。
这句话我只能理解一半,晚些我大概会吃苦,可现在吃苦的是他啊。
除了武功外,李忠还教给我一个本事,就是玩女人。
男人除了练武功外,还应该会什么?有一天李忠问我。
卖药?我的想象力只能到此为止。
李忠笑了笑:你有银子吗?
李忠带我到镇上的妓院逍遥了一次,这下不打紧,十六岁的我一下对女人产生了奇异的兴趣。于是隔三差五,我都会和李忠一起以进药材的名义去镇上嫖娼,当然,每次我都付帐的时候,也会把他的那份一起付上。遇到我尤其喜欢的女子,我还会多使些银子。李忠知道后,就劝我不要这样:没意思,婊子无情。
当时我只是觉得李忠说这话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吝啬,直到在东平府的西瓦子,我被那个叫李睡兰的婊子出卖,才意识到李忠在这些事上,还是颇有远见的。
逛妓院的事情还是传到了父亲耳朵里,他的腰骤然疼了,怒不可遏的将李忠赶走。临走前,李忠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前天我一个人憋不住又偷去了一次,下回你帮我把银子给了罢,嫖债欠不得。
那些日子我是正经八百管李忠叫师父的,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几年后在梁山,李忠的座次远在我之后,开始一个哥哥一个哥哥的叫我,每叫一次我心里都哆嗦一下,都为年少的荒诞再度后怕一回。
五
第九位师父王进见到我时,我正在耍第八位师父教给我的棒法,比起第五位师父教的叉、第六位师父教的刀和第七位师父教的锤来,第八个师父教的棒还是颇有神威的。
五、六、七、八位师父也都曾经让我景仰过,但他们后来的结果都和李忠一样。比如六师父以灵活著称,刚学的时候我怎么也打不到他,后来知道他是唱戏的武丑,除了翻跟头外也不会什么,只要闭着眼一阵乱砍,包管要他人命。八师父的棍能舞得密不透风,但只要两块石头扔过去,照样脑袋开花。
这些武功就像粪便一样,看起来也结结实实一大坨,实际臭不可闻。
我边舞棍,边悲伤。
当初为什么要习武呢,那个抢我鸡腿,扯我衣服的丫头如今远嫁他乡,在和那些妓女寻欢时,我脑子里会忽然浮现出她的影子。
我边悲伤,边舞棍。
王进看出了我棍法的破绽,但他怎么能理解我舞棍的悲伤?
这个说着一口官话的异乡人为什么要多嘴呢?
不服,我们就练练?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用如此快的速度就将我打倒,在倒下的那一瞬间,习武的热情再次从我心头点燃,无论如何,我都要他成为我的第九位师父。
王进说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尽管我并不知道这个官职究竟有多大,但八十万这个数字就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父亲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这多半年,我的武功在王进的悉心指导下,进步神速。
王进不但是我经手的师父中武功最高的一个,也是最用心教我的一个。他为什么会如此倾心相授?难道仅仅是因为父亲曾对他施以恩惠?我实在琢磨不透,仅仅在一些小细节上感悟出些原因。
王进是得罪了高太尉才被迫出逃的,带着他的母亲去那个叫延安的地方。我们庄上从来没有人去过延安,包括那些做生意的,甚至都没听过延安这个地名,也许是延安太遥远了,他母亲多病的身体怕是很难支撑这艰苦的路程,如果没有在史家庄的这段医治疗养,说不定已撒手人寰。王进的母亲是个慈祥的老人,有时候她看到我练功那么辛苦,就说:孩子,你休息一下。然后取出一条用凉水浸泡的毛巾递给我。有一次,王进的母亲对我说:其实练武功有什么用处呢?就像进儿,不也沦落到逃亡的地步吗?反倒不如做个老实的庄稼汉子,踏实自在的过一生。
王进的母亲这番不经意的话触痛了我,我念起我的母亲来,她当年也这么说过我,但我执迷不悟。母亲几乎是被我气死的,她出殡那天我都没哭,匆匆埋葬后,当天又跟六师父学起翻跟头来。
我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猜测,王进母子从史家庄离开,一切生死难料,九师父真的想去延安吗?那个遥远边陲不会有东京的灯红酒绿,只能任凭风沙吹老他自己的下半生,只能用陌生的土壤埋葬他母亲的身躯。如果在中原,能有个人学会他的武功,像他那样神勇盖世、闻名天下,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离开,至少还有一个人用和他一模一样的招式叱咤着,显然,这关头,这个人只能是我。
尽管我万般挽留,王进在我武功精熟之后还是走了。我送他们母子俩走了十里,有一种东西,我想忍住它,像当初纹身时那样强忍住,却没能成功。我看着我的第九位师父挑着担子,牵着他母亲骑的马在西方渐渐消失,泪水大滴大滴落下来。
六
半年后,父亲死了。
看到我武艺惊人,他的腰不再痛了。然而有一天,心口忽然疼起来,怎么也医不好,就死了。
死不是件坏事,至少,腰和心口永远都不会再疼痛。
我把他和母亲葬在了一起,狠狠的磕了九个头。
父亲死后我就有了离开史家庄的想法。后来,因为少华山上的朱武、杨春和陈达,我得罪了官府,逃离的时候,我杀了因喝酒疏忽让人把回函偷走的王四,还一把火烧了史家庄。
除了银子,我最想带走的就是王二种的那棵树,这也只能成为一种幻想。很多年后,我经常幻想如果当时真把那棵树带走,植到少华山,再植到梁山,最后植到禺岭关,该有多好。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幻想。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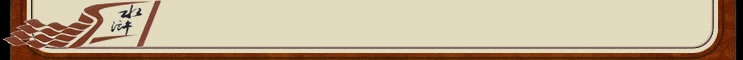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