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刀锋上的行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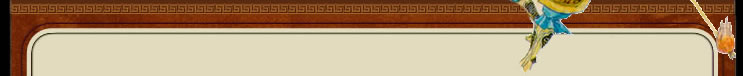 |
|
剑和刀都是杀人的兵器。
不同之处在于喜欢拿剑的人性格飘逸狂放,习惯持刀的人性格阴冷沉郁。
手中这把刀伴随我多年,或者藏在鞘中,或者握在手上。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我带着它走过许多路。
世界上有许多路是没有尽头的,所谓的尽头只不过又是它的另一个开始。
我有一个绰号,叫做行者。
我曾经杀过很多人,他们的血溅在我的刀上,象一朵朵怒放的梅花。
在一次惨烈的战争中,我失去了右臂,没有跟随梁山的人马返回京师,而是留在江南照顾生了毒疮的林冲。当时我甚至想,自己未必能比林教头活的长,没想到他那么快就离开人世了。那一天北风吹动着我空空的袖管,我忽然很想家。
林冲临死之前昏迷了三天,三天里他一直在说胡话,我却听不清一句,仿佛从他苍白的嘴唇中吐出的是另外一种语言。江南的空气潮湿的让人压抑,我眼睁睁看着他惊恐的样子,实在难过极了。最后他指着屋顶说了个我终于可以听懂的词。
北方!
我无法理解他这最后的心愿。林冲死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当黄昏的时候就向北眺望,在暮钟声中眺望那一去不回的刀光剑影,北方有我们的老家,每年秋天都有燕子从那里飞来,黑色的羽毛里藏满往事。
一 大哥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过世了,相依为命的哥哥将我养大。
据说大哥小时候得了侏儒病,所以我们从身材上有着很大的差异。邻家顽皮的小子常取笑说我们不是一个妈生的,那是对我和大哥最大的侮辱,所以我就和他们打,他们以多欺少,渐渐成就了我打架的好本领。
每次出去玩,大哥都会叮嘱:别给人打架,更不要打别人。
每次打完架回家,大哥都会说我:又给人打架,又打别人。
在我记忆中,他这句话重复过无数次。
他们说咱不是一个妈生的!
怎么可能呢?你看我们的胎记都生在右臂上,连形状都差不许多。说着他掀起袖子,露出一块粉红色的胎记,活象一个伤疤。
我也掀起袖子,果然也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活象一个伤疤。
在我想象中,我们的父母应该是那个年代赫赫有名的英雄美人,有次我为了证明自己的想象,去问大哥,他说:天下哪有那么多英雄美人,父亲和我一样,是靠卖炊饼营生,母亲算不算美人我也说不清,其实女人就是一个炊饼,外表美不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味道。
那时大哥还没成家,我不知道他心中的女人应该是什么味道。不过大哥的炊饼的确是方圆十里出了名的。
十八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我打死了当地的一名官吏。我永远都记得那个那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大哥把我送到城外的树林。
兄弟,这个包裹里面有银两、干粮,还有一件棉被心。
知道了,大哥,你回吧。
兄弟,你可得多多保重啊。
知道了,大哥,你回吧。。
还有,大哥从包裹里取出一把朴刀来:这把刀是早年间从张铁匠那里打的,你带去防身吧。说着把刀递给我,姿势仿佛是递给我一只炊饼。
我真不知道大哥怎么还会藏着这么一把刀,记忆中他连杀鸡宰鹅都不会。我把刀从鞘中拔出来,寒气逼人。
快走吧。
大哥。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大哥将我扶起来,说:快走吧。
远处,已经有隐约的火光和嘈杂的脚步声向我们逼来。
我转身跑了,听见大哥在喊:记住,别给人打架,更不要被别人打!
我停下来,朝大哥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兄弟记住了!
这件事情连累了大哥,他被官府抓起来坐了牢。而我用他送我这把刀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的大嫂。
二 柴进与宋江
朋友就是可以肝胆相照的人。
所谓肝胆相照,就是能为一诺独行千里,为义字两肋插刀。
我的第一位朋友是在我这次逃亡途中认识的,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官人,我投奔到他的府中,记得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逃出来?
我杀了人。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
我听说你是可以相信的朋友。
哈哈!柴进大笑两声,就将我收留了。
在柴府的头几个月,我过着神仙一样的逍遥日子,毫无寄人篱下的窘迫,后来这种生活渐渐消失了。
没有一个朋友会象亲大哥那样无怨无悔的养着你,即使他有再多的银子。
除了偶尔陪柴进打猎外,在这里我无事可做。
无事的意思就是没有价值,没有价值的人做不了别人的朋友。 除非他同你一样没有价值。
柴府来过许多象我这样没有价值的人,也来过许多有价值的人,最受柴进待见的是林冲,他当时已经成名,是京城风光无限的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陷害,发配沧州途中路过横柴郡,柴进还利用他让自己府上的洪教头羞辱而去。,
在柴进眼中,林冲是天下少有的英雄,武松不是。
如果林冲能晚些日子来柴府,恐怕那个遭羞辱的人就是我了。假如我遭到那般羞辱,定会等林冲走后,拿刀砍了柴进全家。
林冲被陷害的原因据说是因为高俅的儿子看上了他的妻子,导致飞来横祸。我很同情他,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投奔柴进是因为杀了自己的妻子,他叫宋江,江湖人送绰号“及时雨”。
有个好消息传来:我当年以为打死的那名官吏并没有死,大哥早已从监牢了放了出来,官府表示对此事不再追究。
我可以回家了。
这时候我遇上了宋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从一个角度看上去,他的五官有点象我的大哥,这使我平生了几分亲切感。
这位好汉可是清河县的武二吗?
那时候我还是江湖上一文不名的小卒,他居然能唤出我的名字,好象唤一位故人那样。我的心不由暖烘烘的。
从这一点,我断定他有非凡的领袖天赋,几年以后,他坐上了梁山的头把交椅,尽管他武功低微,相貌平平,却令我景仰。
那天晚上柴进为我设宴送行,但他没喝几巡就推脱身体不适,早早退席了。更可恶的是,柴进还把倒酒的丫环支使走了,后来我每次都要亲自去厨房抱酒,结果因为头晕脚滑摔了一坛子,将我的小腿划出一道血口子来。
宋江的酒量和我比起来差的太多,可能他还不如柴进能喝,但他舍命陪君子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一口一个兄弟的叫着,比我大哥叫的都亲,一说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说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尽管我读书不多,但完全能从这些话里感觉到他的这份豪爽,于是,我们两个都酩酊大醉,吐了柴进一屋子。
第二天,我离开了柴府,宋江送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我让他回去,他也不说话,憨厚的笑笑,继续往前走。当时我想如果有缘,今后定会陪他走更长的路,甚至远征万里。
三 老虎
离开柴府前,有几个夜晚我都从恶梦中惊醒,梦见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从漆黑中向我扑来,算命先生说这意味着我到了生命的攸折点。
还说:你是天孤星转世,注定一生孤独。你做的梦证实了这一点,你必须牺牲所有你爱的人,当做你成为英雄的代价。
我不想做什么英雄。
你是在骗自己。年轻人,这是命啊。
他这句话在我耳畔回荡了许多年。
年轻人,这是命啊。
我命中注定了有这么一只老虎的出现,在我从柴府回家的路上,我打死了这只老虎。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在那个叫景阳岗的地方,我打死了一只老虎。
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篇章了,足以让我骄傲一辈子。
后来有很多人问我打虎的事情。
你为什么打死那只老虎?
你是在为民除害吗?
你是在捍卫人格的尊严不受侵犯吗?
你是在为爱情或者理想做的一次伟大的冲锋吗?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因为真实的答案太简单。
因为老虎要吃我。
它要吃我,我就要先杀了它。这是我唯一的理由。其实那天我已经喝醉了,老虎向我扑来的刹那我还以为是一梦,在它锋利的牙齿的我的咽喉还有零点零一公分的时候我才下意识的醒来。北方很少有老虎,所以包括猎户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把老虎想象成了魔鬼,其实老虎并没有那么可怕,有很多人都可以战胜它,只是战不胜自己心中的老虎。
从此,武松美名远扬。
从此,我做了阳谷县的一名都头。
都头其实是个很小的官,可还是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尤其是当我被称为打虎英雄被人们用披红戴绿的轿子抬到街上的时候,真是如沐春风。这就好象潮湿的柴禾突然见了阳光,那些在阴暗的角落沉积的水分正一点一点的蒸发掉,只剩下一脸灿烂的笑容招摇过市。
兄弟,是你吗?
我听见人群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向我传来,随即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吃力的挤到了人群前面。
兄弟,是你吗?
我一下从轿子里跳出来,跪倒在大哥面前。
兄弟快起来,你为我们武家争光了。
这时候人群中出现了一些交头接耳的吁声,我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我站起来,用目光扫视了一遍这些陌生的面孔,大声说:这是我大哥,一个妈生的亲大哥!
一个妈生的亲大哥早已泪花满面了。
一年前大哥从清河县搬到阳谷县,路上认识了大嫂,一年后大嫂死在我的刀下。
四 嫂子
我第一次见到潘金莲的时候我感觉她很象一只美丽的鸟,说不出它的名字,这种鸟可能会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划过你的视线,却给你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
那时候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嫁给大哥,她有一次告诉我她从来没有爱过大哥,因为大哥的手是习惯了拿炊饼的,她不愿做大哥手中的炊饼。
潘金莲没有出嫁之前是一个员外家的丫鬟,这个员外想纳她为妾,被她拒绝了,员外非常恼火的问她原因,她说我宁可嫁给普通人,过平凡的日子,也不愿在大户人家做小。
然后她又说:明天,我去城外一条小路边等候,路过的第一个男人,无论他英俊或者丑陋,富贵或者贫贱,我都会嫁给他。员外一怒之下答应了她的要求。
那年她十八岁。我不知道她在路边等待的是爱情还是命运。
曲径通幽。
那天一早,大哥挑着一担炊饼从那里路过。
从此,她成为我命中注定的嫂子。
有一天嫂子对我说,在她心情郁闷的时候,她就去城外那条小路看看,猜想一下如果当年第一个从这条路走过的人不是我大哥,又会是怎样一个男子?
我说:猜想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第一个从这条路走过的人是我大哥,这是无法改变的。
嫂子说:即使不去猜想的话,我还愿意知道会不会还有人从这里路过。
我把腰间的刀解下,拍在桌子上,说:不会有人敢从这里过了。
那一天窗外的雪纷纷扬扬。
嫂子取出一只酒壶,斟了两盏酒。
她说:可是已经有人从我心里走过了。
说完,她的眼睛痴痴的望着我,象黑暗中两团跳动的火焰。
我不敢去正视她的眼神,我深怕自己会象陷入沼泽那样陷进去,然后窒息,然后死亡。
潘金莲拿起一盏酒,先饮了一半,举杯说道:小叔若有意,就饮了这半盏。
我已经心乱如麻了。
在我心里也有一条路,想不到第一个从这里路过的,竟是我的嫂子。
大嫂,休要无礼。我猛的推开窗,一股冷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
潘金莲在我身后笑了起来,清脆的声音好似一种鸟的啼叫。
这场雪在我记忆中下了许多天,几天后,衙门有一个出远门的差使,是去一个遥远的北方城市。我主动请命,接了下来。与其说是在逃避别人,不如说是在逃避我自己。
大哥把我送到城外的树林,树枝上落着厚厚的雪,象一大群身着孝服的年轻女子。
大哥,我一去就是几个月,你多保重。
是的。
对了,嫂子… …也保重。
大哥没有说话。
还记得两年前那次你送我吗?
那是在另一片树林。
这片树林离那片树林究竟有多远,我们谁也说不清。但是在我身边的大哥已经越来越沉默了。
你回去吧,大哥。
你先走吧,兄弟。
不,你回去吧。我的语气非常的固执。
好吧。
大哥缓缓转身走了,黑色的背影渐渐消逝在茫茫雪地之中。
在他背影消逝的一刹那,一只乌鸦从白色的地平线上掠过。雪天据说是不会看到乌鸦的,这是个不祥之兆,但我怎么也没预料到这竟是我和大哥的生离死别。
在北方的这段日子,差事办理的异常顺利,只是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惆怅萦绕着,还经常做一些奇怪的梦,几乎所有的梦中都在重复这么一个场景:一名身姿婀娜的女子在落叶飘飘的夕阳中舞剑,剑花很美,能让人联想起许多美好的事物,只是无论怎样也看不清这个女子的面孔。在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的剑花中,这个女子忽然化作一团红光,无影无踪了。
这个冬天格外的冷,也格外的长,我以为我能够在这个冬天忘掉那个女人。
突然有一个晚上,在那个梦中的场景里,我看见了舞剑女子的面容,她向我凄然一笑,这笑容很象我的嫂子。
第二天,河边的柳树全绿了。我才想起来我已经出来了很久。我不知道阳谷的柳树是不是也绿的那么灿烂,便决定回去看一看。
阳谷县异常的安静,在回家的街道上走路甚至都能清晰的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你大哥死了。
嫂子告诉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非常平缓,仿佛在说一个掉在地上的炊饼。
他是病死的。
大哥!我跪倒在大哥的灵位前,真想大哭一场。可是男人怎么又能轻易落泪呢,并且还是在一个女人面前。虽然我的心里难以盛下这么多痛苦,但我绝不能让它从我的眼睛中流出来。
眼泪在我心中冻成了一把雪亮的刀。
生老病死,都是天意,我的眼泪早哭干了。嫂子说。
我抬起头,看见潘金莲空洞的眼睛里闪出一丝亮光。
原来阳谷县的柳树早就绿了。
你说什么?嫂子有些惊讶的望着我。
没说什么。我站起来,推开窗,不远处果然有两棵垂柳枝叶繁茂。
你大哥临死的时候,你也不在身边,对门的王婆婆做主,烧了。
潘金莲说“烧了”两个字时,好象烧的不是我大哥而是一把柴禾。
大哥得的什么病?
心疼病。
他的心恐怕还在疼着。我冷冷的说。
小叔说话怎么莫名其妙的?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都是莫名其妙,也有许多东西总会水落石出。我在心里这么想,没有说出口。
我暗访了给大哥验尸的何九和一个大哥生前的朋友郓哥,我最不愿猜中的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是嫂子杀害的大哥。
这件事情比大哥的死去更令我悲痛,我彻底的陷入一种绝望的状态。我一度认为大嫂是为了那个叫西门庆的男子才对我大哥下的毒手,然而,事情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这天晚上,我在大哥的灵位前沉思。嫂子悄无声息的走过来,说道:你大哥今生命苦,娶了个不该娶的女人,但愿来世能过上和和美美的好日子。
我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其实我知道你已经明白了真相。我不怕,因为你大哥在我心中早就死了。
我的牙齿都快咬出了血。
嫂子接着说道:其实有很多刹那都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如果那天你喝了那半盏酒,你就不会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更不会有西门庆在我生命中出现,更不会… …
她的声音呜咽了。
嫂子我今生命苦,爱上两个不该爱的男人,一个令我心寒,一个令我心狠……我的身家性命也葬在这二位身上了… …其实我有什么错,不过是为了和我爱的人在一起,过上和和美美的好日子,这难道也算错?贞洁牌坊、伦理道德可以令那么多尘世中的凡夫俗子心惊胆战,包括打虎英雄,堂堂八尺男儿,竟不如一个弱女子敢爱敢恨……
住口!我“嗖”的拔出刀来,只是心头那把眼泪冻成的刀已经开始融化了。
这又何必呢,这只能表明你的软弱。嫂子凄然一笑,和梦中那个舞剑女子竟是一模一样。
我要杀了你和西门庆,为大哥报仇。
今天不是你杀我的时候,因为事实上并不是你愿杀我,但我一定会死在你的刀下。至于西门庆,他的武功与你差不许多,你们俩定会有一个去阴间陪我… …真的,我倒希望那个人能够是你,让我不枉活一场。
我把刀插入鞘内,转过身去,背对着她说:潘金莲,你走吧。这时候,有一种液体从我眼睛中流出来了。
我不走,我哪里也不去,我爱的两个男子,一个欲杀我而后快,一个吓的不敢见我了,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死在… …爱人的刀下,也能圆你一桩心事。
如果这个女人不是我的大嫂,如果我从小就没有大哥,如果这些奢望的如果都能化做事实,那又会怎样?如果仅仅是如果而已,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第二天是谷雨,每年这时候都要有一场甘霖,而这一次的阳光却分外娇媚。我把街坊四邻都请到了家中,置办了几桌酒席。酒桌上的气氛极其沉闷,大家都在心里暗暗的揣测着即将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敢说离开,大门让我唤来的两位衙役锁住了。
我点上三柱香,插在大哥的灵位前,转身面朝大家,面无表情的说道:武松从小无父无母,大哥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们是一个妈生的。
接着我端起一碗酒,洒在地上:大哥对我恩重如山,七岁那年我得了重病,大哥冒雨背我走了三十里路去看医生… …
三十三里。嫂子说。
十八岁时我跟人打架出了人命,是大哥替我坐的牢。从牢里出来,大哥娶了漂亮的嫂子,我原以为这是上天对大哥半世辛苦的回报,谁知道不到两年就惨遭横祸。嫂子说大哥是得了心疼病死的,不知道大哥现在的心还疼吗?
我又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将刀架在潘金莲的脖子上:嫂子,大哥是得了心疼病死的吗?
潘金莲冷冷的看着我说:是我害死的武大。
王婆忽地从一旁扑过来,说:你可别乱说。
老猪狗!我飞起一脚将这个心如蛇蝎的老婆子踹的昏死过去。
潘金莲把与西门庆、王婆如何谋害大哥的事说了个明白,我一句也没记住,只听得她最后说的是:杀了我吧。
我一生杀过许多人,想不到我杀的第一个人竟是我爱上的第一个女人。
嫂子的鲜血从喉管喷涌而出,带着她滚烫的体温溅在我的脸上。
原来,一个人死去的姿势都可以那么壮丽。
从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了“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的女子。
嫂子的血在我脸上渐渐干了。
接着,我去狮子楼杀了西门庆,他武功不错,可我的武功更具杀气。其实我都有点羡慕他的死,因为在那边一个世界,会有一个那么深情的女子陪伴他。
我被发配孟州,带上铁枷走出阳谷县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照得那片树林葱葱郁郁,一片生机。大哥的坟就在这里,我在坟前多叩了几个头,我想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六、施恩和蒋门神
一个人在这个纷杂的世界上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我形似一匹孤独的狼。
去孟州的路上,我遇上了一个女人,她让我叫她嫂子,后来,她和我一同上了梁山,江湖人送绰号:母夜叉。
去孟州的路上,我遇上一名非常年轻的侠客,他浪迹天涯的原因很特别,是为了找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我们聊的很投缘,虽然我们是两种性格完全不同的男子,有时候的心情却是共通的,再次遇上他的时候我已经在南方出家了,我惊奇的发现他竟然和我一样断了一条手臂,他说那个他要找的女人让他等十年,十年是一段多么漫长的岁月,说真的我有点怀疑他能不能坚持下去,再后来据说他们终成眷属,双双退隐江湖,人称神雕侠侣。
我宁愿相信这是个爱情的童话,因为对于我来说,所有看似美好的东西都象童话一样破灭了。
在孟州大牢里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不但没有罪受,还有大鱼大肉天天相伴。比在柴进家开始那段日子还要舒服。就连新犯的一百杀威棒也被管营免去。这等待遇不象是对待一个杀人的囚犯,倒像是一个财主家新上门的女婿受到的殊荣。
这一天我说:我不吃了。
送饭的老家伙很诧异:是不是吃的腻了,要不我去换点素的?
谁让你这么做的?
你吃就是,我家主人不让说。
那我就不吃。
我固执的语气和凶恶的眼神让他不敢继续问下去,他放下饭,一溜烟走了。
半柱香功夫,来了一位官人模样的男子,拱手说道:哥哥可是打虎武松?
我说是。他又说:兄弟久闻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我只好说:哪里哪里。
坦白的说,我不喜欢这种人,他的名字也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就是施恩,这个名字总会让人自然联想起“图报”。
他说很想交我这个朋友,我想自己落难之际,别管怎么说,人家也是一片衷肠,就在心里答应了。
施恩果然是图报的。
一天,他请我去他家的后花园饮酒。酒过三巡,我发现t的胳膊抬动时不太自然。
你的胳膊?
施恩长叹道:说来话长,不说了。
既然你不说,我就不多问。
那我就说吧。
接着他给我说起了孟州城外的快活林,那里有几十家生意兴隆的酒馆,曾经是他的地盘。后来来了个叫蒋门神的将快活林抢去,施恩带人去说理,反被毒打一顿。
这些天所有的奇怪事情现在都迎刃而解了。
令我痛心的是蒋门神是在我之前来的孟州。如果是在我之后,这将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施恩果然是图报的。
我一用力,将手中的酒杯捏的粉碎。
我说:明天我去快活林。
施恩说:还是养好身体再去吧。
我想反正早晚都得去,否则还是一桩心事。
这个石桌有多少斤?
少说也有百十斤吧。
我吸了口气,一把将石桌举过了头顶。旋即听见盘子在地上破碎的声音。
明天我去快活林,身体不成问题。我一字一字的说道。
翌日清早,施恩送我到孟州城门的时候,说:前面就是快活林了。
我沉默了一下,说: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啊,什么都能答应。
快活林有多少酒家?
三四十家吧。
我要在每个酒家喝上三碗酒,再去找蒋门神算帐。
这… …施恩很是犹豫。
放心,我醉不了,心里清楚。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间很想喝酒,我希望能在见到蒋门神之前忘掉那些事情。
我没有带刀,我自己就是一把握在别人手里的刀。
那天我真的喝醉了,蒋门神被我揍的一塌糊涂。
人的武功好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去战胜一些武功不如自己的人,也会被一些不会武功的人轻易就战胜了。
我并没有杀蒋门神,因为我想如果他和施恩的位置换一下,如今倒在地上的就是另外一个人。
七、都监府
孟州的天晴朗的像一把明晃晃的刀。从这把刀面的反光中,我看到自己的影子,它有着英雄般的轮廓。我甚至忘记了我是一名囚犯,尤其是认识了张都监之后,我便彻底离开了孟州大牢。
那时候我刚刚打败了蒋门神,施恩夺回了原本属于他的快活林。但我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快乐,我总是梦见死去的大哥。还有嫂子,那个美丽的女人经常在梦中对我笑,她死在我的刀下,临死的时候也是这么笑的,这笑容令人心碎。
我想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开始,张都监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
都监府是一所很深的庭院,被葱郁的树木遮罩的不见天日。庭院深处,有一座鸳鸯楼,高耸的楼脊上有一对琉璃鸳鸯,我没有见过真正的鸳鸯,第一次到鸳鸯楼见张都监的时候,我被彩色的琉璃所反射的阳光刺的睁不开眼睛。
张都监是一个会一直向你笑的人,他的笑容和蔼而又亲切,有点象宋江。
张都监笑着说:武都头乃打虎英雄,在府上当教官,实在是委屈了。
我说:不委屈。
张都监笑着说:单就你的名声,也能令寒舍熠熠生辉,你又何必这样客气呢?
我说:不客气。
张都监笑的很爽朗,让我想起当年景阳岗的虎啸。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名叫蝉儿姑娘,她说她是张都监干女儿,张都监命她来服侍我,我对她说:武松不需要人来服侍。
蝉儿说:那怎么行呢,武都头是贵人呀。
我说:什么都头?贵人?武松乃一名囚犯而已。
蝉儿眨眨眼睛,说:那我叫你哥哥吧。
蝉儿说话的声音非常清脆美好,象一串熟透的樱桃在树枝上荡漾。
我笑笑说:好吧。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叫我哥哥,我没有妹妹,从小是大哥把我带大。大哥是被嫂子害死的,为此我杀了嫂子。嫂子活着的时候曾经有一天问我是否愿意和她共同喝一杯酒,做一对鸳鸯。尽管那时候我连鸳鸯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我断然拒绝了她。我知道鸳鸯什么样就是在鸳鸯楼,在鸳鸯楼,我认识了蝉儿。
蝉儿有个愿望,就是让我带她去看大海。她对我说:哥哥,你能带我去看海吗?我们一起去海边吧,从这里跑出去,在海边盖个小房子,你打渔,我织网,过没有纷扰的清净日子,好不好,哥哥?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觉得她的想法十分荒唐。我是英雄,可以赤手空拳打虎,也可以舞刀弄棒杀人,怎么可能去海边打渔?我笑蝉儿的无知和单纯,蝉儿被我爽朗的笑声把脸震红了。
我很怀念蝉儿和我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她是一个聪明、纯真的女孩,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内心深处那一点早已僵死的东西开始融化,仿佛春天的阳光照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然而,和雪原的辽阔、寒冷相比,这阳光则显得那么孱弱、无力。
这一天是张都监的生日,在鸳鸯楼举行的晚宴上,大家都很开心,推杯问盏,吆三喝四。席间,张都监笑着对大家说:今天是都监府双喜临门的日子。
有人问:都监大人,你说的一喜是您的大寿,这二喜是?
我想将我的干女儿蝉儿许配给武都头。
就象一把刀从鞘中拔出来的声音,很容易让喜欢拿刀的人陶醉。这种声音似乎是从楼顶传来的,似乎是那两只琉璃鸳鸯在鸣叫。
我被这忽从天降的幸福激动的冲昏了头脑,那时候我真的年轻,还没有达到宠辱不惊的境界,在一片“天作之合”的呼声中,我飘飘不知所以然了。
蝉儿从人群中羞涩的走出来,宛然一笑。
那一瞬间,我突然看到她的笑容似曾相识,好像我的嫂子。
我还发现,蝉儿的纯真的眼睛里多了几分凄婉,在月光中更显得楚楚动人。
张都监笑咪咪的问道:武都头,你可愿意?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张都监笑咪咪的说道:老夫就擅自做主了。
那天我实在记不清自己喝了多少酒,醉眼朦胧时,看见蝉儿抱着琵琶在唱:思悠悠… …恨悠悠… …恨到何时方始休……
蝉儿唱歌的场景似乎不太真实,因为那天我回房间的时候问她那首歌的名字,她居然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唱歌,还说我喝多了。可她的歌声是那么清晰的在我的记忆中回荡着,怎么也不能平息。
刚刚躺下,就听见后院有人喊:捉贼!
我忽的坐起来,拿刀,推门。
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前。
哥哥… …你不要去。
蝉儿?
哥哥,听我一次,不要去。
我去捉贼。
哥哥… …
怎么了?一个小小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烁了一下,马上就消失了。
同时,一个黑影从花园中闪过,是贼。
我推开蝉儿,毫不犹豫的冲了出去。
贼影仿佛从哪里见过,一时想不起来。
伴着一阵异常的风声, 一张大网从天而降,将我裹了个结实。
你们干什么?!我又急又怒。
捉贼。
我是去捉贼的!我大声分辨。
张都监笑着说:武都头当真是去捉贼的?
我说是。
那可不能冤枉好人,快,去武都头的房间看看。
家丁在我的房间里搜出了一包我从未见过的金银珠宝,打开来,在烛光下晃的眼睛生疼。张都监冷冷的说:家贼难防。
我的大脑简直要着火了。我突然想起那个熟悉的贼影是谁。
蒋门神。
可这包赃物怎么会在我房间呢?
一名美丽的女子俯到我耳边,用极小的声音说:哥哥,我对不起你。
那些愤怒的火焰突然间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汹涌的海水。
贼配军,我真想不到你会这么对我。张都监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我武松是响当当的一条汉子,既然中了人家的圈套,再解释又有什么用,只能用自己的铁骨铮铮去承担。
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盛满谎言的嘴唇,那么多藏满圈套的笑脸。
那些海水顷刻间在我体内结了冰。
我又重新回到了孟州大牢,陪伴我的是冰冷的铁窗。
施恩已经被贬了,快活林上飘扬起写有“蒋”字的旗帜。
这一切如此富有戏剧性,真象一场梦。
我差点判了死刑,法律是属于算尽机关那些人的。
我被发配至很远的边疆,上路那天格外闷热,几万只蝉在树上悲鸣。
出了快活林,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前方。
蝉儿提着一坛酒:哥哥,我是来为你送行的。
我低着头,一言不发,目光中只有木枷和铁链。
蝉儿泪流满面的望着我,那一瞬间,我的心颤抖了一下,我想:如果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背叛过我该有多好,如果我从来不认识这个女人该有多好。就像我的嫂子,如果我从来没有在她的世界里出现,也许她现在依然和我的大哥恩爱着,也不会再有西门庆,我们都会甘守属于自己的平凡。平凡多好,不用付出做英雄的代价。
我接过蝉儿的酒坛,摔了个粉碎,酒在地面上渗出两只鸳鸯的形状。
蝉儿脸上的悲痛也被我摔的无影无踪了,转换成那种我在梦里很熟悉的笑。她用手扶住我的木枷,用极小的声音说:酒是有毒的,他们要在飞云浦对你下手,哥哥小心。
我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惊讶和愤怒,将蝉儿一把推开。
飞云浦。这两位受了张都监贿赂的差人要杀我。
我恨透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这么多人都想置我于死地。我只能杀了他们,这个世界来不及把我当人看,我就先把它当做一头野兽。
这两个可怜的都差被我砍的血肉模糊。
当夜,我赶回都监府,张都监和蒋门神等人正在鸳鸯楼喝酒。张都监说:武松的人头怎么还没到?
武松的人头到了。我破门而入,看到一张张惊惶失措的脸。
鸳鸯楼顷刻变成一片血海。
我在鸳鸯楼的墙壁上蘸着他们的鲜血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杀人和打虎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也许人很多时候都比老虎还要残暴。
在我准备走的时候,听到楼顶传来一阵琵琶声。
蝉儿站在鸳鸯楼的楼顶,抱着琵琶在唱:思悠悠… …恨悠悠… …恨到何时方始休……
我翻身上了楼顶,蝉儿放下手中的琵琶,说:哥哥,我知道你会回来,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
等我来杀你吗?我冷冷的问。
蝉儿向我走来,抓起我从都差手中抢来的朴刀,刚才,这把刀砍死了太多的人,刀刃都有点卷了,蝉儿把朴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告诉你一个秘密。蝉儿说:我是蒋门神的女人,蒋门神和张都监是一伙的,他很早就把我霸占了。
认识你之前,我一直觉得蒋门神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你那时候打败了他,我想为他报仇。认识你之后,我很后悔,但已经晚了。这世间根本就没有顶天立地的英雄,也许你差点就是了,但你放不下英雄的架子,英雄是不应该有架子的。
我把刀夺下来,扔到一边,心乱如麻:你走吧。
蝉儿一边后退一边说:好,哥哥,我走……我走。然后纵身跳进夜幕中。
我想抱住她,可已经晚了,蝉儿像一片飘落的树叶,在坠落的过程中大喊:哥哥,来世… …
也许是蝉儿临死前的话真的没有完,也许是我没有听清。那对琉璃鸳鸯一旁是她的琵琶,一旁是我的刀。凄凄的月光洒下来,我的脸被刀面映照的惨无人色。我不敢肯定蝉儿最后说的两个字是不是再见。
九、二龙山和梁山
平民、都头、囚犯、逃犯… …
下一个属于我的角色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也没得出答案。其实人生都是安排好的一处戏,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过场而已。
在十字坡,孙二娘送给我一套行者的装束,我很喜欢,每个人都是人生路上的行者,在路上走着是幸福的,别担心没人陪伴。
如果脚下的路变成刀锋那般锋利,我们可以踩着仇人的尸体前行。
二龙山上,我认识了一个奇怪的和尚,在他心中没有任何的佛门戒律,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抱不平。我问他: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平的事,你能管的过来吗?他说他会尽力。
尽力,就够了。
再后来我们去梁山投奔宋江,和他一起四方征战。直到我被敌人砍断了一条拿刀的手臂。
施恩说他会让他的后代把我们的事写成万人传诵的书,我真不太相信,因为有很多关于我的事情我不愿意真实的告诉别人,只希望在世人眼中的我能是一个冷血的英雄。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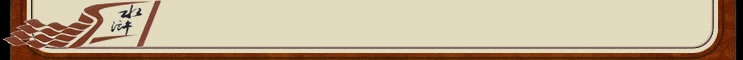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