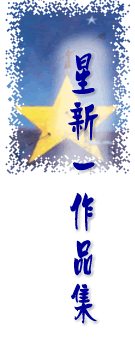
窗口
这位姑娘十八岁,肌肤好象初夏清晨的花草,水灵灵的;双眸充满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乌黑珐琅似的秀发细如雨丝。她映在手镜里的模样显得那么稚气。当然,手拿明镜,瞧着镜中人的本人,同样也是那么稚气,不论是表情,头部,直至心灵深处……
深夜就寝前,总要花费很长时间梳理青丝,这已经成为她的习惯。与其说是“习惯”,莫如说是“力争”更贴切些。因为她深怕困慵于梳妆而失去难得的机缘。机缘宛如彩虹,不知什么时候才出现,并且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
她不仅年轻而且自由。她从外地的小镇来到大城市,住在亲戚经营的公寓里的一个房间,过着独身生活,已经将近一年了。白天她去西装裁剪学校学习,放学后就和朋友们排练节目,偶尔去玩玩滚球游戏,或者去溜冰。家里给她寄来的钱足足够用。
她不仅自由,也很快活。大城市的生活,五光十色,不断地给人以刺激。不过,也许由于习以为常,近来她对于声色刺激,感受已经有些钝了。尽管如此,她一直幻想亲身体尝一番刺激的心情,却丝毫未减。
她放了刷子,把小镜立在身旁小型电视机前。然后她将脸儿贴近镜子,自言自语道:
“我适合上电视,非常合适……”
这也成为她近来的日课了。
在电视上出场,沐浴在辉煌的灯光中,众人瞩目,周身都感受到阵阵艳羡的赞叹声……那一定是梦境般充满着美妙刺激的世界!
她挪开镜子,打开电视开关。显像管亮后,出现了几匹马在西部沙漠奔驰的画面。大约这是夜间的电视节目。但她又换了个频道;却没有出现任何影像,只有无数的光点在舞动;和不知什么发出的似乎在空中飞舞的杂音。
她以不胜憧惺的表情注视着电视屏幕。心想:“有朝一日,也会映出我的身姿。”她情不自禁地在想象中描绘自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惰景。这也是她一向的癖好。她一定要设法走进荧光屏。
她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蓦地一留神,只见荧光屏上出现了又白又亮的光雾,仿佛预示着什么,那光雾竟然晃动了起来。怎么问事?是否因为目力过度疲劳?她眨眨眼,再一次凝神注视。
画面上似乎是有一个人影在晃动。图像逐渐清晰起来,原来是位年轻姑娘。也许由于长时间凝视那耀眼的光亮,昏沉中看见了希望之梦?但是,随着图像愈加明晰,则辨认得出那位姑欣既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她的女友。
那姑娘不知何许人也。似乎在简陋的屋子里在演戏,而且演得正起劲儿,手舞足蹈,全是大动作,并且大喊大叫。
她把音量旋钮调到最大极限。但是,只听到宛若飞流直下的涛音,却听不见人的语声。大概不是正规播放,而是试播传来的电波吧?因为报纸的节目表上没有刊登这个节目。夜,又是这么深了。而且,这个频道,并没有相应的电视台。由于听不见说些什么,也就不知演的是什么戏了。
她看了一会儿,轻蔑地喃喃说道:
“别美!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我,会演得更好。况且,论体型,论长相,都比她……”
这里没有人来责备她,因此她就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后她闭了开关,入梦了。
翌日,她独白漫步在黄昏路上,身后竟然有一个男声把她叫住。
“喂,喂……”
回头一看,是个陌生人。
“你是……”
“我是电视台的……”
此人究竟有多大年纪,简直难以断定。但见他相貌虽然年轻,却显得很老成。也许从事电视工作,就会给人以如此感觉吧!
“叫我有什么事吗?”
“嗯……冒昧提起这个问题,有些失礼。不过,你想不想当电视演员?”
一听这话,她的心顿时剧烈地跳动起来。这可是朝思暮想的心愿,机不可失呀!这是将从百无聊赖的生活一下子升到荣誉之巅的自动扶梯啊!多亏梳理乌发,从不怠慢……
她窥伺了一下对方的脸色。但见他面无表情,也并不热情。但至少不象是开玩笑,尽管如此。她还是小心措词,问了一声;
“我不是没有这种想法。不过,我能胜任吗……”
对方也许听得出她那谦虚的语调中夹杂着自负,便说:
“你自己认为如何?”
她脸红了,回答道:
“我觉得总还可以。”
“那么,近日内和你联系。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她担心对方会变卦。要是错过这个机会……”
“我什么时候都有时间,现在就可以,不知您是否方便?”
“我也是什么时候都没关系。”
“那就求求您啦。”
对方并不立即应允。
“不过,你还是和谁商量一下再……”
“没有那个必要。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没事儿!”
“既然这样,现在就走吧!”
说着,那男人指了指停在不远处的灰色小汽车,俩人走了过去。那男人坐在驾驶席上,她坐在旁边。小车飞也似地驶去了。
意想不到的幸运使她喜不自禁,再也不能缄默。
“电视台的工作,很不平凡吧?”
“不!一旦涉足,再也拔不出脚来。若想改变主意,现在还来得及。”
“不,我担心也许会被淘汰。至于说什么退出,这没有考虑的必要吧!”
“你那么向往做电视演员吗?”
“是的,只要能上电视,我别的什么都不求。”
她笑着回答。那男人开着车也含笑说道:
“你这么虔城,一定会有作为的,不这样是不会胜任的。”
小车慢慢行驶在夜幕方张的长街。性急的小店,已燃亮了霓虹灯招牌。
“本想从这儿向右拐,可这儿拐不过去,还得绕回去。”
说着,小车从他指点的交叉路口向左转,又向左折上一条小路,最后又向左拐。
好容易才折回原来的地方。
不过,她觉得和刚才的地方不太一样。是那条路错过去了?还是方才太高兴没看着呢?据说道路这东西,换个角度看,就会看成另外的一条。
汽车重新费了好大劲,反复右转弯。她想看看路边停车站的站牌,可正在油刷,看不清楚。
暮色渐浓,弄不清车是在哪里开。知道的只是;车外是街道和无数房屋。
这时,车子稍稍加速,无意中又投进一条路。
这条路没有街灯,车窗外黑漆漆一片。
“哪儿呀?是这儿吗?”
“不远了,马上就到。”男人回答道。
少顷,车子停了下来。她被催促下车后,仰视一下旁边的高大建筑。
“这座楼……”
“这楼是电视台摄影楼呀!”
“在这种地方,什么电视台?”
暗雾中楼房耸立,更显得昏黑。
“是个新成立的电视台。你若是认为不理想,我再把你送回家去……”
然而,刚才还想回去的心情,这会儿已无影无踪了。此刻地正想:再迈进一步,愿望就要实现了。
她跟着那男人走进门厅。厅内没有她想象中那般华丽,银白色的灯光洒满寂静的长廊。
听不到那男人的脚步声,只听自己的皮鞋在得得作响。
“就是这间屋。”
说着,男人随手把门打开,屋内射出耀眼的灯光。她走进去,好半天眼睛才适应。当她看清屋内的情形时,不禁失声叫道:
“哎呀,这……”
原来这屋子和昨天夜里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那间屋子一样。
男人点头,声音带笑,可面部却依旧设有任何表情。
“是的,你已经明白了吧!”
“明白什么呀?这屋子是……”
“这就是摄影室。这栋楼里同样的房间有好几间,专门收容电视台的牺牲者……”
她双眉紧锁。
“够了!我不舒服,让我出去!”
“那可不行。我几次提醒过你,问你是否想改变主意。”
“那,我自己出去,然后就去控告你。”
“这也是不可能的。这扇门只有我可以出去,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通行。”
“太残酷了,你简直象个魔鬼!”
“不!别误解。不是象魔鬼,我就是魔鬼。”
“说谎,哪有什么魔鬼!快别搞恶作剧了,让我出去!”
男人没有答应她,却说道:
“有魔鬼。只要有它存在的必要,就不能没有。当然喽,是称呼魔鬼,或是根据别的现象起个名字,这,随你的便……不过,失踪之类的名称好象不大贴切。”
“什么魔鬼!根本没有必要存在。”
“当然有。如果讨厌的差事没人肯干的话,整个世界就会灭亡。如同需要家禽屠杀业者、死刑执行人、执达官等,魔鬼也是必要的。我自己也并不是心甘情愿。早就想适可而止,销声匿迹。可人们的欲望不允许我这样做。”
“也许如你所说。可这与我有何相干?”
“有关系。比如电视演出,为了树立起光辉顶峰的名角,就不能没有在显像管下默默死去的入;为了竖起纪念碑,必须有奠基石;美丽的花朵要有根。然而,谁也不愿做奠基石和花根。进行调整的就是我。为了使幸福女神健在,就需要我这样提供牺牲者的角色。”
“随你的便,反正我要出去!”
“除非人们从心中赶走要幸福女神健在的幻想……”说话间,那男人在门口消失了。
她立刻紧紧追赶,结果撞在厚厚的门上,被弹了回来。
再也不见那男人的踪影,她心中只有痛悔。门,怎么也推不开,想拽又没有抓手。
她想尽办法,但一切都以失败而告终。她已经精疲力尽,茫然地环视这间屋子。室内任何装饰品都没有,混凝土的墙壁上只开着一扇小窗。所谓小窗嵌着厚厚的麻玻璃,相当结实,不可能打碎。即使弄碎,窗口太小,也出不去。
她望着小窗发呆,一筹莫展。不一会儿,小窗似乎透亮了。
窗外象是谁家的屋子。一个年轻姑娘正望着这边。那眼神里充满着憧憬和渴望。
“喂,救我出去!”她挥着手,拼命地连连大声喊叫。这是唯一能求救的人。然而,声音象一点也传不出去,听不见……
这时,她顿时回忆起昨天夜里在电视上看到的情景。窗外的姑娘也会和我的命运相同。既然不可能得救,那就索兴制止其他人再做无谓的牺牲。
她设法要把这件事告诉给窗外那位姑娘,可是,这番努力也终归徒劳。
只见窗外那位姑娘的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神色,随之看到她的嘴在微动。虽然听不见说什么,但那意思立刻就能明白:
“拙劣的演技,要是我的话……”
(译自《早川书房》1982年版星 新一著《假如冬天来到》)
孙立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