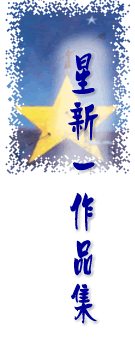
面孔
有那么一位男子。他还没有孩子,但有一位中等水平的妻子。他上一家普通的公司工作,虽已放弃了拼死竞争升职晋级的念头,但也不愿怠惰到落后于众人的地步。可以说,他过的是一种宁静的生活,日月如同春潮,昏沉沉地从身边不断地流逝。
这是一种平庸的生活,但在如此生活过程中,他的心底上不免荫生了一种意念,那就是对这种平庸生活的抵抗心——难道我就这样算了吗?这样的方式只能算是生活在支配我,找难道不应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吗?
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最后竟发展为一种彻底解脱的愿望,那就是使过去的自我消亡,另走一条全新的道路。那样的生活将是自由和充实的。这种念头如此具有魅力,以至他刚一想到,浑身便一阵阵发抖。
他想使这个计划更臻完善,于是,去找整形外科医生:
“请给我的脸做一次整形手术。”
医生看着他,不解地说:
“没必要这么做吧?您的面孔也许是比较平常,但也决不算难看呀?”
“不,正因为如此,所以得想个办法。我想有一张具有个性的面孔,哪怕难看点也没关系,因为我打算从头开始,另闯一条富有个性的人生道路。请您一定帮忙!”
“那么,让我们研究一下吧。请您等一个星期。”
医生知道这个男子的决心很大,只好这样回答,因为有些人过了几天便会改变念头,放弃手术要求的。可是这个男子却利用这些天时间,租了间小屋,做好了各种准备。然后又去找医生:
“我想改变面容的希望仍没有变,向公司也已递过辞呈了。”
“既然这么诚心,就给您想想办法吧。不过,以后您懊悔可就麻烦,所以请签写一份今后决不抱怨我们的保证书,并请预付手术费。这两件事您能答应吗?”
“当然。”
他上了手术台,注射了麻醉药,感到药性渐渐发挥作用,同时,不知不觉地告别了在他意识中逐渐模糊的往日生活。
终于他又听到了医生的声音:
“好,基本结束了。虽然不知能不能使您满意,但这毕竟是您的新面孔。”
他睁开眼,拿过镜子。头虽因残存的麻药药性而有些发晕。但往镜子里看时,到底得有番勇气。他不由得一阵激情遍布全身。不过,此时已无反顾余地了。
他瞅着镜中的自己,简直是另一个人——平庸之感已经消失,有的却是一副狰狞而有气魄的非凡仪表。
“这果真是我的面孔吗?”他点了点头,“也无所谓满意不满意了,反正我的希望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所以这样也蛮好。”大概声带也被动了手术,他的声音变得稍微低沉了些。
医生说道:
“请您再往几天医院,住到手术伤痕消失为止。”
“好的。”
他在病房里,看着镜子度日,看镜子对他来说,比看杂志、电视这些东西有趣多了。他有时还会出声试着和镜子里的人攀谈,于是才发现,若用以前那种符合于自己平庸生活的语调,已经与镜子里的形象不相适应了。
出院那天,医生问他:
“今后的生活,您计划……”
“我没什么计划。我正是因为对既定人生持有怀疑,所以才这样做的。”
“愿您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
他把医生这职业性的客套甩在身后,出院上街去了。这一天的时间他全部消磨干在街上东游西逛。仅止,也使他觉得够刺激的——自己能认识别人,却没人能认识自己。在街上和过去的同事擦肩而过,却丝毫没被他们注意,这时,他简直有一种销魂般的解放感。虽已黄昏来临,他却还想再享受一番这种滋味。
他试看来到一家过去常去的酒吧,这儿的女招待都把他当作初次光顾的客人对待,投以充满好奇和警戒的目光。他喝着酒,一面在心中暗自好笑,也颇想讲出自己的真实身分惊惊她们,但又想到那样一来,就又得返回从前的生活中了。
那是一种何等的快感呀,真想更好地乐一乐,闹一闹。他从这家酒吧喝到那家酒吧。独自举杯祝兴,祝贺他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新生之日。
他跑到不知第几家酒吧时已是醉醺醺的了。在那里他备受欢迎。吧女们都过来围在他身边,拼命地巴结,迎奉。他十分得意,对自己这张新面孔的自信力和亲切感也都涌上了心头。这家酒吧让他下次来时再付酒钱,他喜滋滋地连连点头,然后回他那事先准备下的小小居室去了。
睡熟后,梦中出现了他以前的生活,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对新生活习惯以后,大概就不会再梦见旧的生活了。
找工作的事似乎还可以再稍等等。第二天晚上,他又到了昨天去的那家酒吧,吧女们迎了上来:
“啊,今天又光临啦,沙罗!”
他想起了自己昨天晚上也被她们叫做“沙罗”,是怎么回事呀?大概是昨晚被她们问及姓名时,他就着醉意信口胡编出“三郎”这么个常见的名字,却又由于舌头打不过转来,于是便说成了“沙罗”。不过,这种事就随它去吧。他又象昨天一样地受宠,快快活活地喝酒,有些醉了。
喝着喝着,酒吧的门开了,进来一位顾客。这是个一眼看不出他职业的中年人。这家伙喜见我们的主人公,便走近来拍拍他的肩膀:
“喂,沙罗!你在这儿吗?美加想见见你呢。将她冷落在一旁,这可不太好吧。”
“这……”他除了这么回答,再也找不出话来。那家伙又说:
“去一趟吧!再说我正好有车,送送你!”
“那就去吧。”他的好奇心被引了起来,而且事情也渐渐有点明白了——大概自己长得象那个叫“沙罗”的家伙。他想更多地知道一些那个沙罗和美加的事情,想窥视一下与自己这张新面孔相适应的生活。
他被那人带去见到了美加。这是个大美人,独自住在高级公寓的一室。美加出来迎接,朝他莞尔一笑:
“啊!沙罗!好久不见了,正耽心你出了什么事呢。”
“哪儿的话,最近有点事情……”他含糊其辞地回答,并打量着这儿的情景。这是个豪华的房间,放着许多看来很昂贵的洋酒。美加请他喝酒——这真是个迷一般的女人。这也难怪,对他来说,这个女人当然是个迷咯。
这个女人始终没断微笑,却又不太说什么能使他借以了解情况的话。这也是很自然的——一既然和沙罗是老交情,当然就不会再重复讲那些事情了。
“不过,这个女人也并不了解我的真实身分。”他想到这,于是又沉醉于一种奇妙的兴奋之中。
过了一些时候,他声明告辞。美加说:
“啊,沙罗!上次你走时将上衣丢在这儿了。比起现在身上这件来,你还是穿原来那件合适。怪不得我觉得你今天不知怎的有点异样,再一想,原来是这个原因呀。”
美加从里间拿出上衣来给他穿上,居然意外地合身。刹时间,一阵异样的感觉从他的心中闪过。不过,照照镜子一看,确实是这件衣服与他的面孔很相称。
他身穿这件衣服,手提先前那件衣服回到住处,想想不知能不能找到什么关于“沙罗”此人的线索,使摸摸衣服口袋。衣袋里放着一个信封,打开来一看,是一捆大笔头的钞票。
“太奇怪了,这……”地瞪圆眼睛,自言自语道。这钱已不能再送回去了。若讲了实话,可能会被认为是捉弄人而挨骂的。唉,既然如此,还是让我随心所欲地用用这笔钱吧。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他屋里的电话铃响了。他刚要伸手去拿电话,想想又嘀咕道:
“真奇怪……”
确实是怪——自从变了面容以后,他从未将这个号码告诉过任何人。可是电话铃响个不停,也许是打错了吧。他拿起听筒放在耳边,传来一个老头的声音:
“喂,是沙罗吗?”
“啊……。他一边回答,一边有点发怵——人家怎么知道这儿的?是我昨天晚上回来路上被什么人盯梢了吗?这个老头到底是谁,这声音从来没听见过,如果他是真的沙罗,那就立刻真相大白了。
对方并不理会他这时的心情,说道:
“喂,沙罗!你想躲起来,我能理解,可是连联络地址都不肯诉我一声,这可叫我不好办呀!”
“啊,对不起!”
“那么下次再联系。你得当心点!”说完挂了电话。
他渐渐不安起来——自己好象正在被卷进什么不明不白的事情中去,不,是已经卷了进去。沙罗到底是什么人?真正的沙罗到底怎么了?这一切,现在还都是个谜。
他又仔细检查了衣服。可是除了装有钞票的信封外,没发现任何线索。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翻来覆去地摆弄这件衣服消磨时间。
到了晚上,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先前那个老头的声音:
“喂,沙罗,你待在那里有危险,快走出你的房间,明天天亮以前别回去!”
“啊……”
情况紧急,似乎已容不得他再问问清楚。他奔出住处,在一家小西餐馆吃了饭,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转了一夜。他边走边思索,可是只觉得自己如堕入浓雾之中,甚至都不知自己怎么想的,想些什么。
他既觉恐怖,却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到了早晨,提心吊胆地回去一看,屋里零乱不堪,好象有谁来找过什么而又一无所获,于是便在这里糟塌了一番借以泄愤。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也许是来找沙罗本人,也就是说来找我的。如果我不出去,也许会被抓住。那以后会怎样呢?有可能硬被他们带走,被逼着招供。那时我说什么好呢?即使咬定自己不是“沙罗”,他们也不会相信的。若想顺从他们,以求宽宥,却又毫无交代的材料。于是,最后结果也许是拷问……
想到这儿他心中好一阵哀愁。
象是与此呼应,电话铃又响了,还是那个老头的声音:
“呀,沙罗:祝贺你平安无事!目前已无危险,你不用耽心了。”
“啊……”
“钱已送到了,你看看信箱!去好好散散心吧!”
电话就这样结束了。信箱里又放着装有一扎钞票的信封。他并不太感到庆幸——没人会心血来潮而送钱给别人的。也许最近又会有指令来,到底会叫他干什么呢?
思路朝着令人不快的方向发展,与之同时,他难以抑止地怀念起以前的生活来。那虽然平庸,却也因而样样都有条有理。
出门后,他的脚步不知不觉地朝向了自己以前的家,并在他家附近遇到了象是买东西刚回来的妻子。他条件反射似地打了声招呼:
“啊……”
“什么事?”
妻子回过头来时那冷漠而困惑的神情使他重新意识到自己已非以前的自己了。越是做出亲近的样子来,恐怕越是会给妻子造成不正常的印象的。于是他说:
“我是您丈夫的朋友……”
“啊,是吗?我一点也不认识呀;以前见过吗?”
“我可认识您。您丈夫现在……”
“现在去公司上班了,但大概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上咱们家等等吧……”
“什么……”他差点叫了出来——是谁“会回来的”呀?
“您的样子为什么好象很意外听,是不是以为他出差了?其实没那事儿——早晨出门时,他还说今天和平时一个时辰回家呢。”
“是吗?您丈夫身体好吗?还跟以前一样吧?”
“唉,托您福,他很好。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最近他又换了一家公司上班。那家公司并不比原来的强,所以他在那里也不怎么样,不过,倒用原来公司给的退职金买了衣服什么的穿了回来。他大概是心血来潮吧。不过我们家也仍旧是平平凡凡的……”妻子说着笑了笑。
听了这话,他心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仍旧是平平凡凡的”这话令他苦笑。同时,他急于想知道成为自己妻子的主人的那家伙到底是何许人也。这种欲望使他觉得自已站都站不稳了。妻子可并没理会他此时的心情,问道:
“……那么,请教大名……”
“我叫沙罗,您丈夫最近没提过这名字吗?”他反问道,并期待着反应。
“这名字真怪。我从没听说过。”
看来妻子不是撒谎。他支吾了几句便走开了。
他回到住处,使自己定下心来。越是想理出个头绪来,却越是不得其解。自己离家以后,到底从哪儿跑出个什么家伙来混充自己的?真想剥下那家伙的画皮看看。可是,自己已没权利教训他了,而且现在的自己还……
“喂,沙罗!已经决定了。一星期后动手,你做好准备!知道了吗?”
“啊……”
事到如今,他已进退维谷,想不到变了面容会造成这种结果。他曾懂憬过自己的真实面目不被任何入发现时的情景,可是现实却和想象的相反。现在他的周围有许多家伙都认识他——“沙罗”,可是他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
这天晚上,他用手头的钱痛痛快快地喝了一番,可是心里却一点都不好受。对以前生活的依恋之情一个劲儿地涌了上来。睡着以后又做恶梦,即使天亮醒了,也如同自己仍在恶梦中一样。他真想从这种状态中脱身,无论如何也得回到原来的世界中去,可是又怎么做是好呢……
回头之路看来只有一条。他第二次去找整形外科医生:
“讲起来真不好意思,可还得求求您,让我恢复原来的面容吧。”
“这张脸没给您带来好处吗?”
“哪来的什么好处,可让我陷进泥沼里去了……”
“什么,是我坑了您吗?您要这么说,我可就不管您啦!”
“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再这样下去可就难办了,很可能会更倒霉的。”
听了他的央求,医生说:
“可是,要恢复原来的面容可不容易呀。其实只要改成和现在不一样的别的面孔,不就行了吗?”
“还是原来的面孔好,我可不想再冒险了。那副平平常常的样子就蛮好。不能替我想想办法吗?”
“您既然说到这个地步,我也就不能不替您办了。请再等一个星期吧。”
“我实在等不了这么长时间,请稍再快点吧!”
“可是已有预约好的人在排队了,要是打乱秩序可就……”
“想想办法吧……”
“那就五天后做吧,不能再提前了。您若不愿意,那就……”
“不,这就行了。那么五天后一定来麻烦您。”他叮咛了好几遍才回去。
这五天他是提心吊胆地过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电话铃响了,通知他提前行劫,那可就推不掉了。虽不知会被吩咐干什么,但总不会顺手的,他将陷于最坏的境地。
他也曾想从屋里逃出去,但也许有人在什么地方监视着他,即使没受监视,他也不知在哪儿逃才安全。这个问题只有真正的沙罗才知道。
他连气也不敢大喘,心里不断地暗暗祈祷,就这样总算过了五天,于是又到整形外科医院,上了麻药,开始了手术。
从麻醉中醒来后,他知道又恢复了自己以前的面孔。医生问他:
“满意了吧?”
“是的。”
“刚才忘记了,请您在对手术不会反悔的保证书上签字,并请付手术费。”
“是。”
他等伤疤长好便出了院,并朝自己的家走去,却又犹豫起能不能回家了:
“冒充我的家伙会采取什么态度呢?不,没必要耽心这个。我是名正言顺的家主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他赶出去。必要时还得让他尝尝厉害……”
他气势轩昂地闯进家里,妻子迎了上来:
“呵,您回来啦?又换了衣服吗?您怎么啦,这么气喘吁吁的……”
迎接他的神态还是跟以前一样,可是他仍然放不下心来,因为想到那人可能马上就会到来而一直紧张得惶惶然。妻子问道:
“马上会有谁来吗?”
“不……”
到了晚上,仍没有任何人来。这一夜他都没能入睡,既难相信自己已经恢复了从前的状态,又怀疑那个在这里冒充自己的家伙上哪儿去了。
各种各样的想法在他头脑中流动,最后形成了漩涡,变成了一种假设:
“难道我被那个医生骗了?难道他没给我做手术?是不是他使麻醉药性不断,并用暗示的方法使我一直做着恶梦。我被他用这方法……”
“若是这样,就被医生骗去了两次的手术费。要去找他吧,可自己已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也没办法再怪罪人家,对于医生来说,这可是个好买卖。也许他将手术费分了一部分给我妻子做回扣,跟她事先做好手脚,让她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来迎我。”
他还在不断地苦苦思索。可是,疑问的旋涡又形成了另一个假设:
“也许确实是做了手术,但也中了那个医生的谋算。他巧妙地将我打扮成‘沙罗’这个子虚乌有的人物,牵着我的鼻子走,也许是要利用我为他做什么坏事。
“不,不!也许事情真相还要复杂得多,沙罗以及那个趁我不在家时冒充我的家伙都是真正存在的人物。”
“那个名叫沙罗的家伙不愿再干危险的行当,想要脱身,为了使自己的计划更完善;便跑到哪一家整形外科医院,请他们将他的面孔改成一种别的随便什么样子。虽说是‘随便什么样子’,可是到底怎么改法,医生却一时想不出个什么形象来。再也没有比‘随便什么样子’这种要求更使人为难的了。有个具体的模样倒反而好办。如果在这方面有个联络部门,那可以方便地取得自己需要的面容了。也就
是说,有这么一种面孔交流中心,一些人不要了的面孔可以在这里找到愿意利用它的主顾。现在是物质、金钱、情报的流通性都愈加提高的时代,面孔又何以能唯独例外呢。
“在接受申请后的数日内,便达成与其他适当面孔进行的交换,接受并完成手术。我被强加上了沙罗——一那家伙的面孔。而沙罗这时想必也接受了什么人的面孔,正在一个什么地方呢。继我之后被安上沙罗面孔的人则大概正不由分说地吃着苦头吧。真不愿相信,难道这就是我所拼命追求的生活吗?
“我不在家时冒充我的家伙后来则被说明缘由而换上了另一副面孔,给我让出了位置。这真象把人当七巧板游戏玩,一会儿填在这里,一会儿嵌在那里……”
各种假设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他却不想去逐个做一番查证。虽然要想查证也许就能真相大白,可是不管如何明白真相,到头来也只能落得个心中不快。
他重新去找工作,又开始过起了平凡的生活。不过,生活的外表虽然一般,空闲时浮现在头脑中的回忆可决不平凡。
(译自新潮社1980年版星 新一著《歧途多端》)
慈心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