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祖有取天下的雄心,而又不惜孤注一掷。萧、曹文吏,虽有兴邦佐国之才,而畏首畏尾,不敢冒险,只能因人成事。唐僧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其有取经的雄心,谁都不能否认。然要实现雄心,必须克服艰难,这个艰难是现实的,而非念念《多心经》(第十九回),就可了事。换言之,须有具体的实力,绝非抽象的观念所能解决。佛门弟子本以慈悲为怀。唐僧敬重三宝,富贵不能动其心,威武不能屈其志,只因有了好“善”之心,却延搁了许多前程。韩非说:“好恶见,则下有因,而人主惑矣。”(《韩非子》第三十四篇《外储说右上》)妖魔“因”唐僧向善之心,遂设圈套,使唐僧坠入其中,而不之觉。“尸魔三戏唐三藏”(第二十七回),孙行者谓其“一心向善”,故有此灾(第三十二回)。银角大王说:“我看见那唐僧,只可善图,不可恶取。若要倚势吃他,闻也不得一闻,只可以善去感他,赚得他心与我心相合,却就善中取计,可以图之。”(第三十三回)红孩儿说:“若要倚势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却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在我善中生机,断然拿了。”(第四十回)对这妖精圈套,孙行者劝告唐僧:“师父,今日且把这慈悲心收起,待过了此岛,再发慈悲吧!”(同上)姹女求阳之时,孙行者又警告唐僧:“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药医。”(第八十回)一路遇到魔障,而均为“善”所迷,中了妖精圈套。商鞅说:“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商子》第十四篇《修权》)韩非说:“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智去旧,臣乃自备。”(《韩非子》第五篇《主道》)昔者,燕王子哙好名,欲为尧舜,而以子之为贤,让之以国,遂致齐师来伐,兵败身死,此人主好名,人臣饰贤以要其君之例也。汉代取士有选举之制,所谓选举是乡举里选,采毁誉于众多之论。但是一般民众哪里有评判的能力,因之核论乡党人物,就有待于当地的名流,汝南月旦评可以视为一例(《后汉书》卷九十八《许劭传》)。凡人能够得到名流赏识,无不身价十倍,如登龙门(《后汉书》卷九十七《李膺传》)。一般士子遂矫饰其行,以邀名流青睐。至其末造,沽名钓誉乃成风俗。举一例说:
许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后汉书》卷一百六《许荆传》)
既自污以显弟,复剖陈以自显,一举而兄弟皆贵,盗名窃位于兹为甚。此亦朝廷尚贤之过也。所以韩非又说:“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韩非子》第六篇《有度》)妖魔之于唐僧,固曾多方诱之,而皆不能动其心,最后诱之以善,唐僧果然坠入圈套。此即韩非所谓“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韩非子》第七篇《二柄》)之意。
更进一步观之,古来政治上成功的人往往不讲小节,有时他的行为且与“善”字相反。贾谊说:“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贾子新书》卷一《益壤》)齐桓公多内宠而霸,宋襄公行仁义而亡,这是读史者共知的事。楚汉相争之际,项羽大破汉军于彭城,汉王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坠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夏侯婴)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参阅卷九十五《夏侯婴传》及《汉书》卷四十一《夏侯婴传》)。这固然是“为天下者不顾家”,然而跋下两儿乃欲减轻载量,以便自己逃命,其忍心害理,完全为私,而非为公。诸吕作乱,太尉周勃之功最伟,而文帝即位之日,即夜拜宋昌(由代国带来的亲信)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借以牵制太尉周勃。俄而又徙周勃为丞相。不久,又免丞相勃,遣就国(《汉书》卷四《文帝纪》、卷四十《周勃传》),盖国有威可震王之臣,非国家之福。七国之乱,周亚夫之功最大,其结果如何。景帝说:“此鞅鞅,非少主臣也”,遂乘其子买甲盾以为葬器之时,逮亚夫入狱。此际狱吏与亚夫之对话,真是无理极了。
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亚夫不食,五日呕血而死。(《汉书》卷四十《周亚夫传》)
至于武帝之杀钩弋夫人(赵倢伃),更出于深谋远虑。
钩弋夫人之子弗陵(昭帝),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尔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后元元年)
即东汉母后临朝之祸,武帝早已看到,故欲立其子,先去其母,其忍心害理是为公而非为私。政治上的是非与伦理上的善恶有时未必一致。父仇不共戴天,而禹乃佐舜治水。兄弟应该友爱,而周公竟杀管、蔡。徒“善”不足以为政,小善只足以误国。孙行者“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吃尽千辛万苦”(第二十七回),积了许多经验,而后劝告唐僧收起善心。取经尚且如此,何况治国平天下!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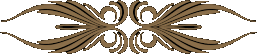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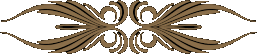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