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梦想照进现实
作者:陈鲁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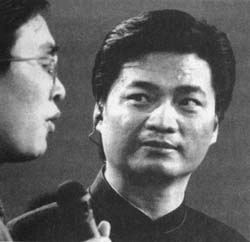
“我有个想法。”这是我的开场白。
“你说。”郭志成并不看我,只是忙忙叨叨地摆弄着面前摊成一片的手机、香烟、打火机、车钥匙。我喝了口奶昔,等他整理妥当,才慢悠悠说出我近十年的梦想。
“好事,可做!”老郭仍是他一贯不紧不慢的风格,腾出右手推推镜片,若有所思地望向我的身后。
“有个投资公司愿意出钱,可他们胆小,一开始希望每周一期,我兴趣不大。一来,我还是想在凤凰做这个节目,毕竟我是凤凰的人嘛。再说,每周一期,那我自己出钱都能做,还找他们干什么呀?”我不屑地撇着嘴,心里想着那个缺乏勇气和远见的公司自有他们后悔的那一天。
老郭嘿嘿笑了一下。
“你说我是该做每周一期呢还是豁出去了每天一期?”我终于说出了内心的犹豫。不是我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我无法确定每天做一档时长一小时带几百名观众的访谈节目需要多大的工作量。我不是工作狂,我可不希望每天奔命似的干活。
“当然做日播的了。”老郭的回答斩钉截铁。
“凤凰会给我投这么多钱吗?”我平常在生活中工作中从不管钱,倒不是故作风雅,实在是在数字方面我是个白痴。我深知自己的弱点,也颇懂得扬长避短的道理,索性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做个甩手掌柜。可再不食人间烟火,我也能掰着手指头算明白这个账——《鲁豫有约》的投资绝对是以千万来计算的。
“前期投入没你想象的那么多,有几百万就能周转过来。但播出平台必须扩大,我想,除了凤凰以外,还在内地各电视台播出。”郭志成说话依然慢悠悠的,我听来却是心潮起伏。
“公司会同意吗?”短暂的兴奋之后,我又面露愁云。有时,我实在是个悲观主义者。
“为什么不同意呢?这事对你对节目对公司都有好处啊!”郭志成开始兴致勃勃地展望新节目的美好未来以及由此给我带来的事业腾飞,我被他说得双颊绯红,心潮澎湃。
在金湖门口挥手道别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不远处的长安街上塞满了回家的车流。我深吸一口微甜的空气(这可不是抒情的写作手法,旁边就是哈根达斯),心中满溢着幸福的感觉。
接下来的筹备工作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这期间没什么跌宕起伏离奇曲折的情节,无外乎是说服公司管理层接受我的想法,租借办公场地和招兵买马之类,在此忽略不谈。
2004年6月12日,我和郭志成以及《鲁豫有约》的主创人员共进晚餐,席间,由郭志成向大家宣布了节目的改版计划。看得出,大家有些吃惊,但更多的是兴奋。身为电视人,谁都想做一个有影响力有长远发展的节目,他们眼中那一刻闪现出的光芒更增添了我的信心。很巧,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十一长假一过,我们在凤凰会馆2楼租下了两间办公室,稍稍粉刷清洁之后,就搬进桌椅电脑开始工作了。
很快,两大间办公室里就坐满了人。每次我出出进进,都看见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从电脑屏幕后探出来,怯生生地叫我“鲁豫姐”。他们的眼神总是让我的心温柔地颤动一下,好像又看到了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自己。
身边的同事朋友和媒体都知道了我要做一个“奥普拉式的日播访谈节目”,于是见到我的每个人都流露出无比的温柔和关切,那一个个柔情似水又充满担忧的眼神里写满了疑问。一直到今天,在我写这篇文章的2006年夏天,每一个和我久未见面的朋友仍然用怜惜的语气和我打招呼:“你一定辛苦死了!每天要做那么多的节目!”
一开始我乐得全天下人都以为我每天为工作殚精竭虑,尤其在公司管理层面前,我总是半玩笑半认真地点头:“就是就是,我累得要死!”可等了又等,老板也没有要给我涨工资的意思,我干脆就实话实说了:“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可再看同事们,眼泪几乎在眼眶里打转了,我这才明白,有时否定就是最大的肯定。
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法让人相信,我在轻松愉快地做着《鲁豫有约》。
“东方奥普拉”,是在夸奖我吗?
我在这篇文章里多处提到奥普拉,所以上网goo了她一gle,赫然发现我的名字夹杂其中,名字后面一定有个破折号,外加那几个耸人听闻的字:东方奥普拉!哎,他们这是夸我吗?就连CNN记者采访我,也问了个“你被称做东方的奥普拉,你对此怎么看?”的问题,我还能怎么看,既不能做欣喜若狂状有失体统,也不能不解风情地回绝别人的好意,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半天终于说了句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最爱说的话:“我就是我!”废话!
我的团队倒是常常以奥普拉的标准要求我:
“奥普拉出的杂志《O》,每期封面都是她,火得一塌糊涂。我们也该出一本。”
“奥普拉的节目去年20周年,她在一期特别节目中送给现场200名观众每人一辆轿车。”
“奥普拉又要出一本食谱啦。”
“奥普拉还跑马拉松哎!”
以上种种令我备感压力。反正马拉松我是绝对不跑的,至于其他方面,我,努努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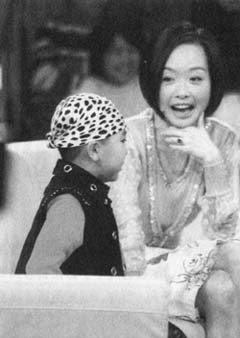
就在众人支持反对信任怀疑纷繁复杂的注视下,专为制作《鲁豫有约》而成立的能量公司也新鲜出炉了。能量这两个字总让我想到劲霸广告里那个四处乱撞精力无限的电池小子,而我,倒挺像那紧绷双臂怒目圆睁的卡通人。
办公室里来来往往的编导有大半的面孔是陌生的,我还叫不上名字。偶尔我从办公桌上抬起头,透过敞开的门望出去,能看到他们忙忙碌碌地查资料、打电话、写文案。这时我总会困惑地眯起眼睛,努力回想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会有些小小的得意,而更多的是恍然大悟后的郁闷:“这么多的人在忙同一件事,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随随便便地说退出江湖这类的话了。”
当然,人就是江湖,哪里退得出去呢。
一直以来,我只是专注而自我地当我的主持人,别的,一概不管也一窍不通。我不知道做一期节目要花多少钱,搞不懂录像用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磁带有什么区别,还有编辑机房里一排排的机器,鬼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的。有一阵常常听到媒体鼓励主持人要兼具“采编播”等各项技能,吓得我一阵阵出冷汗,不明白会摆弄编辑机上一个个按钮和当好主持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只想涂上淡红的唇彩、换上服装,当灯光亮起的时候走上我的舞台,其他的,交给我的同事去担当吧。
而2005年1月1日,新版《鲁豫有约》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内地20多家省级电视台同时播出后,我就一点点地发生着改变。
每天节目一播完,片尾字幕还在走着呢,我的制片人无论在哪,一定拿起手机贴向耳边,等着我的夺命追魂call准时响起。每次连寒暄都没有,我总是气急败坏地直奔主题:今天灯光不好,我的眼影太深,观众大笑时镜头为什么不切过去,他成名前的那段经历很好听为什么删掉了,他获奖的故事讲过无数遍了为什么还留下,字幕里又有两个错字……节目中每一处疏漏在我眼中都被无限扩大,这让我无法容忍。樊庆元当时是节目的制片人,有一次上午十一点他正召集所有主编开会,这正是《鲁豫有约》在凤凰首播结束的时间。樊庆元看看表,冲大家做个安静的手势,然后缓缓从桌上拿起他的手机,把显示屏举向众人,嘴里念念有词地数着三二一,就是那么巧,电话在他倒数结束的一瞬间响起,大家凑上去看见屏幕上赫然两个字鲁豫,不由哄堂大笑。樊庆元接通电话也笑着说:“你真行啊,一秒钟都不差!”
偶尔我也会放过制片人,直接折磨编导。我能想象,节目播完,编导的手机响起,屏幕上一闪一闪地竟是我的名字,他们的内心一定惊恐万分吧。
有一天编导李安负责的节目刚刚播完,我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李安还在梦中,冷不丁被铃声吵醒有点蒙,可一看来电显示着我的名字,他一下子清醒了,先是有些慌,既而兴奋地想:“今天是我的生日啊,鲁豫姐来电话一定是祝我生日快乐的!”于是我听到听筒那头传来李安睡意未消但愉快的声音:“鲁豫姐早!”早字刚说完,李安的嘴大概还没闭拢呢,我劈头盖脸一通狂轰滥炸指出节目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然我的语气尽管有些严厉,可还算有理有利有节,只不过在刚刚被铃声吵醒的人听来,简直有如晴天霹雳。李安不知所措,只好沉默不语。我是个刀子(橡皮做的)嘴豆腐(不是冻豆腐而是南方那种最软的豆腐)心的人,听那边完全没了声音,感觉很是不忍,于是一个劲地鼓励李安:“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做得还不错!”简直就是废话,做得不错还批评人家?几天后,从主编雷蕾那我才知道了李安生日的事情,这让我愧疚了很久。
我还有一位主编叫肖矢,每每我们夸奖他把组里的工作管得井井有条,他总是面露矜持的微笑,然后慢悠悠地说:“这就叫管理的艺术。”
他的话虽然半是玩笑,但却给我很深的触动。我开始认真考虑长江商学院项兵院长的邀请,去长江读EMBA。
2005年11月,我成了长江商学院第7期EMBA秋季班的学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每个月有四天,我要一大早睡眼惺忪拎着电脑赶到北京东方广场去上课。我们的课程光听名字就让人肃然起敬,什么高级理财学、管理会计、统计与决策、生产与运营管理、商法概论。每每坐在课堂上,翻着面前厚厚的讲义,看看身边个个企业老总或高管的同学,恍惚中我好像也统领着千军万马的队伍驰骋在商场上似的。我于是得意地给我的朋友高雁发短信:“我们正讨论GM所使用的六sigma战略呢。高深吧,崇拜我吗?”
很快短信回来:“sigma是什么?手表吗?GM还做手表?比Cartier好吗?你认识GM的人那可以打折吧?”
你看看,上不上EMBA的差距有多大啊!
文章写到这里要暂告一段落,因为,我所描述的一切是正在进行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