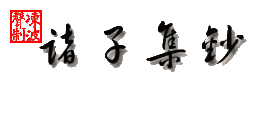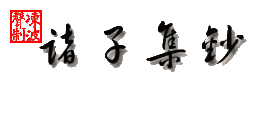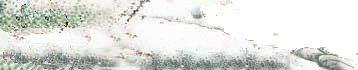論衡是中國哲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自從董仲舒治公羊,明天人相感之說,以為天是有意志的,與人的意識相感應。大小夏侯、眭孟、京房、翼奉、李尋、劉向等都推演其說。儒家到了此時,內部起了質的變化,披著巫祝圖讖的外衣,把天說得太神秘,太聰明,人的行動,是要受他的裁判,這就是一班漢儒所說的陰陽災異的理論。
這種荒謬的迷信的理論,把儒家改裝成為帶有宗教性的儒教,自漢武帝時起到光武時止,一直支持了一百多年,才能有小小的反動:即鄭興、尹敏、桓譚一班人。但他們只知道攻擊圖讖的荒謬,對這些儒教徒所持天人感應說的原理,還不能根本上擊破,或者還相信這原理。到了仲任,才大膽的有計畫的作正式的攻擊,用道家的自然主義攻擊這儒教的天人感應說,使中古哲學史上揭開一大波瀾。
論衡全書就是披露這天人感應說的妄誕。用自然主義為其理論的出發點。現在把論衡全書,就他的思想體系,列為六組:
第一組是說性命的。
甲、性命說所依據的理論:
物勢十四。
乙、說性的:
本性十三。率性八。
丙、說命的:
初稟十二。無形七。偶會十。命祿三。氣壽四。命義六。逢遇一。累害二。幸偶五。吉驗六。
丁、性和命在骨體上的表徵:
骨相十一。
〔注〕物勢篇說:“天地合氣,人偶自生。” 此為仲任以性命定于初稟自然之氣(初稟篇語。)所據之理。骨相篇說:“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是仲任的意思:性命稟于自然,現於骨法。各篇排列的順序,不依原書目次,是以其理論的體系之先後為據。
第二組是說天人的關係。
甲、天人關係說所依據的理論:
自然五四。
乙、評當時儒家陰陽災異天人感應諸說違天道自然之義:
寒溫四一。譴告四二。變動四三。招致四四。闕。感類五五。
丙、論當時災異變動:
明雩四五。順鼓四六。亂龍四七。遭虎四八。商蟲四九。
丁、論當時瑞應:
治期五三。齊世五六。講瑞五十。指瑞五一。是應五二。宣漢五七。恢國五八。驗符五九。須頌六十。佚文六一。
〔注〕仲任說災變符瑞,以“適偶”代替“感應”,以自然主義為宗。
第三組論人鬼關係及當時禁忌。
甲、論人鬼關係:
論死六二。死偽六二。紀妖六四。訂鬼六五。言毒六六。薄葬六七。祀義七六。祭意七七。
乙、論當時禁忌:
四諱六八。□時六九。譏日七十。蔔筮七一。辨祟七二。難歲七三。詰術七四。解除七五。
〔注〕人稟天地自然之氣,偶適而生,(見物勢、初稟、無形等篇。)人死則精氣滅,(論死篇語。)故人死不能為鬼。無鬼,則祭祀只緣生事死而已,無歆享之義。(祀義、祭意篇語。)吉凶禍福,皆遭適偶然,(偶會篇語。)故不信一切禁忌。
第四組論書傳中關於感應之說違自然之義和虛妄之言。
甲、評書傳中關於天人感應說的:
變虛十七。異虛十八。感虛十九。福虛二十。禍虛二一。龍虛二二。雷虛二三。
乙、評書傳中虛妄之言:
奇怪十五。書虛十六。道虛二四。語增二五。儒增二六。藝增二七。問孔二八。非韓二九。刺孟三十。談天三一。說日三二。實知七八。知實七九。定賢八十。正說八一。書解八二。案書八三。
第五組是程量賢佞才知的。
答佞三三。程材三四。量知三五。謝短三六。效力三七。別通三八。超奇三九。狀留四十。
第六組當作自序和自傳的。
對作八四。自紀八五。
這八十五篇書,今缺招致一篇。反復詰辯,不離其宗,真是一部有體系的著作。可惜這部大著,宋以後的人就忽略它了。
從漢到現在,大家對於這部書的認識,可以分作三期:
一、從漢到唐 如謝夷吾、蔡邕、王朗、虞翻、抱朴子、劉知幾等,都認為是一代的偉著。詳後舊評。
二、宋 帶著道學的習氣,認為論衡是一部離經叛道的書。如晁公武、高似孫、陳振孫、王應麟、葛勝仲、呂南公、黃震等是。詳後舊評。
三、明、清 取其辯博,但對於問孔、刺孟仍沿宋人成見,罵他是非聖無法。如熊伯龍、無何集。沈云楫、虞淳熙、閻光表、施莊、劉光鬥、傅嚴、見後舊序。劉熙載、陳鱣、周廣業、章太炎先生見後舊評。都是極力表張此書。四庫全書目錄提要、幹隆讀論衡跋、譚宗浚、王鳴盛、梁玉繩等見後舊評。 皆詆訾此書,或毀譽參半。
對論衡有真正的認識,還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因為諸子是研究思想史的寶藏,研究諸子的興趣,不減于經史。治諸子的人,盡革前儒一孔之見,實事求是,作體系的歷史的探討。不因為他問了孔子,刺了孟子,就減輕他的價值。或者在現代人看來,還要增高他的價值。
四庫全書目錄和劉盼遂先生據自紀篇以為論衡當在百篇以外。見後版本卷帙考。近人張右源據佚文篇云“論衡篇以十數”,疑原本論衡的篇數沒有今本這樣多,認為今本是混合其所著譏俗節義、政務、養性三書而成。(見東南大學國學叢刊二卷三期。)其說非也。佚文篇“十數”為“百數”之誤。我以為仲任的手定稿,或者有百篇,但抱樸子、見後舊評。後漢書本傳都只著錄八十五篇,蓋論衡最初傳世,是由蔡邕、王朗兩人,據抱朴子、袁山松書。見後舊評。他兩人入吳,都得著百篇全稿。虞翻說:“王充著書垂藻,絡繹百篇。”足為當時尚存百篇之證。後來因為蔡邕所得者,被人捉取數卷持去,據抱樸子。故只剩八十五篇。見存的論衡,大概就是根源于蔡邕所存的殘本, 史通鑒識篇:“若論衡之未遇伯喈,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所以葛洪、範曄都只能見到八十五篇。劉盼遂先生所引類書中佚文,似乎都只是八十五篇的佚文,未必在八十五篇之外。因為唐、宋人所見的不能超出范曄、葛洪之外。
自從後漢書著錄八十五篇之後,只缺招致一篇。至於各篇的先後排列,大致保存本來面目。據今本各篇的排列與全書理論的體系,及篇中所載的史事的先後,並相符合,可以為證。那麼,這部書傳到現在,好像是沒有經過後人的改編。
未經後人改編,固然保存當時篇章排列順次的本來面目,但流傳到現在一千多年,還沒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釋。近人劉盼遂論衡集解,有自序見古史辯第四集,全書惜未經見。其說見采入者,皆據古史辯。劉叔雅先生三余劄記二論衡斠補云:“校理論衡既畢,付之剞厥,刻垂成矣。”曾面詢之,據云:“全稿存在安慶。”故未獲睹。楊樹達云:“曾校注數卷,以事中輟。”章士釗云:“有意整理箋釋。”(見甲寅週刊一卷四十期四十一期。)梁玉繩認為論衡有注,乃是誤說。瞥記一云:“禮記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孫奕示兒編謂王充論衡注云:‘出易緯之文。'”按示兒編一云:“經解引易曰:‘差若豪厘,繆以千里。'乃出易緯之文也。”自注云:“王充論注,詳見‘豪厘'。”卷四“豪厘”條云:“按王充論注,乃易緯之文。”徐鯤曰:“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論章懷注引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此省文作‘王充論注'。”據此,則梁氏謂出於論衡注,非也。孫蜀丞先生也認為有舊注,見亂龍篇、卷十六,頁六九五。指瑞篇、卷十七,頁七四八。死偽篇。卷二十一,頁八九五。但據我的意見,前兩者乃是正文,後者乃是兩本異文誤合,不是注語。說具本篇。御覽引舊音一,別通篇卷十三,頁五九一。舊注五。逢遇篇卷一,頁七。儒增篇卷八,頁三六五。變動篇卷十五,頁六五0。亂龍篇卷十六,頁七0二。是應篇卷十七,頁七六三。篇中衍文,推知其為舊校者二,儒增篇卷八,頁三七六。藝增篇卷八,頁三九一。似出於舊注者十七。命義篇卷二,頁五二。吉驗篇卷二,頁九五,又九六。骨相篇卷三,頁一二三。本性篇卷三,頁一三五。物勢篇卷三,頁一五二。書虛篇卷四,頁一八三。道虛篇卷七,頁三二九。儒增篇卷八,頁三七六。刺孟篇卷十,頁四六六。說日篇卷十一,頁五0四。答佞篇卷十一,頁五一九。效力篇卷十三,頁五八二。亂龍篇卷十六,頁六九四。自然篇卷十八,頁七八一。感類篇卷十八,頁七九七。紀妖篇卷二十二,頁九二九。但這些,我都疑為是讀者隨手旁注,不像是出於正式的注文。理由是:若是曾經有人正式的注釋過,不當把許多需要注釋的地方都抹殺去,反來注這些不經意的地方,甚至於不須注的。
宋仁宗慶曆五年,楊文昌刻本序說:“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現在的各本,都根源于楊刻本。那麼,今本校語,是出自宋楊文昌之手。在楊校之後,輾轉刊行,當又加添不少的校語。如問孔篇卷九第四一一頁。“子曰予所鄙者”,“鄙”下舊校曰:“一作否。”宋、元本並無此三字,則此注語當出自明人。但這班翻刻古書的人,不都是通人,不見得備具校勘董理的學力和方法。如無形篇卷二第六一頁。“化為黃能”,舊校曰“能音奴來反 ”,朱校元本同。及上面所引問孔篇的校語“鄙”一作“否”,都是顯著的訛誤。說見本篇。
清儒,尤其是幹、嘉時代,校勘古書是一代的偉跡。但對於論衡,如盧文弨、王念孫等,都是手校群書二三十種的人,而沒有一及此書。莫友芝說:“抱經有校宋本。”未見。因為他們只把論衡當作一種治漢儒今古文說的材料看。俞樾雖然是校正數十條,想是以餘力致此,所以不像所校他書那樣精當。孫詒讓、孫蜀丞先生對這部書,用力比較多些,諟正若干條,才使這部書稍稍可讀。
我整理這部書,把校勘和解釋分成兩部工作。在校的方面,因為流傳的善本不多,連類書的援引及見於他書的地方也很稀少。在釋的方面,因為此書用事沉晦,好多是不經見的故實,加以今古文說的糾紛--這兩方面,都使我經過相當的困難,感覺學力的更貧乏。
論衡的版本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元刊明正德補修本,累害篇不缺一頁,是由慶曆本、幹道本、至元本直傳下來的。一個是由成化本到通津本,到程、何諸本所構成的系統,從成化本起,累害篇並缺一頁。參看論衡版本卷帙考列表於次:
宋慶曆五年 宋幹道三年 元至元七年 元刊明正德修本
┌─→ ──→ ─ ─→
楊文昌刻本│ 洪適刻本 宋文瓚刻本 (累害篇不缺)(1 )
│
│
│ ┌ 程本
│ │ 何本
│ 宋光宗時刻本 宋刊明成化 嘉靖時通津 │ 錢本
└─→ ──→修本(累害 ┌─→ ├ 黃本
(二十五卷)(2 )篇脫一頁) │ 草堂刻本 │ 鄭本
│ │ 王本
│ └ 崇文本
│
│
│ 天啟六年
└─→劉光鬥刻本(3 )
〔注〕一。葉德輝說,正德本累害篇脫一頁,不對。
二。宋光宗時刻本二十五卷,見存日本,疑是根源慶曆本。
三。天啟本的序說,據楊文昌本刻。我想不是直接依據。因為天啟本也脫去累害篇一頁。明正德補修本是楊文昌本的四傳的本子,還沒有脫此一頁,則知其所謂據楊本,不足信。疑出自成化補修本。
我所用的本子,是以通津本作底本。所見宋本,只是十四卷到十七卷的殘卷。其餘的所謂宋、元本,都是借用別人的校錄。其中以朱宗萊校元本為最精詳,楊守敬校宋本太粗疏。我想,一定忽略了一些好的材料。
胡適之先生在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序上說:
校勘之學,無處不靠善本:必須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謬誤;必須依據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謬誤;必須有古本的依據,方才可以證實所改的是非。……王念孫、段玉裁用他們過人的天才與功力,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種推理的校勘學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可以補版本的不足,但校讎的本義在於用本子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精力於推敲,終不是校勘學的正軌。……推理的校勘,不過是校勘學的一個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終甚微細。
當然,版本是作校勘的唯一的憑依。但是論衡這部書所保存的善本是這樣少,要整理這部書,只靠版本是不夠的。勢必於版本之外,另找方法,即取證於本書、他書、類書、古書注的四種方法。
孫詒讓在他的劄移序上說:
其諟正文字訛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音通轉為其錧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
本書、它籍、類書,這是揭舉校勘學在離開版本的憑藉時的三大途徑。陳援庵垣。先生元典章校補釋例說得更詳細。他舉出校法有四:
一。對校法 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
二。本校法 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
三。他校法 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
四。理校法 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
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
第一種對校法,是用兩本相比,是最容易的工作。只要有相當的學力,就能判斷“某本作某是對的”。第二種本校法,即孫氏所謂求之於本書。第三種他校法,即孫氏所謂旁證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有時憑據他書注的引用,也屬於此法。第四種理校法,即胡先生所謂推理的校勘。
在沒有古本憑依的時候,想對於某一部書,發現它的謬誤,改正它的謬誤,證實所改正的是非,用本校法和他校法,即取證於本書、它書、類書、古書注的四種方法,是有相當征實性的方法。因為它的客觀性是與憑藉版本差不多。如唐、宋人的類書或古書注的引用,就可大致的見到唐、宋時這部書的本子。胡先生告訴我說:“依據類書或古書注,也就大致等於依憑古本。”
取證於本書、他書、類書及古書注,這四種方法,在運用時,應當各有相當的精細和警戒,茲就本書舉例於下:
一、取證本書的方法,是求本篇的上下文義,或把本篇與他篇作一種歸納的比較,找出他的句例常語,以相諟正。
例一--據上下文義
高祖詔叔孫通製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複定(儀)禮〔儀〕?謝短篇卷十二,第五六一頁。
此謂禮經十六篇何在,而庸叔孫通再定儀品也。後漢書曹褒傳論:“漢初朝制無文,叔孫通頗采禮經,參酌秦法,有救崩弊。先王容典,蓋多闕矣。”張揖上廣雅疏曰:“叔孫通撰制禮制,文不違古。”是儀品本於禮經,故仲任詰之曰時“十六篇何在”也。禮儀即謂儀品,司馬遷傳、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儒林傳、禮樂志、本書率性篇並可證。此作“儀禮”,字誤倒也。程樹德漢律考,以“叔孫通製作儀品十六篇”為句,(前漢書禮樂志考證,齊召南讀同。”則以“儀禮”為禮經,非也。據曹褒傳,叔孫通所作,只十二篇,未云“十六”。且此文屢云“禮經十六篇”,則此“十六篇何在 ”五字為句,以指禮經,明矣。此句既謂禮經,則下句又云“儀禮”,於義難通。且禮經有儀禮之名,始見後漢書鄭玄傳,(吳丞仕經典釋文序錄講疏謂始自晉書荀菘傳。)仲任未及稱也。
例二--本篇與他篇句例的比較
今魯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合)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講瑞篇卷十六,頁七二二。
“不同”當作“合同”,涉上文誤也。此反承上文。仲任意:即有合同者,不過體貌相似,實性自別。下文即申此義。奇怪篇云:“空虛之象,不必實有。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為人,乃生二卿。”是應篇云:“屈軼之草,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則言能指。”句例正同。
例三--本篇與他篇常語的比較
占因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變動篇卷十五,第六五五頁。
據下文“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則州刺史、郡太守之事,非謂大將軍也。“將”謂州牧、郡守,本書屢見,當時常語。“大”字蓋後人不明“將 ”字之義而妄加者。累害篇:“進者爭位,見將相毀。 ”又曰:“將吏異好,清濁殊操。”答佞篇:“佞人毀人於將前。”程材篇:“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又云:“將有煩疑,不能效力。”超奇篇:“周長生在州為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齊世篇:“郡將撾殺非辜。”諸“ 將”字並與此同。
二、取證他書的方法,是就本書文句出於他書,或本書文句與他書互見的,及被他書徵引的,而為比較的考察。
例一--本書文句出於他書
齊詹(侯)問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定賢篇卷二十七,第一一一0頁。
“齊詹”當作“齊侯”,“侯”一作“□”,與“詹”形近而誤。此事見晏子春秋問上。晏子作“景公問于晏子”,說苑臣術篇作“齊侯問于晏子”,是其證。下文“詹曰”,亦當作“齊侯曰”。“
侯”訛為“詹”又脫“齊”字。晏子作“公不說曰” ,說苑作“君曰”。
例二--本書文句與他書互見
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文)彌明。書解篇卷二十八,第一一四九頁。
“人”當作“文”。上下文俱論“文德”,不得轉入“人”也。“人”“文”形近之誤。說苑修文篇 “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句意正同,是其證。
例三--本書文句被他書徵引
廣漢楊翁仲(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眇)馬〔者〕,相去〔數裏〕,鳴聲相聞。翁仲(偉)謂其禦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禦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禦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實知篇卷二十六,頁一0七九。
高似孫緯略一引“仲”並作“偉”,“聽”上有“能”字,“
田間有放眇馬”作“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下有“數裏”二字,“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作“彼放馬目眇”,“目竟眇焉”作“馬目竟眇”。類聚九三、御覽八九七引亦正同。並是也,當據正。
取證於他書的方法,是最艱難而最精當的方法。劉先生告訴我說:“取證於他書的方法,才能夠發揮校勘學最大的效能。”校勘學的本義,固然是賴於版本的比校,但版本本身有兩個缺陷,即:一、版本本身的錯誤。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本子,不外唐寫本、宋刊本,但遇著這樣事實,在唐、宋以前就已經錯了,則雖有版本,也不能據正。二、善本流傳到現在,委實有限,若必待於版本而後校書,則有些書必致無法去校。取證於他書的方法,正能補救這兩種缺陷。這方法能使用校勘的材料有三,即:一、上溯本書所援據者。二、旁搜本書與他書互見者。三、下及本書被後人引用者。因為這方法取材的方面這樣多,又沒有版本的那兩種缺陷,所以這方法能夠發揮校勘學最大的效能。如荀子堯問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楊倞注:“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為人下,未知其益也。”按:“而未知”下當有“為人下之道”五字。說苑臣術篇:“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臣下之道也。”韓詩外傳七:“請問為人下之道。”家語困誓篇:“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並其證。注:“下、謙下也。 ”是所見本已脫此五字,而望文生義加“謙”字釋之。這就是取證於他書能救版本之窮之明證。
但取證于他書時,當注意到家法的不同。因為今古文的章句文字是不一樣的。如別通篇“猶吾大夫高子 ”,是用魯論,不當據今本論語改“高”作“崔”。氣壽篇“舜征二十歲在位”,今本作“三十”,即由淺人據偽孔本妄改,而不知仲任是習歐陽尚書的。潛夫論班祿篇引詩皇矣“此惟予度”亦見本書初稟篇。是三家詩,王謨本據毛詩改“度”作“宅” ,也是由於不明家法的原故。
三、取證於類書的方法,是不可過信。因為類書漏引節引,與原書時有出入。要是善於運用,它是最好的材料,因為它能夠使我們的推理得著更確實的證明。最好不信賴類書中一兩條的孤證,能夠把類書所引的歸納得數條以上,那就能夠使今本比較的近古。且舉孫蜀丞先生誤援類書的例子如次:
例一
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能耕也。亂龍篇卷十六,第七0二頁。
孫曰:“立土牛”當作“立土象牛”,與上文 “為土象人”句意相同,此脫“象”字;“未必能耕也 ”當作“土牛未必能耕也”,又脫“土牛”二字,故文義不明。類聚三十九、御覽五百三十八(當作七。)並引作“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畢能耕也”。“土牛”二字未脫。“或立土牛”作“或立土牛象人”,亦非也。惟事類賦四(當作五。)引作“或立土象牛”,不誤,當從之。暉按:類聚、御覽引作:“或立土牛,(句)象人土牛,未畢而耕也。”(御覽二十引同。)當據補 “象人土牛”句。“未必能耕也”,是承“為土象人” 、“或立土牛”兩層為文,言土人與土牛並不能耕。下文“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亦以“人”“牛” 並舉。“象人土牛”,“象人”即承“為土象人”,“ 土牛”即承“或立土牛”,類聚、御覽所引不誤。今本脫去“象人土牛”四字耳。孫誤以“或立土牛象人”句絕,而信事類賦之孤證,非也。
例二
楊子云作法言,蜀富〔賈〕人□錢千(十)萬,願載於書。子云不聽,〔曰〕:“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佚文篇卷二十,第八六九頁。
孫曰: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七十二引此文“ 富”下並有“賈”字,“千萬”作“十萬”,“聽”下有“曰”字,“之行”二字作“猶”,皆是也。今本脫誤,當據補正。暉按:孫補“賈”字、“曰”字,改“ 千”作“十”,是也。御覽八二九又八三六引亦有“賈 ”字,“千”作“十”。又朱校元本、事文類聚別集二引亦作“十”。孫謂“之行”二字當作“猶”,非也。御覽八二九引“之行”下有“
正如”二字,又八三六引“之行”下有“猶”字。事文類聚引同。則“之行”二字不誤,當據補“猶”字。
四、取證於古書注的方法,即就唐、宋人注他書時所引本書以與今本兩相比勘,往往可以補缺正誤。如感虛篇:“堯時五十之民擊壤于塗。”卷五,頁二四五。文選注、路史注引“堯時”下有“ 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九字,則知今本脫落。言毒篇:“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卷二十三,頁九五三。史記儒林傳正義引“血毒盛” 作“氣熱而毒盛”,則知今本脫“氣熱”二字,“血” 為“而”字形訛。
我對此書解釋的工作,是用歸納和分類的方法。
關於字義的解釋,是用歸納法。王氏父子就是運用這個方法得著絕大的成功,在經傳釋詞上可以表現。王引之經傳釋詞序說:“凡此者其為古之語詞,較然可著。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所無,可以心知其意者也。”沒有舊說的根據,為什麼他能心知其意呢?就是因為他用的方法正確。歸納各書中同樣的字,找出共通的意義,所以能夠“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試將本書“嫌”字的用法,歸納於下:
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
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
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以上並見書虛篇。
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談天篇。
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儒增篇。
材能以其文為功于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書解篇。
上列各“嫌”字,並當訓作“得”。劉盼遂先生訓為 “貪”,則不能“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了。 說詳書虛篇卷四,頁一六八。
又歸納全書“起”字,審其用法,可以得一通訓。
一、云雨感龍,龍亦起云而升天。龍虛篇卷六,頁二九一。
二、禹問難之,淺言複深,略指複分,蓋起問難□說,激而深切,觴而著明也。問孔篇卷九,頁三九七。
三、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頁四0六。
四、今孔子起宰予晝寢,……頁四0七。
五、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頁四一六。
六、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頁四一六。
七、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謝短篇卷十二,頁五七七。
八、天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譴告篇卷十四,頁六三九。
九、夏末蜻□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陽氣也。變動篇卷十五,頁六五0。
十、人君起氣而以賞罰。頁六五一。
十一、夫喜怒起氣而發。頁六五五。
十二、起水動作,魚以為真,並來聚會。亂龍篇卷十九,頁七00。
十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講瑞篇卷十六,頁七三0。
十四、奚仲感飛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感類篇卷十八,頁八00。
十五、皆起盛德,為聖王瑞。驗符篇卷十九,頁八三九。
十六、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為命絕也。解除篇卷二五,頁一0四二。
十七、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定賢篇卷二七,頁一一二一。
十八、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頁一一二一。
十九、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頁一一二二。
二十、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為也。頁一一二二。
二一、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為文者眾矣。頁一一二二。
二二、儒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正說篇卷二八,頁一一二六。
二三、感偽起妄,源流氣烝。書解篇卷二八,頁一一五三。
二四、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無細知以閑而能記。頁一一五四。
二五、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對作篇卷二九,頁一一七八。
二六、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頁一一七九。
二七、故論衡者,……其本皆起人間有非。頁一一七九。
以上二十七則。二五、“起”與“因”字互用,十六、“起”與“應”字互用,十六、二十、“起”與“為 ”字互用;一、七、九、十四、二三、“起”與“感” 字互用。據此,這二十七處的“起”字,有“因”、“ 為”、“應”、“感”等字的意思。這是不見於字書,而可以由歸納的結果,證明這種解釋是不會錯誤的。
再者,仲任慣用“何等”二字,歸納於下:
一、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感虛篇卷五,頁二五三。
二、實黃帝者,何等也?道虛篇卷七,頁三一四。
三、所謂屍解者,何等也?頁三三一。
四、今言男女□,相逐其間,何等潔者?語增篇卷七,頁三五0。
五、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藝增篇卷八,頁三八八。
六、年五十擊壤于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為伍,何等賢者?頁三八九。
七、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非韓篇卷十,頁四三六。
八、名世者謂何等也?刺孟篇卷十,頁四六0。
九、所謂十日者,何等也?詰術篇卷二五,頁一0三一。
“何等”二字當是漢時常語。孟子公孫醜篇:“敢問夫子惡乎長?”趙注:“醜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呂氏春秋愛類篇:“其故何也?”高注:“為何等故也。 ”都是以“何等”連文,猶今言“什麼”。
上列“嫌”、“起”、“何等”三例,都是以歸納法來解釋字義的。雖無舊說可憑,但若玩其本文,參之他卷,自覺其為適當的解釋。
全書故實,也用同樣的歸納法,以便於與其所根據的他書及本書各篇前後互見的相參照。如漢高祖的母親,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見吉驗、奇怪、雷虛、感類等篇,此事出史、漢高紀。王鳴盛說,“
遇”是“構精”的意思。據奇怪、雷虛,謂“遇”是龍施氣,則知漢人的意思與王鳴盛說同,而仲任則謂“ 遇”是“遇會”。又如湯遭大旱,禱于桑林,見感虛、明雩、感類等篇。明雩、感類並說“湯以五過自責”,而感虛篇則說以“六過”,與荀子、說苑、帝王世紀等書正合。則知仲任本云“以六過自責”,其說無異,而一作“五過”者,是出於誤記,未必仲任另有所據而云然。說詳感虛篇。卷五,頁二四五。又如桑榖之異,見無形、變虛、異虛、恢國、感類、順鼓等篇。這件故事,有書系之高宗武丁,有書系之中宗太戊,仲任於無形、變虛、異虛、恢國作高宗,於感類作太戊,于順鼓並存兩說。則知這個故事相承有如此異說,不關於今古文說的不同,故仲任隨意出之。說詳無形篇。卷二,頁六四。
關於本書援引群經的地方的解釋,是用分類法。陳奐詩毛氏傳疏序說:
初放爾雅編作義類,分別部居,各為探索。久乃□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
可見陳奐作詩毛氏傳疏事前準備的工作,將全書拆開,分成若干類,會集材料,然後會通成書。我也用這種分類的方法。不過陳氏就山川名物學爾雅那樣分類,我則就所引群經,將各經作一單位,分別抄集,然後再參照各經的各種注釋,求其家法,探其義蘊。如本書所見論語的地方,都輯為一類,以便於與本書各篇前後參照,及博征舊說,以求合於本書的原義。如論語雍也篇: “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見幸偶、命義、禍虛、問孔、刺孟等篇。據問孔篇,卷九,頁四0九。 知“亡”字讀作有無之“無”,不當如集解讀死亡之“亡”。又據禍虛、刺孟,知所謂“惡疾”,所謂“ 有疾”,是“被厲”。又如語增篇引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卷七,頁三四0。仲任的意思,“與”是讀“參與”之 “與”。但舊說“與”字的意思有四種。具見本篇。結果,可以發現分類的好處:一、就仲任的意思以相解釋,不致前後相違。二、博考舊說,取其當於本書的原義,不致於只憑舊注,使正文與注義不相吻合。
我整理這部書,前後凡七年。在三年前,只就文選李注所引本書及本書見於他書者,互相比勘,成論衡校錄若干卷,王充年譜一卷,就正于劉叔雅先生,幸蒙許為精當。去年,胡適之先生也以為我的論衡校錄有些是處,所以願意出其手校本和楊守敬校宋本借給我。今年,馬幼漁裕藻。先生借給我朱宗萊校元本,吳檢齋先生借給我手校本。因為增加了這些新的材料,校錄的內容也就擴張了。計校釋的時間凡五年,全稿寫定凡二年。其中一部分的稿子,曾經胡先生和高閬仙步瀛。先生看過,改正好多地方。全書既成,友人齊燕銘舉其論衡劄記稿本相餉,又抉取約二十餘條。--這些都是幫助我這書能夠有成功的人。謹志其始末,以申謝意。
本書今古文說,大致能說得清楚,是孫星衍、陳喬縱、皮錫瑞一班人的功績。俞樾、孫詒讓和孫蜀丞先生都對此書費些精力,我平易的援用,應當銘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黃暉序于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