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亨利.詹姆斯和唯美主义者
作者:理查德.埃尔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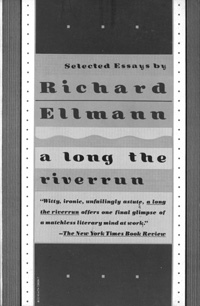
像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那样沉默寡言的小说家很少见。尽管他在写给一位青年雕塑家的信件中透露出同性恋的倾向,但我们无法肯定他们是否真的有过通常意义上的性生活。许多作家以放任著称,詹姆斯则似乎因谨慎而扬名。相比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作家,例如英国的拉斐尔前派及其后继者,法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颓废派诗人,詹姆斯鹤立鸡群,因为他从无绯闻缠身。谨慎不但是他个人生活的最大特点,而且也体现在他的文学自信心上。他那洋洋洒洒达数卷的自传、他的信件和他撰写的前言只是隐隐约约地透露出自身艺术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1873年,亨利·詹姆斯迎来了诗意的人生的第三十个年头。他决定做一点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事情。他准备写首部长篇小说了。正因为如此,他酝酿这第一部长篇——《罗德里克·赫德森》(Roderick Hudson)—— 时所花的那几个月时间具有特殊意义。詹姆斯相当直率地承认,叙事的“萌芽”源于一次晚宴上偶遇的安斯特鲁瑟-汤姆逊夫人(Mrs. Anstruther-Thompson),但他不肯透露是什么学究式的冲动促使自己着手创作。要了解这个,些微的暗示都可能有用。而在他于1873年5月31日写给哥哥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的信件中就有这样一个暗示。当时他住在佛罗伦萨,那天在一家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了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新作《文艺复兴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就在那一刹那间,他像被“火焰烧灼一般”地想买下这本书,然后写上一份短评。然而,他又写道,他意识到自己对该书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一无所知,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表示,无论如何,自己都会写些不同的东西。
亨利·詹姆斯的回信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未读过那本书,只是透过橱窗瞄了它一眼。但事实上他一定进过书店并且翻阅过它,否则他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内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既然有证据表明,他要么当时当地就买下了该书,要么后来才买,甚至还写过短评(尽管这份短评从未付印,并因此佚散),他的沉默就暗示了作家的“国家机密”,一种避免承认该书对自己的震撼的习惯性谨慎。我认为,这本书对《罗德里克·赫德森》的成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也把亨利·詹姆斯引向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后来被证明是他的伟大主题之一。
我们怎么知道他读过这本书呢?1874年,在创作《罗德里克·赫德森》的同时,他连续数月在纽约一家名为《独立者》(Independent)的周刊上发表“佛罗伦萨札记”(Florentine Notes)。札记中明确引用了佩特著作中的谈论波堤切利(Botticelli)的一章。詹姆斯提到了“一位天才的评论家(《文艺复兴史研究》的作者佩特先生)”对波堤切利的评论“与其说是条理分明,不如说是能言善辩”。詹姆斯在1894年佩特去世后给埃德蒙·戈斯 (Edmund Gosse)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称佩特为“微弱的、苍白的、尴尬的、精美的佩特”,还将他比作“一点磷光,而非火焰”。“精美”同“过分讲究”一样,是一个两面都说得通的词汇。当詹姆斯告诉哥哥自己刹那间“像被火焰烧灼一般”想读佩特的著作的时候,正如他称佩特为“一点磷光,而非火焰”时那样,他是在取笑佩特书中最著名的字句 :“用耀目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就是生命的成功。”
詹姆斯拒绝用这种方式燃烧。没有其它任何信条能激起他更大的反感。他似乎把自己的热情都注入到笔下角色的生活中去,而不在个人生活里表露。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詹姆斯——依照佩特的标准——没有获得生命的成功。他的内心火焰都被引向虚拟人物。然而,考虑到他的同性恋倾向,他不可能不注意到佩特的著作在暗地里颂扬这样一种倾向,因为后者为列奥纳多(Leonardo)、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和温克尔曼(Winckelmann)倾注了许多笔墨。我想詹姆斯受到了警示,不希望落下一个唯美主义者或同性恋者的名声。与此同时,他了解同性恋者,也想刻画他们。他可以假借唯美的名义对他们进行负面刻画。普鲁斯特(Proust)就会这么做。佩特昭显男同性恋者的兴趣也可能导致了詹姆斯在同期撰写的艺术评论中强调“男子气概”这一对立面。在这样一个情境中,“男子气概”意指除同性恋之外的一切。
可是,他对佩特的反应并未止于警惕。我们必须想象一下他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阅读《文艺复兴史》的“结论”部分的。他之所以认为佩特对波堤切利的论述雄辩胜过条理,是因为他觉得文中对某种风格的偏爱胜过了内容实质——在后来的《一位女士的肖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里他指责唯美主义者和唯美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他在《佛罗伦萨札记》中写道:“有时候人们有种冲动,想对那些在这样一个饥饿和罪孽的世界里过于钟情纯唯美的人提出无言的抗议。”( 詹姆斯本人对罪孽的兴趣浓于饥饿。)尽管他在文中承认“对艺术的一知半解有其豪壮之处”,但豪壮行为不等于英雄行为。
佩特主张在艺术和生活中强调品味和风味。他博学地引用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话语(其实引用赫里克[Herrick]即可),强调万物的瞬间即逝性,尤其是它们的“流变”——他对此的称颂多于感伤。万物如流水——这是一个常用的意境——抑或(用人体作比喻)似脉搏。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只能寄情于对情感、印象、感觉、搏动、瞬间的追求—— 这些词语对佩特来说都有双重含义。“脉搏次数只是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生活对我们的赐予。”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体验的结果,而是体验本身。”佩特说:“一切都在我们脚下化解,我们应该抓住任何细致的情感,或者任何能让精神获得瞬间自由的知识,或者五官受到的任何刺激,不同寻常的颜色、罕见的花朵、奇妙的气味,还有朋友的脸……情感使人对生活更敏感、更能感受随爱而来的喜悦和悲伤、更有政治或宗教热情,抑或是对人类的热情。”……“但一定要确保它是情感,”他加了一句告诫性的后话。这段名言不但为唯美运动指明了目的,也为其提供了词汇。
佩特的言语好似爱抚,詹姆斯对此退避三舍。他所钟爱的角色可不是随波逐“流”的人物。他详细铺垫他们情感的来龙去脉,求爱几乎绵延不断,订婚期长达数年,对另一方真实面目的了解被无限期地延迟。延迟对詹姆斯来说就像即刻满足对佩特来说一样重要。詹姆斯对“结论”的最直接的评论体现在艺评里,他反对印象派,坚持认为(见《格罗夫那画廊》[The Grosvenor Gallery])“画作不是印象,而是表现。”就好像他预先知道叶芝(Yeats)会在《人物》(Dramatis Personae)中写道:“佩特所表达的文化理想只能催生阴柔——灵魂成了镜子,而非火盆。”詹姆斯还在各篇文论中批评了那些被佩特冠以情感美称的自恋念头。
我们只要仔细推敲就可以认定,詹姆斯的小说《罗德里克·赫德森》的中心主题正好同佩特唱对台戏。小说的情节几乎就像一个寓言:大有前途的美国青年雕塑家罗德里克·赫德森获得艺术爱好者罗兰·马利特的赞助,可以去欧洲游历三年。这份赠与的动机看上去再纯洁不过,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两个人都爱上了同一名妇女。游历的目的是让他开拓视野,提升艺术表现力。罗德里克·赫德森一到罗马就开始发表佩特式的、而非罗马式的言论。赫德森问:“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印象怎么了?……一个星期里有二十个片断……看起来是终极性的……还有二十个看似极致的印象……可是其它片断和印象接踵而来,挟卷它们一同前行,然后它们全都化解了,如同水化解在水中一般……”这就是佩特所说的片断、印象、花、化解和水的意象。罗兰·马利特对赫德森的言论表示不以为然,他想:“他对新鲜事物的追求永无止境,而对一切看似异类的事物,他总会付出额外的情感;但半小时过后,新鲜感消退了,他猜出了秘密所在,他挖掘出了秘密的核心,就吵嚷着要求更多的感官刺激……”“异类”在此等同于佩特爱用的“不同寻常”和“罕见”。罗德里克·赫德森宣称:“我们必须像脉搏跳动那样生活,” 这是对佩特所言“脉搏次数只是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生活对我们的赐予”的呼应。无怪乎罗德里克在罗马度过的最初两周被他的朋友称为“一次高度唯美的狂欢”。他已经陷入到对艺术一知半解的非英雄行径中。
不幸的是,这场狂欢很快变成了一种“流变”,而“流变”这个生动并受佩特赞许的词汇在詹姆斯那里不受欢迎。罗兰·马利特告诉罗德里克:“你蹒跚过,漂流过,你从一件事漂向另一件事,而我确信此时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佩特曾经颂扬过米开朗琪罗所创作的亚当的不完美;而罗兰则用遗憾的语气说“这可怜的家伙(罗德里克)不完美。”罗德里克沉浸其中的“无限试验”只是一种“有害的幻想”。“最终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流变不仅仅是流变,而且变成了坠落。罗德里克后来真的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上摔了下来,而这一摔也有象征意义。他的崩溃由于试图从对克里斯蒂娜·莱特的追求中获取新的感官刺激而加速了。注定将成为卡萨马西玛王妃的克里斯蒂娜对他来说是一个合宜的目标,因为她比佩特笔下的蒙娜丽莎更有道德上的模棱两可性;同佩特对“希罗底的女儿”的秘密崇拜遥相呼应,克里斯蒂娜·莱特被描写为“能与希罗底媲美”。詹姆斯后来觉得自己给了罗德里克太多不利的筹码,以至于这位年轻人迅速崩溃。这也许是因为詹姆斯对佩特的公式过于恼怒。通过罗德里克,他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物,一个被他嘲弄、讽喻和从道义上批判的唯美主义者的形象。对罗德里克的刻画并非全无同情:他在阿尔卑斯山区险崖的死就相当雄辩。
《罗德里克·赫德森》是詹姆斯精心策划并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拿破仑式战役的第一阶段。四年后的1878年,他写了一个题为《一束信件》(A Bundle of Letter)的短篇小说。其中的一个“唯美型”人物谈到:“除了艺术,生活还能是什么?佩特在某处已经讲得再透彻不过了。”我无法肯定那时佩特是否有如是的言语,但他一定有所暗示。在《一位女士的肖像》(1881)中,詹姆斯演化出了一个明确发表此种言论的角色。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提醒伊莎贝尔·阿切尔:“你难道不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一个人应当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奥斯蒙德身上渗透着佩特式的异端邪说。他说自己是“在世的最最过分讲究的青年绅士。”他的确过分讲究——他有品味,他有感觉;他缺少的是同情心和对妇女的爱。他爱摆姿态,他只求形式而不关心内在实质,正如拉尔夫·杜歇所言,他是“一朵褪色的玫瑰花蕾”,也因此是“一名毫无生气的艺术半吊子”。佩特在他的“结论”里说,个体是孤立的,“每个头脑都囚禁着一名孤独的犯人,那就是对世界的梦想。”同这个比喻相呼应,奥斯蒙德把家当成囚禁妻子的地方,把女儿送进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监狱——修道院。作为生活艺术家的奥斯蒙德,还有作为艺术家的赫德森,都为自我所困。奥斯蒙德的情妇默尔夫人同他们气味相投,因为她把“生活的艺术”当作“被她猜透的某种花招”。通过对照,詹姆斯呼吁少谈艺术,多关注心灵。

詹姆斯一看到佩特的书就觉得厌憎不迭。其他人对佩特的态度没有这么激烈。奥斯卡·王尔德比詹姆斯稍晚一些阅读了《文艺复兴史研究》;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正急于依附于某种令人向往的信条。对他来说,这本书一直是他的“宝书”,“一本对我的人生有着如此奇妙影响的书。”他在1877年给同班同学写了一封信,劝告他“充分发挥你天性的每一部分”。在他不知道自己人生何去何从的情况下,他认为佩特为自己指明了方向。
同《罗德里克·赫德森》里的克里斯蒂娜·莱特一样,王尔德尝试过天主教——这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感官刺激”;而《一位女士的肖像》中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写给伊莎贝尔的题为“重访罗马”的十四行诗之所以得名,可能是因为王尔德在1881年发表了“未曾拜访的罗马”一诗。然而,吸引王尔德注意力的并非只有罗马天主教;他同时还从共济会得到新体验。如果说,他对佩特的诱人论调有所反应,那他同时也对罗斯金(Ruskin)的讲座和谈话里的道义斥责作出反应。有时候,他为自己的善变感到不安:他曾经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然而,我随着思绪的改变而千变万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软弱、更自欺欺人,这一点我就用不着详叙了。”他就是在这种情绪中写下了诗歌《哎呀!》(Helas!)。诗中的他像佩特和罗德里克一样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