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与远东纠缠的西方作家们
作者:惠 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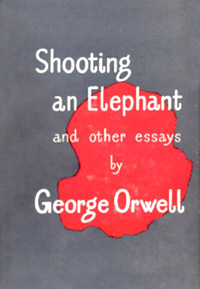
同是作家,想法却是如此不同。不过奥威尔也有“蜕化”的迹象。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毫不客气无节制地使用缅甸仆人。他把衣服和烟蒂都往地板上丢,让仆役捡,还让他们为他穿衣脱衣(吉卜林甚至训练其仆役学会在他睡觉时为他刮脸)。后来,奥威尔写过一本书:《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他对“我在暴怒时用拳头打过仆人和苦力”表示悔恨。
去缅甸前,奥威尔肯定是处男,到了缅甸后,虽然他一再念叨“社会良心”,但他一定去过码头区的妓院,排遣孤寂,他跟一个缅甸女孩有过一段私情。奥威尔喜欢虐待自己的肉体,可他不是寡欲的清教徒,在不长的一生里,交织着不少女人的故事。
关于在缅甸当警察的经历,奥威尔写过两篇重要的随笔:《绞弄》和《杀象记》,这两篇文章相当坦白,是自传性的,是对五年警察生活的反思与总结,也是政治告白:表明他与殖民制度脱离了关系,为他认为是自己罪咎之事赎过。
《绞刑》是奥威尔的第一篇出色作品,它记叙了一次讲究仪式的处决。描写很细致,从被绞者表情动作的细微变化到行刑者的紧张不安都一一毕现,奥威尔说“我认识到看到将一个生命正当盛年令其中断一事的不可理解及错得可怕之处”。他明确地表现了人道主义观念,并以此成为他所有作品的特点。
《杀象记》也是关于一次未必正常的杀戮,但此次的受害者是头大象。正是奥威尔向它下的杀手。在缅甸,发情的大象有时会在街上及市场上乱跑,当地警察必须将其打死。那是一头4吨重的大象,已经因发狂而闯了祸,将一个苦力踩到了脚下,年轻的警官带着恐慌与负疚,取了杆猎枪,第一枪就击中,然后一直开枪,直到把子弹打光。这场杀戮是勉强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显示英国警察的权威,奥威尔感觉到自己已成了“野蛮人”,是粗暴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执行者,这么做对吗?
1927年,22岁的奥威尔回到英国,他辞去了待遇优渥的警察职位。
奈保尔:离印度很近又很远
奈保尔是西方作家吗?不是,也是。
说不是,理由很靠得住,奈保尔祖父以上都扎根于印度,是纯粹的东方人,1880年,祖父作为契约劳工才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移民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岛(位于向风群岛最南端,委内瑞拉东北部海岸外),奈保尔是在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长大的。如果奈保尔像我们一样,要在官方文件上填写“籍贯”的话,他只能写上“印度”二字。

但,奈保尔又是难以质疑的西方作家,至少他是用西方(更准确说是英国)的眼光观察人、物、事件,他的作家梦是在英国实现的,他所装备的文学武器也是从西方的文学仓库里挑选来的。在13岁之前,他就已经记得很多英国文学中的片断,它们主要来自莎剧《裘力斯·凯撒》、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大卫·科波菲尔》、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印度的记忆和理解得自于童年时代家里的一些物件摆设和游戏般的宗教仪式,这只是些碎片,是一些七零八落再也拼凑不出一幅完整画面的碎片。其实,他更多的印度印象来自于英国作家(毛姆、艾克利和奥尔都斯·赫胥黎)笔下的印度,这是苦涩的荒诞:一个印度的后裔,居然要借助西方的透镜去观察自己的祖国!这种透镜是有偏差的,歪曲的,所以,1964年奈保尔在访印游记《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中承认,印度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形的世界,因而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远离特立尼达,是个存在于虚空之中,没有具体历史的国度”。1956年,他与牛津同学英国姑娘帕特里夏·黑尔结婚,这个婚姻是有象征意味的,是一种姿态,奈保尔背向印度,面朝英国(西方),虽然他的心仍在漂泊,但我们不得不把他看作是一个“西方作家”。
1962年,奈保尔已在英国确立了作家的地位,他不再需要心无旁骛地盯着一个目标埋头苦干,他要放松些,要走走看看,拓展视野。他“寻根”去了,从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再到他外祖父的故乡。他是不是有点锦衣归乡的感觉,可能有点,一路上,他都是以作家的身份(英国来的作家!)同人打交道,是的,他还有个漂亮女伴,这多少有点炫耀的成份。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他走的是“寻根”之旅,他说:“如今,在我个人的这趟印度之旅中,我会发觉,我们家族的迁徙和转变——从印度北方邦东部,漂洋过海来到特里尼达——到底有多彻底,究竟能不能再回头。”看来是不能回头了,风筝已经断线,英国文化将奈保尔武装到了牙齿,他的目光是西方式的,这种目光又与康拉德、福斯特、毛姆等人不同,后者自然是坚固的西方中心观念,可他们又痴迷于东方的神秘,而奈保尔的血缘来自印度,他对印度文化没有起码的好奇与惊诧,他的目光赤裸裸的尖锐,如利剑一般斩断回归之路。
真是不凑巧,奈保尔刚到孟买就遇上了糟心事,他带的两瓶洋酒被海关扣押了,孟买有禁酒令。于是,他费了几天时间,同臃肿、懒惰、推诿的印度官僚部门打交道,这两瓶酒总算索要了回来。这就是印度,奈保尔刚刚与之打交道的印度,一个不好的兆头。
然后,奈保尔看到的是一连串的贫困、丑陋、腐败、堕落、肮脏。他感到的是震惊、愤怒、疏离、鄙夷与失落。在外祖父的故乡,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这种热情是有企图的,他们希望从奈保尔那里得到各式各样的帮助。所谓的乡亲也是这么功利。奈保尔受不了,他开始奔逃,匆匆地、草草地结束了第一次印度之旅。这次旅行的记录《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是尖酸刻薄的,缺乏同情与体谅,可以归入丑陋系列,他写的是“丑陋的印度人”。
奈保尔就这么简单地逃离了印度吗?没有。1975年在甘地夫人颁布“紧急状态”令前后,他又来了。他愿意稍稍深入一步,不再是仅仅看风景,他要揭开现实的表象,去看看真实的印度。他交结朋友,走进当地人的家庭,考察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状况,他发觉这个印度是几千年的宗教文化、种姓制度、甘地主义等因素共同影响塑形的结果,它有独立、政治民主、现代技术的外壳,但内部还是很空虚无力。
第二次的探访也没枉费,他写了《印度:受伤的文明》,他写道:“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又那么远。”面对印度,奈保尔不断在调整焦距。
1988年,奈保尔把焦距调得更近了。他又一次走上印度的土地。在孟买一下飞机,他看到了一场庞大的集会,是一群贫穷人的聚会。敏感的奈保尔立即判断出这是印度的新风景,是低级阶层的民主自觉。以后的日子里,他聆听记录了各方人士的叙述,他感觉到印度的弱势群体也发展出了集体归属感和政治意识,虽然,各阶层之间有矛盾有斗争,但,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印度开始出现活力。
奈保尔越来越耐心,越来越善于倾听,越来越抵达印度人的心灵,《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他的第三次游印记录,也是一部由印度人口述的历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