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在神秘物质的王国里
作者:乌尔斯.杰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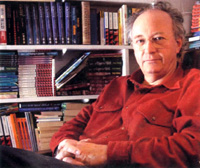
在英国与美国,他是畅销书作家,而在德国,他还只
是个“探秘者”——英国幻想小说家菲利普·普尔曼
想象一下我们的灵魂能有个表现其存在的躯体,比方说以某种动物的模样出现——当然应是一种能够理解我们的想法、会说话、并能陪伴我们一生的动物,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当我们坐在咖啡屋前一边晒太阳,一边观看行人带着他们各自的有着动物模样的灵魂在我们面前走过,我们的灵魂所赖以寄存的躯体——也许是猞猁、松鼠,也许是小鸮就坐在我们的脚边、怀里或肩头;当我们在办公室与某位同事不期而遇,这些灵魂的寄生体也许会在我们的脚前把我们头脑里的记忆表演得淋漓尽致——时而像狗碰见了猫,时而像兔子遇见了蛇,要不就像正在相互猛啄对方的两只乌鸦。
无论青蛙、绵羊、蝴蝶还是别的动物,总之,不难理解“人的本质会映照在他们各自的动物形象中”这样的想法。“你难以想象,有多少人希望自己能得到一头狮子,但偏偏只能满足于一条卷毛狗!”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谁能以他自己的这种“灵魂动物”——吉祥物、图腾、保护神——作为生命的伴侣始终陪伴左右,那他也许永远都不会寂寞孤独了。
这样的世界现在已经有了。在这个世界中,各人都拥有他自己的灵魂动物,它们甚至还被赋予了名字和昵称;但在其他方面,这个世界实际上却几乎与我们的真实世界完全相似。这“另一个世界”,当然有另一个创造者。这个世界就是由文学创作出来的,它的作者英国人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渐渐在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了读者,然而在出版界里却依然不大令人注意,所以书商们仅把他作为“探秘者”来推荐。
但在英国和美国,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那儿,现年五十四岁,曾当过教师,与其家人一起居住在英国牛津的普尔曼先生,并非只是以他新近出版的小说《琥珀望远镜》(The Amber Spyglass)才雄踞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行家们认为,在当今人数众多、风格各异的盎格鲁撒克逊幻想小说作家队伍中,他是最具创造力的“创世者”,是造诣最为深湛、就连令人头晕目眩的深谷都毫不畏惧的历险故事作家,是《指环王》名作者J .R.R.托尔金的后来人与继承者。

普尔曼自己却避免使用“灵魂”这一概念。他用的是“精灵”这个字眼,以此表示对这种专门版式的重视,以求把“灵魂动物”与其他种种森林的、草原的或田野中的恶魔区别开来。普尔曼式的精灵看得见摸得着,虽具有某种动物的外形,却是另类物质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通常具有同它主人相异的性别(个别例外曾有所提及,却未做出过阐述);它既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人一旦死去,它就销声匿迹化为乌有。
就像托尔金在英国或者《讲不完的故事》的作者米歇尔·恩德(Michael Ende)在德国一样,菲利普·普尔曼是青少年读物作家。他比他自己可能意识到的还要强有力、还要令人信服地跨越了青少年读者群,发展成为一名有全面要求、有实力的童话作家。
但他的精灵三部曲的第一部《金罗盘》,其实还仅仅是一本青少年读物。从以下的内容就能看出这一点:书中的主人翁是个孩子,一个没爹没娘的十二岁姑娘,在牛津某个古老乡村长大——当然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牛津,那里同样也住着许多人,所不同的是还有这些人的灵魂所化身的各种各样动物。
这小女孩名叫莱拉·贝莱克娃。就像神话中的男女主角理所当然地那样,她的出身高贵却又模糊不清:她是一位富得难以想象的浮士德式的自然研究家与一名美得难以置信却又狂热信仰原教旨主义的名门女子伴有谋杀传闻的破裂婚姻的产物,这名女子已身居教会高层,非以往任何一位女子可比,几乎已达到了神圣的宗教法庭的顶峰。对这位丈夫和这位夫人来说,上帝就是他们生活观念的中心主宰;而这,恰恰就使他俩成了死敌。
这个出身如此特别的孩子,就像神话故事中常见的那样,身负震撼世界的诅咒或祝福。但莱拉却幸好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这也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传奇故事创作手法)是在乳母身边长大的,对父母毫不了解。就这样,读者最早遇见莱拉时,她与她的玩伴及他们的精灵在一起,是人们自“长袜子皮皮”(注:瑞典女作家阿斯里德·林格伦 (Astrid Lindgren) 创作的《长袜子皮皮》(Pippi Langstrumpf)中的主人公。)以来所遇到的一位最最调皮捣蛋的小孩,是一个诡计多端、恣意妄为且谎话连篇的女孩,甚至还赢得了一个人们以为早已永远赠予奥德修斯(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主角)的诨名:骗人精。
当孩子越来越频繁地失踪——这显然是谣传中所说的一帮卑鄙无耻甚至会吃人的专门拐卖儿童的歹徒所为——玩耍的日子结束了。等到莱拉最亲密的朋友罗格也成了这帮歹徒的战利品,她就开始了跟踪。途中她却迷失了方向,以致她生平第一遭离开牛津,又是坐船又是坐狗拉雪橇又是乘气球,朝着北极而去。
后来她也见识到了人间的牛津以及某些人间之外的世界,它们有时像意大利,有时像西藏。她途中结识的主要同伴,是北极白熊和一群女巫,最后还有天使。天阴了下来,那个一会儿说莱拉将承担起救世主的任务,一会儿又说她将担当起新的人类之母夏娃这一角色的可疑预言里只有一点是明确的:莱拉——人们愿意按照亨利·卢梭所画的图画那样来想象她——会带来战争。

至于在精灵的体形方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小孩们的精灵都是多形态的,它们可以根据意愿与需要在一刹那间就改变自己的动物形貌,几乎能从大象变化到蚊子——当然只是“几乎”,因为一个精灵的体重,大概从不会超过他的主人。在莱拉丰富刺激的历险记中,她的精灵的变形占去了很大比重,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她与她的精灵始终都明白,童年时代即将结束。那将是一个“凝固”的时刻,也就是每个精灵都将失去变化能力、永远保持某一形态,而它的主人也将无可逆转地有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只有(在人们讲述的有关莱拉的世界的版本中)天国里的亚当和夏娃,才会拥有永远可以变化的精灵。
菲利普·普尔曼的小说主角所到的每个世界里,都有一条具有决定意义的“阴影线”。它细如发丝,深如山谷,将童年与成年截然分开:它意味着“无辜”的终结、被逐出天国以及发现羞耻、罪恶与死亡。跨越这条界线,对作者普尔曼来说,也就等于超越青少年小说而进入了宇宙幻想神话创作的领域。
在普尔曼所著的《黑暗物质》一书中(该书未列入三卷本德文版计划),自然科学家以及神学家们的最大兴趣都集中到了一个尚不能解释其原因的现象上,一个莱拉家乡的牛津专家们用一个不起眼的代号“尘埃”来称呼的现象。它所涉及的是,有人认为在北极光五彩缤纷的雾霭后面,依稀可以看见梦幻般的另一世界的种种场景,虽是远在天边,却似近在咫尺;而那闪烁不定的北极光的内里,依稀可以看见的就是这种极易消逝的“尘埃”。据莱拉父亲阿斯利厄尔大人为之奋斗的实证自然科学猜测,这种“尘埃”中蕴藏着宇宙的某种原始能量;而宗教教义却认为——就如莱拉的母亲柯特夫人所说的那样——这“尘埃”无非只是原罪的表现,也就是“原恶”。
在这两种观点的对峙中,动物灵魂的想法起初仅仅显示出滑稽可笑仿佛在开玩笑的一面,后来却表现出了其凶狠狂暴的方面,并对拐骗掳掠儿童的强盗行径做出了一种可怕的解释:在孤寂的北斯堪的纳维亚或西北利亚渺无人烟的冰原中,柯特夫人在做某项试验,用一种斩首机把孩子们与他们的精灵分开——如果他们可以活下来,也不过是被残忍宰割得只剩下躯干,只剩下死而复生的冷漠,却一劳永逸地摆脱了罪恶,而这个,恰被柯特夫人称颂为“信仰的胜利”。
与此同时,莱拉的父亲也正在靠近北极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以他的方式在试验一台精灵断头机:他想证明,在孩童与其灵魂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切断的那一刻,会爆炸性地释放出一种巨大能量。试验成功了,阿斯利厄尔大人(在原版书名为“北极光”的第一卷结束时)用一份“人祭”引发了一次爆炸,它穿过北极光的雾霭,打通了进入彼岸世界的通道。莱拉大胆地作为首批的一位成员走进了这个新世界,而她的好友罗格,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与所有成功的童话作家一样,菲利普·普尔曼也毫无畏惧地利用别的童话里的某些情节。按照“阅读像蝴蝶,写作像蜜蜂”的座右铭,用普尔曼自己的话来说,他已“从我所读过的每本书中都窃取了一些思想”。但他特别推崇的是三个具有启示性的榜样:一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注:1777-1811,德国十九世纪初期现实主义剧作家和小说家。)及其所写的文章《论木偶剧》(“On the Marionette Theatre”);二是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讲述了魔王撒旦垮台和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之原罪的英国的那位巴洛克叙事文学作家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三是那位用诗与画描述了创世场面及世界末日恶战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注:英国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重要诗人兼画家。)

克莱斯特的论文《论木偶剧》,是两个男人围绕诸如“无罪”与“意识”、“活动的灵魂”与“对天国的向往”之类的概念兜圈子的一篇稍嫌松散的对话。“天国的大门是锁上的”,其中一位男子断言,“我们务必围绕着这个世界旅行,看看后面是否会有什么地方重新开了门。”而阿斯利厄尔大人这位周游列国者所试图打开的,也许正是这扇门。
普尔曼想要有条不紊地展开他的世界幻想故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对新的物理学来说也并不陌生的)如下一个观点,即:人们也许能把各种可能的世界都同样地看成是真实的。或许可以设想有千百万个世界存在,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仅仅只在毫发之间。普尔曼笔下人物的历险故事发生在多个世界,它们相互毗邻且相互近似,就好比同一篇原文有种种不同的译文或剧本一样。
假使这些世界是两维的,那么人们就可以设想,它们可以像一本精印的圣经那样一页一页地相互紧密重叠。同样,人们也应当把它们想象成在多维空间里相互紧密插入套叠在一起(假使人们可以这么想象的话)。而因为没有任何创造能做到尽善尽美却都会有些“离奇”,所以人们同时还得设想(或许会有听上去确实比“宇宙绳线”理论更奇妙的事呐):所有这些世界都是“并非完全密封”的,因而,我们这个世界说不定在某处也有一个可以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洞口,而且既非通往《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那位红桃王后霍勒夫人或魔术师欧兹的世界,也不是回到天国(如在克莱斯特的思想游戏里那样),而是比方说通往莱拉的那个世界。
据普尔曼称,八十年代中期,牛津当地,也就是说几乎就在与普尔曼为邻的地方,有位名叫约翰·帕里的探险旅行家在一次考察阿拉斯加的中途曾发现过这样的一个洞,至于它的存在,约翰是从爱斯基摩人的萨满(注:萨满教中的男巫)那里听说的。在一次雪崩中,他满怀好奇地钻进洞去过,从此再也找不到返回的路。迷乱中他又穿越了好几个世界,最后在莱拉的那个世界里重新以探险旅行家的身份(此时他已改名为斯坦尼斯劳斯·格鲁曼博士了)平步青云,甚至永久性地加入一个鞑靼部落。后来他让人帮他穿了颅,最后成为一位著名的萨满。
普尔曼史诗般的宇宙故事中最令人吃惊的,是人物的活动不断延伸扩展,使他的作品形成了甚为丰满的三部曲,却又不针对任何具体的搜寻捕捉对象——既不针对希腊神话故事里的金羊皮,也不针对中世纪史诗与传说中的圣杯,而只是针对所谓“尘埃”,也就是一种朦胧混沌的现象,它是那么虚无缥缈,以致简直就很难说,这“尘埃”是否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设想而存在。但在人间的牛津,有一位女性的天体物理学家就明显觉得,它涉及的是一种“不明物质”,缺了它,就无法使她的宇宙模式处于平衡;在另一个世界中,人们又试图把这种“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