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那一瞬的意味深长
作者:纳 芝 [英] 布鲁克.爱伦
“你又来了,阿瑟。”米德尔顿太太抱怨道,“我们只有彼得一个孩子呀!”接着,她恶声恶气地加了一句,“够了!”

“一周三畿尼吗?”她丈夫反问。
“三天三畿尼。”她回答。“可那时候你花在杜松子酒上的钱又是多少呢?”
“噢你得了吧,黛安娜宝贝儿,你不也爱喝个一两口嘛。”
“我必须喝的。”她加重语气说。
“是呀,至少死了三个人。”彼得突然插嘴说。
忠实地记录下听到的谈话产生出惊人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企图称格林为自然主义者。不过,这一术语不能尽如人意,因为格林的创作也会显得特别佶屈聱牙:在长达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从没停止做新的尝试。《生活着》(Living,1929)是关于劳动者的小说,以一种激烈紧张、省略了所有定冠词的精练文笔,勾勒出工人那严酷刻板的生活;最终取得的文风达到了矫揉不自然的地步。不过,《生活着》依然包含着一些美得异乎寻常的段落。在他后来的几部技巧更加娴熟的小说里,例如《爱着》和《着火》,行文可能更精美细腻,却和任何其他作家没一点相似的地方。下面举一个《爱着》的片段为例,是写管家劳恩斯和他爱慕的女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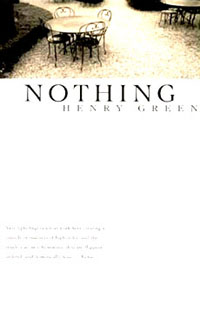
“噢,艾迪,”他气吁吁地说着走上前来。外面风雨交加,屋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把她搂在怀里,他俩的身体合而为一。他们留下了一个剪影,顶部是他的脑袋,它搁在她轮廓清晰、线条优美的头颈上方,俯视着她那一头茂密的头发,又把头发搞得乱成一团,而她的嘴唇隔着这些发丝热烈而急切地吮吸着他。
“艾迪,”他嘟囔着挣开身体,只为可以再一次把脸埋到她的脸上。不过,他把她压成了弓形。“艾迪,”他又喊了一声。
格林厌恶“写得好的英文”,觉得写得好的英文往往是未经思索、韵律呆板的陈词滥调,经常让他构起词来疙里疙瘩,让他的许多想法中途夭折。他评价他崇拜的文学偶像、《阿拉伯沙漠旅行记》(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一书的作者查尔斯·蒙塔古·道蒂(C.M.Doughty)的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很贴切:“他决不优雅,也就是说在处理大主题时决不马虎含糊……他具有一种做作矫饰的文体,可他却是个那么伟大的人物,就连这种文体也无法掩盖这一点……他常常是晦涩的,却始终是气势恢弘的。”
格林终究还是回复到写以前那种叙事散文体,完全用对话来结构他最后的两篇小说:1950年的《虚无》(Nothing)和《溺爱》(Doting)。有些人觉得这些书写得挺肤浅,完全是关于,实际上也的确如此,那些给惯坏了的、有气无力的、上层阶级的寄生虫;另一些人却觉得它们美妙绝伦。正如特雷格罗恩所说,格林成功地探测到中年人“浅薄的痛楚”,显然,他很喜爱他那些有点好色、有点娇纵任性的中年男人、那些索然无味的女友们、那些挺有自制力的妻子们,正像他喜爱他早先的那些人物形象,依照传统标准,这些人物可能会被视为更有价值。《虚无》和《溺爱》这两篇荒唐透顶的小说,是迄今所有小说中最最有趣的两篇,使得那种始终贯穿在格林作品中的幽默感达到了一种几乎是抽象意义上极致。当代的一位评论家如此评论格林的小说《赴宴》:“我们一直读得津津有味,因为实在太有趣了:几乎每一页都会让我们捧腹大笑。可等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心里谁也不会觉得它是一部喜剧。”格林的读者时不时地会发现这么一种效果:尽管谁都不会认为他首先是个喜剧作家,但他写的每一页作品难得有不带黑色幽默的时候。
《溺爱》在格林五十六岁的时候才获得出版。你尽可以责备他因为酗酒而沉寂了二十年,不过那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更多的东西可写:九部小说组成了一套奇特的作品全集。我们也不妨称格林为反高潮的大师。在他的小说中,没有一个人因为阅历丰富以后而在性格上有所变化或有所改进,没有一个人获得奖励或遭到惩罚。正如特雷格罗恩所说的,他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传递了“一种多数人的一生中多数无法获得升华的戏剧感”,要么,正像《溺爱》最末那个精彩句子所表达的,“第二天,一切又都进行得跟原先一样了。”格林书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我们多数人会觉得有趣的那一类。从头至尾,无一例外,他们尽是些自私自利、不思悔改的人。不过到了书的末尾,作者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可喜地缺乏判断力、甚至愚忠愚孝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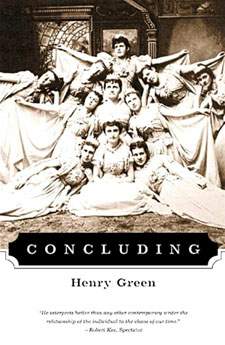
亨利·格林是用英语写作的人当中情感最丰富、天资最聪慧的一个。哪位读者会忘记《赴宴》中阿玛贝尔洗澡的那段描写呢?会忘记《爱着》一书中伊迪丝给孔雀喂食那段精妙文字呢?学者乔治·品特(George Painter)评价《最终结论》(Concluding)的那段话,可以顺理成章地拿来形容格林的其他小说(1948年出版的《后面》(Back),为他所有的作品画上了一个句号):“它令人难忘的原因,根本不是因为它深奥难解、模棱两可的魅力,而是由于读者始终弄不清楚让他们难以忘怀的究竟是什么。”格林几乎达到了一个纯粹艺术家的境界,这一点无人能及。谢天谢地,他的书没有一本是为了阐述一个哲理、推进一种理论或是传达一种信息而写的。对他来说,一个人所感到、听到、看到的“那一瞬的意味深长”,通常会伴随一丁点轻喜剧的性质,这才是惟一举足轻重的那一瞬,如果确有什么举足轻重的那一瞬的话。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