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那一瞬的意味深长
作者:纳 芝 [英] 布鲁克.爱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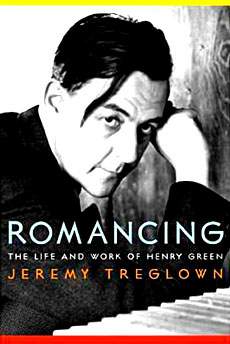
每隔十年,亨利·格林都会被当作一位文学新人重新推荐给读者
亨利·格林(Henry Green)活了六十八岁,死于1973年,是英国二十世纪最优秀、最难以归类的一位小说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一位现代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他的文风那么委婉含蓄、拐弯抹角,使得他的美国门徒泰瑞·塞瑟恩(Terry Southern)不假思索地称他不单是“作家的作家”,甚至是“作家的作家的作家”。他还公然反对理性主义,始终厌恶文绉绉的对话,而偏爱闲言碎语。他的散文表现出慷慨激昂的倾向,也可说是累赘的,甚而显得有些笨拙。他一生不趋时媚俗,在幼稚文学处于巅峰期的时候,撰写一种无产阶级小说;而在提倡简朴意识、以“愤怒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 注:50年代的一群英国作家,他们的作品表达了强烈抗议社会的特点。)为文学主流的年代,又不合时宜地掉头去写浅薄的“客厅喜剧”。
无论依照哪一种理论,格林的小说都该归到那些书页早就翻黄了的二十世纪经典文学之列。他总能得到他同辈作家的最高评价:惠斯顿·休·奥登(W.H.Auden)(注: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青年作家领袖,40年代思想右倾,后期诗歌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的诗集《 死亡之舞》和《 双重人》中的诗篇,奠定了他在20世纪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在处于鼎盛期时称他为“在世的最佳英国小说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注:1909- ,美国女小说家,作品大都描写密西西比河流域小城镇的生活,写有长篇小说《德尔塔婚礼》、《乐观者的女儿》和短篇小说集《金苹果》等。)1960年撰文陈述她的观点时说格林的作品具有一种“比当今任何虚构小说作家的作品都更加伟大的激情”。菲利普·汤因比(Philip Toynbee)认为他是最最重要的一位英语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格林去世二十年后写道,“亨利·格林是一位相当罕见、具有非凡独创性、敏锐观察力、细腻的感觉、无与伦比的小说家,他作品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是无比珍贵的。”或许这是亨利迄今为止所受到的最高评价。
尽管格林的九部小说从同行那里得到的尽是些热情洋溢的赞美,却仍有数量惊人的饱学之士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格林执意要隐去真实姓名亨利·约克(Henry Yorke),而采用很不起眼的亨利·格林当笔名。他总是拒绝别人为他拍照,除非是从背面拍,也不愿向新闻界提供一丁点个人隐私。他在世时隐居避世的作风影响了他死后的声名,所以每隔十年,他都会被当作一位文学新人重新推荐给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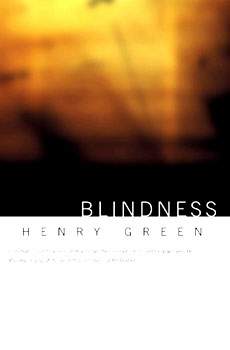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前任编辑、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传记作者杰瑞米·特雷格罗恩(Jeremy Treglown)新近写了一本《亨利·格林传奇:他的一生与创作》(Romanc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Henry Green),使得这个过程又开始了下一轮循环。特雷格罗恩的计划似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格林的儿子塞巴斯蒂安·约克(Sebastian Yorke)曾在1991年委托他撰写格林的传记,一年后却又改变了主意,所以许多门路都被堵死了,特雷格罗恩不得不据理力争。约克的家人完全有理由对这一计划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万一传记作者对这位性情古怪的小说家缺乏同情心,就很有可能描绘出一幅颇具毁灭性的肖像画:格林性关系上无数不检点的行为,他那情感上的虐待狂倾向;从他完成最后那部小说到去世的二十年间,他一直迷醉于酒精招来诸多非议,这些丝毫不会对阅读他的作品产生有益的影响。借用哈罗尔德·罗斯(Harold Ross)“天才不露相”的说法,特雷格罗恩成功地写出一本很精彩的传记,一方面向那位性情乖戾的主人公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的缺点。
大多数一流作家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格林的情况却有点特别,正如特雷格罗恩透露的,他既是位贵族,又是位产业家。他母亲是英国最大的家族之一勒孔菲尔德男爵二世(the second Baron Leconfield)的女儿,是在佩特沃思(Petworth)长大的。他的父亲文森特·约克(Vincent Yorke)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文学家,后来改行经商,接管了一家濒临破产的铜器工厂,将它改造成一家供应酿酒机械和铅管制品的厂家。H.彭蒂费克斯父子公司(H.Pontifex & Sons)变成了一个家族企业,亨利最终将在公司里担任一个不胜任的管理人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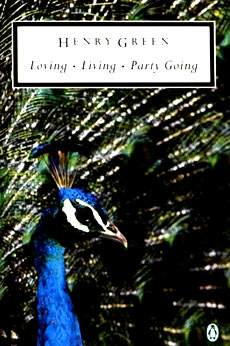
“假如约克性格中的一面发现财富是自由呼吸的障碍,”亨利·约克毕生的挚友,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注:1905- ,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下午的人们》、系列讽刺小说《配合时代音乐的舞蹈》[12卷]等。)写道,“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就会把这当作理智上可以接受的事物。他便会克制自己,对一种与他的家庭环境、经商活动、社交生活有关的敌对情绪做出妥协,在使自己满意这一点上,他从来就做得不大成功。”
鲍威尔的观察,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是一种有意识的轻描淡写:亨利·约克极端保守主义的背景,连同他叛逆的性格以及旁观者的自我意识,使他形成了一种矛盾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达到了一种性格分裂的程度,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在那个高贵庄严、目光锐利、以揭露人们真面目来使人震惊的亨利·格林同那个极富同情心、决不咄咄逼人的亨利·格林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别。”
约克出生在1905年,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他家族的庄园里度过了那种传统的、上层阶级的童年,尽管和较为传统的狩猎活动相比,他更喜欢打台球;尽管不像他那两位闯劲十足的哥哥,他是个“胖乎乎、与世无争、神经质”的孩子。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念书的时候,他那古怪的见解,以及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强烈个人魅力的气质,开始在他的同代人中间留下了深远影响,那可是个非同凡响的团体,其中有安东尼·鲍威尔、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布赖恩·霍华德(Brian Howard)、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和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尽管他无意在学术上出人头地,他依然每天去两次电影院;嘲笑一下他的助教,热心率直的克莱夫·斯戴普尔兹·刘易斯(C.S. Lewis)(注:1898-1963,英国小说家、学者,著述多宣传基督教教义,主要著作有《斯克鲁塔普书简》、《爱情寓言:中世纪传统研究》等,还著有科幻小说及儿童故事集《纳尼亚王国历险记》。);抱怨别人逼他学这学那,他这样说,“其实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我自己的工作。”
这项工作就是他那部早慧的处女作《失明》(The Blindness)(1926),由J.M.登特出版,用亨利·格林这个笔名发表,那年作者才二十一岁。尽管从很多角度看,这都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但它并不是人们期望可以从一个大学生那里看到的那种唯我主义习作,而是一本经过深思熟虑的力作,带有他后期作品的全部鲜明特征:别扭累赘却独一无二的叙事散文体;敏锐的洞察力;浓郁的黑色喜剧风格,事先就透露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出现的“病态幽默”的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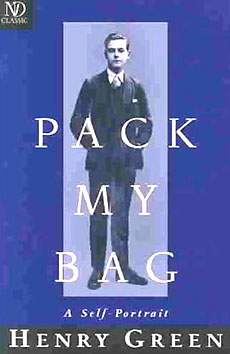
在1926年年末,格林没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牛津。按他自己的请求,他加入他的家族企业当了一名工人,从最最基层的做起;他说他要写一本关于劳动者的小说。他在彭蒂费克斯公司的伯明翰工厂内辛勤工作了两年,他喜滋滋地写信告诉朋友,他恰好住在巴尔扎克小说里描述的那种膳宿公寓里。除了在伯明翰过的那种田园牧歌一般的日子,格林还过着一种不逾越他那个阶层常规的传统生活。他的一个哥哥1917年死于白血病,另一个哥哥生性过于乖僻不适合从商,所以他成了他父亲的彭蒂费克斯公司驻伦敦办事处的合伙人。1929年,他和他的远方表亲阿德莱德·比道尔夫(Adelaide Biddulph,昵称“狄格”)成了亲,这对夫妻开始过起了活跃的社交生活。(伊夫林·沃打趣地称他们为“厕具大王H.约克先生和他漂亮的妻子”。)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人一样,在两次大战之间,他们偶尔会去游览欧洲大陆。不过,格林并不喜欢旅游,“这妨碍了我手淫。”他这么抱怨。1939年,他发表了小说《赴宴》(Party Going),一部表面轻巧却发人深思、一部可以算得上是贝克特风格的小说,它描述了上流社会无所事事、毫无意义的社交生活。
《赴宴》无法获得利润,这一结果就连那位好脾气的出版商登特(Dent)都没法接受,格林就把书转交到荷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托约翰·雷曼(John Lehmann)和雷奥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替他出版。战争迫在眉睫,格林强烈预感到自己会战死沙场,便草草写了一部自传《打点行装》(Pack My Bag),又把妻子狄格和年幼的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送去乡下避难;随后自己加入到伦敦的救援消防局(Auxiliary Fire Service)工作。在那儿他过了好几年单调乏味的日子,和燃烧弹、附近流窜的雄猫,以及各种各样、被某个朋友称作“挺来劲的”时髦女士们打交道。格林是位声名狼藉的勾引家,性情有几分冷酷。“你下部作品的题目该叫‘猎艳’,”他的一位女友发过这样的牢骚。多出来的业余时间都被他用在写《着火》(Caught)上了,这是一部讲述伦敦大轰炸(London blitz)和他的救火体验的小说,极其真实地描绘出一幅战时伦敦的图景——如此真实,使得格林不敢出售它的德语版权,惟恐助长了敌人的志气。雷奥纳德·伍尔夫曾抱怨这部小说把伦敦的消防队描述成“压根就不称职,从头到脚漏洞百出,可以挽救大局的部门甚至稍稍管事尽责的人,连一个都找不出来。”
一般人都觉得格林1945年写的《爱着》(Loving)是他最出色的一部作品。此书描写感官逸乐,伤风败俗,荒诞不经,讲述战时一群英国仆人在爱尔兰的一幢大宅子里纵情狂欢,他们酗酒、淫乱、高谈阔论、一味自得其乐。奇怪的是,经历了五年战争之后,此书却是格林最不悲观的一部作品,它充满了欢乐、喜悦与美好,不难理解此书何以会大受欢迎。这一现象或其他的疑问,还得要用格林“最好”的书都晦涩难懂来做解释,因为格林的每本书都是那么独特,那么与众不同。尽管大家公认《爱着》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也很难把他后来的作品看成是在走下坡路。
不断有人企图把格林归入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里,但这种计划注定会落空:他真正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某种等级顺序,不如说是总体意义上的人类。综观他整个的写作生涯,显然可以发现,他把人类这种动物完全归到同一个种类里,无论是在工厂地板上看见的,在配膳室里待着的,还是在里兹大饭店里吃饭的,都不能免俗。
不管讲话的对象是谁,格林小说里的对话都是无与伦比的。他难得公布他的艺术见解,有一次他宣称一个作者的职责是“认识尽可能多的平常人,倾听最平常的谈话”。他把普通人摆到了一个神圣崇高的位置。他那双灵敏的耳朵把所有无关宏旨的琐屑小事、不合逻辑的推论,以及一般人谈话中不动脑筋的重复一丝不漏都记录了下来。在格林死后出版的作品集《活下去》(Surviving)(1992)里有一个短篇,描写“战时救援消防局”的几个人在一家小酒馆里东拉西扯地谈天。
“哎呀,到今天为止差不多都过去一个礼拜了,你在这家酒吧里找到的这份工对你到底值不值呢?”第四个男的接着说。
酒吧男招待没接他的话,却开口说:“今儿早上我碰到山姆·瑞斯了。”
“噢,乔,我想我还是再花个一便士。大瓶里的酒已经喝光了。”
“马上就得。是啊,他看上去怪里怪气的,那个老黑人山姆。”
“哪个山姆?”
“山姆·瑞斯。哎哟,你保准记得他,泰德。”
“你是说那个沃利·瑞斯吧。”
这类谈话每次可以持续两到三页,可丝毫不让人觉得乏味单调,反而是越来越充满诗意。还可以举个例子,在他1952年写的《溺爱》(Doting)里。
“可你知不知道,有三个人死在了我的病房里,当我在那儿的时候?”
“别这样讲,亲爱的。”他母亲说。
“我真觉得你本可以把我放到单人病房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