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天才和他的天才夫人
作者:王青松 :[美] 斯泰西.希夫

大家都知道,若不是纳博科夫夫人,《洛丽塔》很可能永远只是个胚胎而不会诞生。这本书回报了她的善举:倘若她没能活到它在美国出版的时候,纳博科夫将不得不创造出她来,因为人们极力把亨伯特·亨伯特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同起来。在发行会上,崇拜者告诉纳博科夫夫人,他们根本没料到作者会同他结婚三十三年的银发妻子一同出席的。“是的,”她微笑着、从容不迫地说,“那正是我来这儿的主要原因。”至少有两次,纳博科夫准备把小说手稿投进伊萨卡(注:Ithaca,美国纽约州一地名。)的焚化炉中——像《微暗的火》里的作者约翰·谢德一样——都被妻子阻止了。她正是那位驾驶奥尔兹汽车的女人,而他则在其后座上写小说;她又像是始终睡在亨伯特·亨伯特的汽车旅馆房间里的女人。她为书的出版做各种安排。有段时间,她在纽约四处奔走,带着一只不惹眼的牛皮纸袋,里面放着她丈夫对编辑称为“定时炸弹”的书稿。那么小说中有纳博科夫夫人存在的痕迹吗?没有,但她的指纹可谓无所不在。(有些人坚持寻找她在小说中的影像。当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伊萨卡会见过纳博科夫夫妇后,他对自己的妻子说,他隐约觉得薇拉·纳博科夫就是洛丽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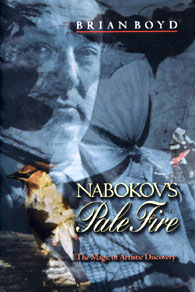
当纳博科夫夫人在小说中露面时,更多是以她本性的对立面,而非实在的她出现的。纳博科夫笔下的妻子们更多的是些不再会有的或永不会有的女性;她们是死气沉沉的人,变化无常的人,迷惘失落的人,愚蠢的,粗俗的,邋遢懒散的,一事无成的,野心勃勃的人。比较而言《塞巴斯蒂安·奈特》中的克莱尔似是一位已故人物的化身——她主要出现在薇拉和弗拉基米尔刚相识时写的作品里。在1923年9月写的短篇小说《喧闹》中,纳博科夫塑造了一位容光焕发的、优雅的、手腕纤细的女性,长着一双灰色的、尘土似的眼睛和一头消融于阳光中的头发。这种外貌特征同样适用于小说《天资》中的津娜,任何一位了解纳博科夫夫妇在柏林时情况的人,一听到薇拉这个名字就会联想起她。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叙述者都是热情地赞美聪明的打字员的人,这些打字员当中,对克莱尔的描写无疑与纳博科夫夫人最为接近:
但最重要的是,她是那些稀少的,少而又少的女人中的一个,她们并不认为世界该当如此,也不把日常生活仅看作是她们女人本性的普通映像。她富有想象力——灵魂的肌肉——而且格外强,几乎有种阳刚之气。她还拥有真正的美感,它与艺术的关系远不及发现环绕煎锅的光圈或垂柳与短腿长毛狗之间的相似处的那种敏捷的关系更紧密。最后,她享有一种机警的幽默感。怪不得她与他的生活契合得如此完美。
希碧尔·谢德与纳博科夫夫人表面上有些相似,而一位薇拉的替身曾挽着《国王、王后和无赖》里的作者闪耀亮相。但只有《说吧,记忆》和《瞧那些丑角!》中的“你”——对这些“你”,纳博科夫断然拒绝谈论——才真正体现了他的妻子的本性。
当纳博科夫本人承认薇拉几经折射的形象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时,纳博科夫夫人则矢口否认。我当然不是津娜,她反驳道,津娜只有一半犹太血统,我是纯犹太人。同样,纳博科夫也爱否认他的人物与自己有相似之处:他误认了一只蝴蝶——这种错我是绝不会出的!他德语说得比法语好——因而这个人不是我!为了使问题复杂化,对凡是涉及丈夫的事谨小慎微的纳博科夫夫人,竭力使自己的说法含混暖味,模棱两可,或者干脆就不准确。有人问她当初怎样遇见纳博科夫,即便对方是好友,她也只说句“我记不清”。有一回,纳博科夫正要向一位美国学者泄露他和薇拉相识的过程,薇拉打断他的话,尖刻地问:“你是什么人?是克格勃?”其他人的妻子被史书所流放,而她却奋力要历史放逐自己。
无须在虚构的关联上耗费精力,首先,因为就在我们忙于在小说中寻找薇拉·纳博科夫的时候,我们从她的书信中获得了关于他的深刻印象。再者,现实生活中的纳博科夫在许多方面是他虚构的人物的对应者。正如一位他最喜爱的出版商警告说:“臆造出一个真实的纳博科夫是桩错误。”他创造他自己,不停地修饰自己,他既存在于现实中,又存在于书本里,如同表演者在表演、魔术师在耍魔术一样。多年来,随着魔术师技艺的发展,他需要个助手。
对纳博科夫夫人的怨恨随同那种神秘性一同增加。学生们奇怪,教室里的这只“灰鹰”是何许人也,而同事们——他们都知道,纳博科夫没有哲学博士学位,没有研究生,没有新生,而到五十年代中期,他却拥有令人妒忌的注册学生数——都对这种夫唱妇随感到恼火。当有人考虑给纳博科夫另觅一份工作——他在康奈尔时只找过一次——一个前同事劝道:“别去雇他;活儿都是她做的。”
纳博科夫对这类诬蔑不加理睬。他对学生们说,Ph.D代表“市侩局。”(注:Ph.D是哲学博士的英文缩写,与“Department of Philistines”的缩写相同,后者是纳博科夫戏谑、嘲弄那些搬弄是非的人捏造的。)他让薇拉顶替自己上班,甚至于轻率地对待讲课。一个朋友坚持要去听他讲课,他只好退却说:“啊,好吧,如果你想成为受虐狂的话。”同事们妒忌他有那么多学生听课,被他的捕蝶网迷惑住,也被他妻子的忠诚惊呆了。就最后一点,爱德蒙·威尔逊同他们一样深有感触,他痛恨她主持考试和一贯的奉献精神。在日记中,他抱怨说:“薇拉总陪着瓦洛佳,人们觉得,当她的面与他争论,她也会怒发冲冠。”其他作家们的妻子被直截了当地问,为何不能向薇拉学习;无形中,薇拉被树为公认的标准,正如小说家赫伯特·戈尔德(Herbert Gold)所称的,她是“作家妻子比赛”的世界冠军。

有人说,纳博科夫夫妇将他们的婚姻净化成了一件艺术品。更确切地说,应是他俩的婚姻在艺术工作中被净化了。《洛丽塔》出版后,商业信函雪片般纷至沓来,纳博科夫夫人可能会给一个出版商一天写四封信。1958年的一封致普特兰出版社(Putnam)的信中,她这样开头:“今天我给你们去过信,但弗拉基米尔要求我再写一封。”许多这类信件都如三色冰淇淋一样——分别用英语、法语和俄语写。打字员到处跑,不是为他,而是为她。没有诸如休假之类的时候;迪米特里·纳博科夫说:“她花在纯粹的消遣上的时间非常有限。”六十年代中期,夫妇俩在意大利旅行时,纳博科夫夫人借在每处逗留的机会,与普特兰出版社议定合同上的一项项条款。《洛丽塔》出版后,公众的纳博科夫成为薇拉·纳博科夫的了,包括纳博科夫的声音。这与学生说的腹语术相距不远了。
当纳博科夫想知道有关《洛丽塔》电影版的消息时,他给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写了几封信。一封是薇拉署的名字:“弗拉基米尔要我告诉你,假如你不介意由我转告的话,他很乐意你能回信。”因为某种缘故,有次他感到非要亲自写信不可,或装成自己写信说:“我很高兴与你交流,但我憎恶电话,尤其是长途电话。若你愿同我妻子说话,我将会一直待在一边听着。”纳博科夫遂几乎不挨近电话,谣传说他正被妻子扣为人质。
即便她对此有所察觉,她又作何感想呢?她会为延误回信向朋友们道歉,但从不将致歉变成叫屈。1963年,她的冒险看似到了悬崖的边缘:“我被弗拉基米尔的信弄得精疲力竭(我是指他收到却由我来回复的信),这不仅是体力活,而且所有的决断他都想由我来做,我发现这比单纯打字更费时间。即使当迪米特里很小,又没有别人帮忙,我也比现在更悠闲。请注意,我这不是在抱怨,而是不想让你以为我在偷懒。”她时常强调她是多么不适应自己的工作。就在《洛丽塔》出版后,她给朋友写信说起令她不堪忍受的工作压力,尤其,她说,因为她丈夫对商业事务不管不问。“此外,我决不是又一个塞维涅侯爵夫人(注“Sévigné,1626-1696,法国女作家,著有《书简集》,收有她与女儿等人大量的通信。)。一天写上十到十五封信累得我浑身无力。”二十五年后,除了工作量外什么也没变,她又对这位朋友说,她不善写信,一生中一直如此,可在近三四十年里,她除了写信什么也不曾做过。她一度有些悲伤地承认,她的孙子们都爱好文学。但她仍宠爱着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随着时间的迁移,她工作得愈加努力。她修订德语版的《说吧,记忆》、法语版的《坚决的意见》和意大利语的纳博科夫诗歌,并且在丈夫逝世后,她开始把《微暗的火》》译成俄语。她写信给朋友们说,最后一件翻译甚为艰苦,但到了八十岁,孤独、体弱,这项工作倒使她很幸福。那年,她对律师们说,她估计每天工作六小时,用以回信、谈判和翻译。有几个人一直知道她的工作异常繁重。七十年代初,批评家阿尔弗雷德·阿佩尔(Alfred Appel)建议说:“你无须为被埋没在弗·纳的信件之后而难过。只有一个办法:为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减少工时而罢工。在蒙特勒宫(注:the Montreux Palace,蒙特勒宫是一家旅馆,亦即他们在瑞士的家。)前,一边举着‘弗·纳不公正对待辅助服务’上的横幅,一边作着劝阻人们上班的手势,定会起到某种效果。”
她当然不会这么做;相反,在私人信件中却充满了她对他的关心:纳博科夫工作如何辛苦,劝他休息是多么地难。她是极其称职于自己的工作的。她的俄语,据她丈夫估计,“很了不起”;记忆力又超人一等(其他不算,她能背诵《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几乎所有的纳博科夫的诗作);她对措辞精妙的语句格外敏感;她似乎是个凭借非己的生活而成功的人。她是与庸俗气作战的理想参谋。像纳博科夫一样,她也有见字、听声犹如有色彩的联觉能力。选择做纳博科夫的妻子在她是如此合乎逻辑,以至于很容易忽视他娶她根本不是为了注重实利的事实。她与丈夫共享细节观察之眼:在她的日记里,纳博科夫经常引用她诗意的、不假思索的看法。几乎无人知道她的这一面。她从不允许自己的魅力现于纸上;必须获得她的信任才能领教到她的幽默、温柔和轻捷的措词。(一次朋友们来蒙特勒宫拜访他们。席间,纳博科夫想往咖啡里加糖,却洒了出来。薇拉伶俐地说:“亲爱的,你刚才给你的鞋子加糖了。”)更多时候,人们总见这对生死同盟在庸人充斥的世界里为博取文学荣誉而战斗着。她仿佛不知道那种恶意,不知道自己有“泼妇”的恶名;即便她明白,一位羞怯的、孤僻抑郁的、有严格道德操守的女性很容易被激怒、变得离群索居和顽固不化,她也毫不在意。作为魔术师的完美助手,她就是被锯成两截也不失优雅和从容。

她的律师无法忘怀,1967年,在彼埃尔旅馆灯光暗淡的酒吧里,她设法迫使那位美国出版商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的情形。她一句没说就成了。当她坚持合同中的生活费一项必须增加时,他认为她有着超人的洞察力,事实证明这种增加利润丰厚。这位律师不曾于1910年间去过彼得堡,也不曾于二十年代到过柏林,而纳博科夫夫人曾有过。她对身边世界的崩溃瓦解已经习惯。这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留下痕迹;对他妻子来说,它锤炼出了她的个性。对于她,一切这样的机会都是时刻存在着的。
她遭遇的挫折是想在混乱的世界里过有序的生活,想在排字员是人的世界里印出十全十美的书籍。她要人们,特别是她自己,遵循她丈夫的文学标准:那种我们中罕有,出版商中则更少能应付得了的标准。她和迪米特里给了纳博科夫这个世界欲从他那里夺走的一切:生活稳定、宁静,古老欧洲的气氛和独创性的幽默,坚定的意见和高雅的、永不堕落的俄国人。多年来,他是一个寻找梦想王国的民族瑰宝;薇拉似是他生活于其间的国度。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在这个世界里的世界,纳博科夫的人物们常常找到了极乐的天堂。一位前康奈尔大学学生说:“他俩牢不可分,自给自足,构成一个二人宇宙。”还有什么能比那在伊萨卡时租住过的一长列的房子,租借的猫、银制餐具以及租借的家族照片更让人理解不透的呢?难怪纳博科夫将其视为假象。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高兴地固守自己的孤独,证明他是别人的白日梦。当一位传记作家给他看一份准备访问的人的名单时,纳博科夫对之作了番注解:“此人讨厌我/几乎不知此人/一个敌人/知其甚少的人/我不认识他/对他略知一二/不能肯定曾否见过他/我的表亲/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最后一次会面是1916年/一个(你)臆造的人。”
那么,让我们再回康奈尔教室去浏览一下。正如我们永不知道哪个是福楼拜的鹦鹉一样,我们也永不知晓纳博科夫夫人究竟在那儿做什么。(她是有支枪,但没有证据表明她曾带去过课堂;纳博科夫一贯身强体壮,且不对粉尘过敏。她是部百科全书,但他同样是。)答案的蛛丝马迹或许存在于1924年写的短篇小说《巴赫曼》中。巴赫曼星光闪耀的钢琴生涯开始于他的崇拜者佩罗娃“身子笔直,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地就坐于他的音乐会的前排座位那天,结束于她没能来的当晚,当时巴赫曼在琴前坐下,发现了前排中央的空位。一个康奈尔学生回忆起纳博科夫教授上课的情形后,似乎领悟了巴赫曼的秘密。他揶揄地说:“似乎他讲课是为了她。”纳博科夫声称艺术家梦寐以求的最佳观众是“挤满戴着他自己的面具的房间。”关于纳博科夫夫人,他对一位采访者说:“要知道,她和我是我最好的观众。应该说是我的主要观众。”有一天,他在黑板上列出五位最伟大的俄国诗人的名字时,他还可能在同谁交谈呢?五人中有位名叫“西林”——这是他到柏林后开始用的笔名。一个勇敢的学生问:“西林是什么人?”“啊,西林,我将藉他的作品加以分析。”纳博科夫板着面孔,没作进一步解释。一次在伊萨卡,一个格外阴暗的早晨,纳博科夫照常开始讲课。几分钟后,薇拉从前排座位上起来,打开了阶梯教室的灯。她在开灯时,她丈夫脸上露出一副天使般的笑容。他在前面骄傲地打着手势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的助手。”
对舞台上的人来讲,最不想被人看见倒可能最为显眼。她一定知道这个道理。似乎无人胆敢问她是否感到受压抑、有些被埋没的失落感——或就此而言,感到是处于核心位置、必不可少、是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伴侣。她无法分出神来让人有机会问她;她对一位传记作家说,你越不考虑我的存在,你离实情就将越近。她将做称职的纳博科夫夫人推演至一门科学和艺术的境界,但她却假装不曾有过此人。她清楚地觉察到,她并非处在丈夫的阴影笼罩下,而是站在他的阳光之中。当初认识他时她就觉得,他是那代人中最伟大的作家:六十六年里,她抱定这项真理,仿佛是为一切损失和混乱,以及历史的沧桑寻求补偿。一位康奈尔同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纳博科夫夫人被迫替丈夫讲课时,她对讲稿是只字不动——她只在空白处对他严加责难。可是,毫无疑问,她什么也不改变!难道他不明白,每堂课都是一件艺术品吗?
1967年,一位美国崇拜者恰巧在意大利遇见纳博科夫夫妇。他们手中正拿着捕蝴蝶的网兜,沿着山路往前赶。纳博科夫一脸喜气;当天早些时候,他发现一个罕见的蝴蝶样本,恰是他一直在找的那种。他回去找来了薇拉。他想在捕捉时,希望薇拉能同他在一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