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华顿的尖眼睛
作者: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文:[英]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注:该文作者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传记家。在此文中,她对伊迪丝·华顿的短篇小说作了一番研究。)(Margaret Drabble)

华顿对文艺、智辩、装饰和高级时装潮流中突如其来的事物和普遍遵循的东西生就了一双锐目。她能够发现伪品,也能够识别真货。在任何意义上,她都是一位行万里路的女性,而她鉴赏的领域也是十分广阔。
读短篇小说最好是读集子。伊迪丝·华顿是这种文体的行家里手(她这个年龄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把她看作是短篇小说大师),她这两大册由小说家莫琳·霍华德(Maureen Howard)收集编订的文集,也声名渐隆。这两册书内容丰富,从天马行空到现实主义,从讥诮讽刺到温情脉脉,华顿尝试的风格之多让人眼花缭乱,而她也确实写得得心应手。这里有故纸堆里的题材——鬼故事,寓言,历史幻想,还有描写一个狂热怀旧的鉴赏家的篇什。同时也有不少对当代欧美习俗的精透剖析。华顿给礼仪和道德之辩带来了新锐视角。她深知该怎样写好一篇小说。在《写一篇战争小说》(Writing a War Story)中,她构思了一个准作家,欧文·斯邦。此人发现自己面对大叠淡紫色稿纸时,竟不知所措,没法把她“丰盈的印象”表达出来。
这件事情她想得越多,就好像越不知道该怎么去写一篇战争小说,或者写成其它形式。为什么小说总得有开头,又得有结尾?生活可不是这样,它就是过啊过的。
如果华顿自己也有过这种怀疑,她可掩饰得很好。她从容不迫地组织材料。构思、选材、剪裁、成文,最后摆在读者面前的是瓜熟蒂落,令人满意的专业产品。我们读她的作品,就觉得万无一失。她的小说总有成效。

这两册书篇幅实在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我没有读过,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读起才好。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赏评一篇华顿不太重要的小说,探一探那或许是所谓的蛇尾吧。这篇小说讽刺了文学名声莫名其妙的性质,情节完整,风格俨然,俏皮之处引得读者开怀不已。《赔款》(Expiation)最初发表在1903年12月的《赫斯特环球杂志》(Hearst's International-Cosmopolitan),当时华顿已经成名,但还没有像两年后发表《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时拥有那么多读者,所以也还没有为发现自己名声显赫或喜或忧过,尽管这篇小说显示她已为此做好了准备。《赔款》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作者在等待自己首部长篇小说《张与弛》发表后的舆论反映时,既期待又害怕的心理。篇名是揶揄华顿在1876到1877年间——当时她才十五岁——写的一个未发表的同名中篇,关于一段和虚构的恶意评论交织在一起的倒霉恋爱(其中部分是对煽情小说的滑稽模仿,她母亲不主张她读那些小说)。这立马就可以和简·奥斯汀的早期作品来番比较,因为近一个世纪前,奥斯汀也是在相仿的年纪开始文学创作,她的处女作《爱情和友谊》(Love and Friendship)以及其它练笔也是对情感小说的仿作。华顿的作品中渗透着奥斯汀的影响:这两位小说家都兴致勃勃地嘲讽把作家当件事来干的人,也嘲讽在叙述手法和风格上改弦易帜的做法。
在这篇有趣的作品中,文坛新手保拉·费斯罗——一个婚姻如意,身份体面的纽约名流,和她的表姐克林其夫人形成对比。克林其夫人精明世故,喜欢死撑台面,婚姻不太如意,而她丈夫从未在小说里出现过。她以写作为生,写一些自己姑且称之为“伪科学和口语鸟类学”的文章——诸如《鸟窝半敞》和《怎样闻花》。她们的叔叔则是第三种作者,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在奥斯宁当主教。他的文学作品有《约拿的痛哭》(二十章无韵诗)和《明亮地穿过玻璃杯》。后者是个陶冶情操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患了肺痨的贫苦女孩如何勉力养活两个白痴妹妹。我们猜想,这位主教的大作销路不怎么样。
有趣的是,虽然这三个人的文学创作态度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发觉要使一部作品畅销,猛烈的抨击比浮泛的赞扬更能见效。华顿精彩地刻画了费斯罗夫人所受的微妙的心理折磨,先是因为她丈夫对她毫无原则的赞美和“愚不可及的认同”而痛苦不已,接着是害怕她的主教叔叔会因她的书不太宣扬道德律而恼火,而且一旦把他惹恼就毫无办法了,最后是由于评论家们公认《张与弛》具有“耳目一新的人生观”。最后一种打击当然最要命。她的第一个评论者认为她震撼人心的社会批判“虽然人物刻画毫无力度,情节也缺乏连贯性,但家庭生活描写得很好,可以称得上是个相当不错的故事”,我们未来的易卜生一听到这话就满心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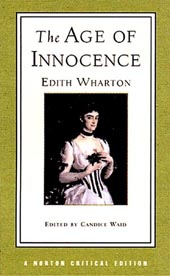
主教被说服了到教坛上抨击侄女的小说,于是它立即畅销起来,一场潮流过后,大家的结局都挺好。当费斯罗夫人看到她的“印有作者像的新版书(第十五万册)”被装饰在车站的书肆中,不由抱怨道,“他们没有权利把我的照片当作招贴画!”自从那天她“不太确信地”告诉克林其夫人说她觉得一本书的成败完全应该按照书的好坏为准,她很快就取得长足的进步,学到不少东西。
对打造文名的讽刺想象扎根于当时的年代,主教对小说的批判能带来商业价值显然和恶毒攻击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不无关系。1894年,该书在《哈泼斯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上连载时,引燃了熊熊怒火。它被一位主教当众烧毁,过后却大大地出名。(在1912年版的前言中,哈代写道,此书“被一位主教焚毁,他很可能是因为无法来烧死我而感到绝望”。)但是,《赔款》也是为我们这个时代而作的,如今猛烈的抨击虽然不是出自主教之口,但还是能把书卖出去。

华顿对文艺、智辩、装饰和高级时装潮流中突如其来的事物和普遍遵循的东西生就了一双锐目。她能够发现伪品,也能够识别真货。在任何意义上,她都是一位行万里路的女性,而她鉴赏的领域也是十分广阔。外表上她不是个现代主义者,但她的阅读量惊人,而且她分析社会的手段一寸不拉地紧跟时代——其实是超越时代。向来认为,她对道德风尚的嬗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而这正是她小说的主心骨之一。在多篇小说中,她着力于绘制新的二十世纪社会地图。她预见到传统宗教的式微和相对主义思想多样化的发展。(在《信仰的种子》(The Seed of the Faith)里,她满怀同情并恰如其分地低调刻画了一个年轻穷传教士的疑虑。他被困于北非,在与“一个正在研究中部山区部落的法国民族学家”有过两三次交谈后,很是悲惨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在她的图表中,离婚率正势不可挡地攀升,而妇女解放的进程却缓慢并不时裹足不前。在《估算》(The Reckoning)和其它一些短篇中,她细细描述了那些自称信仰她所谓的“新种族主义”的人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挣扎所付出的高昂的个人代价。离婚和各种婚外情为她提供许多故事情节,而她的写法则从讽刺到悲剧到悲喜剧一再改变,有时在一篇小说内都有细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