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高采烈写市井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这首诗在本书作为总论的第一篇文章中已经引用过一次。在开始谈到唐伯虎的时候,再借此作一点议论。因为阊门是他的出身地,他的父亲唐广德便在这里开着一家商店,养活全家老小;再引申来说,阊门所代表的那一种商业社会氛围,又是他的整个生活背景。唐家在唐寅之前,世代以经商为业,没有出过读书人。唐寅在科举失败之后,虽没有经商,但他以卖画为生,仍不脱离商业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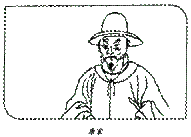 中国自古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所谓“四民”——士、农、工、商,商在最后,甚至常常被看作是贱民。汉代发生战争时,“良家子”是军官的来源,罪徒和商人子弟则是士兵的来源。宋代陆游在《家训》中告诫子弟:“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之事耳。戒之戒之!”似乎一入市井,便随落下流。明代朱元璋建国后,打击商人更不遗余力。禁止民间从事海上贸易,把城市富民迁往荒瘠地区,借故杀死巨商沈万三并抄没家产,甚至规定商人只准穿布衣等等,致使明初商业经济急剧萎缩。商人不过做买卖赚钱,为什么竟被视为洪水猛兽一般?关键在于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帝王要把读书做官成为获得社会地位与财富的惟一途径,把大多数人束缚在土地上,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中。商人财富和他们的享乐生活,在上层削弱了官府的权威,在下层引起人民的非分之想,最容易破坏专制政治和传统道德。 中国自古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所谓“四民”——士、农、工、商,商在最后,甚至常常被看作是贱民。汉代发生战争时,“良家子”是军官的来源,罪徒和商人子弟则是士兵的来源。宋代陆游在《家训》中告诫子弟:“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之事耳。戒之戒之!”似乎一入市井,便随落下流。明代朱元璋建国后,打击商人更不遗余力。禁止民间从事海上贸易,把城市富民迁往荒瘠地区,借故杀死巨商沈万三并抄没家产,甚至规定商人只准穿布衣等等,致使明初商业经济急剧萎缩。商人不过做买卖赚钱,为什么竟被视为洪水猛兽一般?关键在于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帝王要把读书做官成为获得社会地位与财富的惟一途径,把大多数人束缚在土地上,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中。商人财富和他们的享乐生活,在上层削弱了官府的权威,在下层引起人民的非分之想,最容易破坏专制政治和传统道德。
这一种传统影响于文学,特别是主要出于士大夫之手的诗歌,一般对商人也多取鄙视的态度。以白居易的《琵琶行》来说,那一位长安名妓“老大嫁作商人妇”,在作者看来是一种“天涯沦落”的结局。至于专门写商人生活的诗,像元稹、张籍的《贾客乐》、刘禹锡的《贾客词》、白居易的《盐商妇》,等等,都是用讥刺的口吻描摹商人的富足与享乐,并且常常拿农民的辛劳来陪衬。好像凡是不做官而有钱,就是荒谬,就是发不义之财。与此相联系,中国古诗词中写城市商业社会的作品也非常少。偶尔涉及,难免谩骂一通。如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诗:“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臛。啬止廿蟹??,侈唯僣车服。”
但不管怎么样,商业总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行业;经商致富,是一条具有吸引力的生活道路。虽然受到政府的抑制,商业仍旧时起时伏地发展着。以苏州的情况来说,本来在元代已经相当繁华,明初受到沉重打击,萧条近百年,到明中叶再度复兴,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祝允明的朋友王琦著《寓圃杂记》,有《吴中近年之盛》一条,说苏州“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衙。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而苏州商业最集中的地段,就在阊门。
文学同样不能永远漠视商人的存在。首先在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如戏曲、小说中,歌颂商人的作品,从元代开始明显增多。在明代小说里,可以看到《卖油郎独占花魁》,写一个卖油的小贩获得了绝色女子的欢心;可以看到《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写一个落魄书生随商人出海,无意之中发了一笔大财。而一些居住城市的诗人,也开始用同情的或是艳羡的笔调写商人生活。
唐寅的《阊门即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从诗的语言艺术来看,并不是很讲究。它的最大特点,是作者以商人子弟的身份,兴高采烈地描绘阊门一带繁荣的商业经济。这里既没有传统士大夫对商人的蔑视,也没有狭隘地把金钱视为罪恶,更不带一点自卑的心理。诗人把吴中即苏州城赞美为“天下乐土”,又将阊门夸为乐土中的宝地。这里有大量的金钱运转不息,有许多美貌女子为商人献歌献舞,各种交易彻夜进行,各地方言喧喧嚷嚷,组成了一幅难以描绘的市井图画。从唐寅的笔下,可以感受到异常热烈的商业生活气氛,和一个年轻的商人子弟的快乐而自信的心情。这样的诗,虽然不能说过去从来不曾有过,但至少可以说过去极少出现。
人类的生活本是无比丰富,但有各种教条对生活加以否定,使文字能够表现的内容变得单调。当文学中出现新的生活场景,或是以新的态度看待以往被否定的生活时,只要诗人之心是真诚的,就应该承认这是文学的进步。
|